撰文|趙立波
同治六年,是曾國藩一生之中少有的清閑的一段時間,因此處理完日常事務後,他最喜歡和他的秘書長趙烈文談話,內容雖然廣泛,卻都是深度的著眼未來長遠大局的話題,談話甚至上升到道光以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上來。從而引發了對于周邊各國未來全球化走勢和百余年後中國必然在世界中呈現東升西降的必然趨勢。在此之前,我們很有必要簡要介紹一下趙烈文基本情況。
趙烈文,字惠甫,號能靜居士,江蘇陽湖人。其父趙仁基,道光進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趙烈文自幼紮實地系統地學習了傳統教育,但此後三次試均名落孫山,于是絕意仕途,專心鑽研務實之學。

趙烈文資料
大約在1856年1月被其姐夫周騰虎推薦入曾國藩幕僚,1861年12月,由曾國藩專折向清廷請示奏調赴軍營,稱其“博覽群書,留心時事,可堪造就”,統籌負責曾國藩日常辦公事務安排和文秘工作,因此迂回進入了大清官員系統,先後擔任曾國藩幕僚同時兼任曾國荃首席參謀,平定太平軍內亂後,被時任直隸總督曾國藩提拔爲易州知州,在曾國藩去世後辭職隱居常熟終老。
其實,早在鹹豐五年(1855)年,趙烈文當時只有23歲的時候就第一次進入曾國藩幕府,但是因爲雙方在重大軍機問題上未能達成共識,最終導致趙烈文迅速離開。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已經是師徒關系的二人在閑談時,還回顧了當時的一些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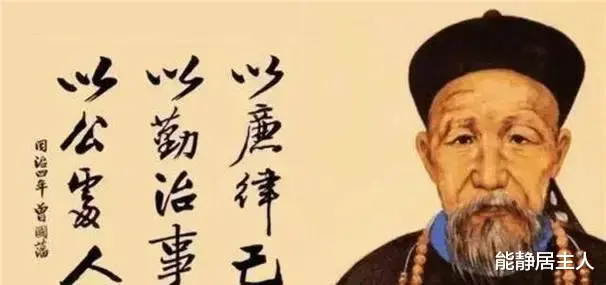
曾國藩畫像
趙烈文四姐夫叫周騰虎,當時是曾國藩非常器重的幕僚,因此周騰虎將小舅子內舉不避親推薦給曾國藩,而此時趙烈文科舉落第後又沒有固定經濟來源,所以曾國藩馬上拿出二百裏銀子聘請他入幕,但是很遺憾,這一次二人未能産生默契,然後沒多久他就回到了江蘇老家。

曾國藩箴言
多年後,曾國藩和他討論人才問題時,趙烈文還不無感激地說:“師本來第自繩耳,于人未嘗不寬。”接著就說起自己當初年紀小,沒什麽名氣,僅憑姐夫周騰虎一句話,您就派人送來二百兩銀子聘請他,此舉動不可謂無氣魄。曾說:“此在吾處亦僅有之事,以弢甫繩足下,且聞足下往日之議論故耳,不常有也。”
話雖不多,卻說明曾國藩在軍費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還是非常原因花錢招攬人才的。
現在就說正題,鹹豐十一年,因爲戰亂和生計問題,加上一個機會,趙烈文第二次入幕並向曾國藩遞交了一份長篇谏言,其中對當時外國情形給予了明確預見,正是這一預見,深刻地影響了曾國藩後來大力倡導洋務運動的舉措,因爲趙烈文在這次萬言書中首次提出未來百年走向必然是“開通六合”。

趙烈文手劄
當時的情況正是太平軍勢力極端強盛,他卻說太平軍不是最大威脅,中國最大的禍患在外國: “外國夷人,政治修明,國家治理,民力富強。人人奮勉,好勝心強而以不如別人爲恥,這些西方人對中國的政務民情,險阻風俗,今天一個圖謀,明天一個說法,考慮事情唯恐不明確,觀察事情唯恐不細微,搜集我們的文化經典,翻譯傳播,兢兢業業,從未有間斷過。”
對此趙烈文總結說:“他們的志向不在小,國家的禍患,再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接著趙烈文又說“中國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虛文,學習使用繁瑣苛刻禮儀,而外國方面務求專精簡一,講究實用。似乎未來大勢是天意要“開通六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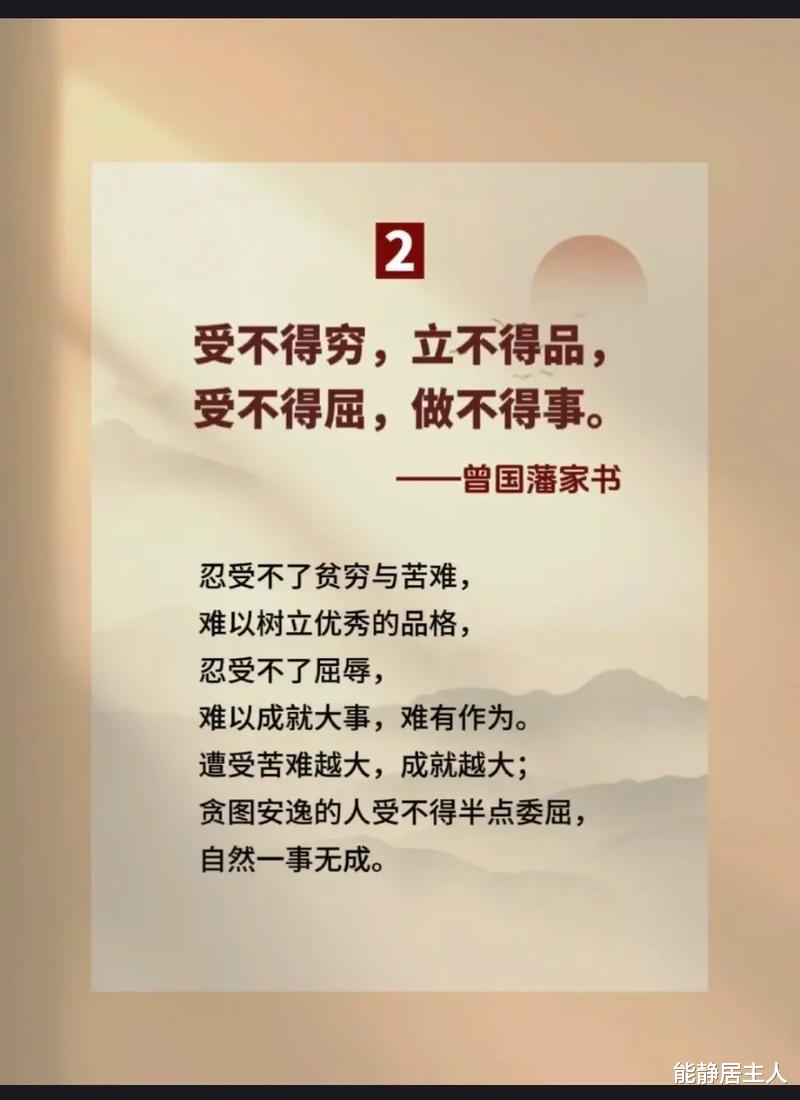
曾國藩箴言
趙烈文的預見很清楚,那就是說要實現宇宙空間全部聯通,用現在時髦的話就是“全球一體化”概念,這在一百五十年前的說法堪稱石破天驚之論。趙烈文最後總結說,外國人也並不是超出人類的異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麽奇異之術,只要我們反其所爲而用之,一定會收到效果。並且說大清之後,全球必然出現“東升西降”的曆史走勢。
曾國藩與幕僚趙烈文交換了誰是對未來清朝最大威脅國家的意見。曾國藩對他說:“今日有佛蘭西傳教人來見,自己介紹叫司铎,我看這幾年洋人氣殊衰減,來中國者似亦皆無聊之人。”趙烈文說:“俄人有邊事乎否”曾國藩沉默了一會說:“目前還沒得到消息,中國將來最大的禍患恐怕會西方各國,但是不要緊,只要做好洋務,跟進西方,就能超過他們,也就是“東升西降”。

趙烈文手書扇面
並引申說:“自南宋以來,天下爲士大夫劫持,凡要做一件事,不論輕重,不揣本末,紛紛力爭,沒有大魄力的君主,就被他們奪了決定權,宋明之亡,皆由此。”
曾國藩無奈地對趙烈文說: “吾甚佩服足下同治二年與吾書,第一條言審查聽言之道。彼時舉國若狂,皆以開言路爲急,而足下已經燭見及此,直至今日,究竟不能出足下範圍。”曾國藩對趙烈文的看法都非常重視,以至于達到了“甚佩服”的地步,這在曾國藩的交際圈裏絕不多見。關注時事,對外國情形了解,讓趙烈文一直走在了清代知識分子的前列,所以視覺獨到,眼界達觀。
最後趙烈文總結說:“天下事但患胸中見地不真,苟是非當矣,外來囂囂之說,直等之時鳥侯蟲可耳”。這種觀點就是及早預判,用相當的文化見識和定力事先就能給出超前預測,就像鳥捉蟲那樣的迅速准確。

曾國藩箴言
也正因此,曾國藩開始側重于洋務研究,並加大了大清自主造船的力度,同時選派百名兒童出國留學,這其中就包括後來學成回國的鐵路專家詹天佑。
不久曾國藩立即以“制造輪船等事,福建尚奏撥巨款,新立鐵廠,江南已有鐵廠,豈可置之不辦”爲由,向朝廷力爭“制造輪船,實爲救時要策”,並明確要求“奏撥二成洋稅銀片”、“以一成專造輪船之用。”
在曾國藩的持續堅持下,造船水平逐步提高,1868年,江南制造局新造的火輪船,具有八個炮位,中國第一艘用蒸汽動力驅動的水上戰艦下水,曾國藩給他命名爲“恬吉”號。當時在上海試航後,“恬吉號輪船初成,逆風劈浪,船行甚穩”,一時激發起上海市民的自豪感,競相觀摩航行。
1871年,重病纏身的曾國藩在雙目幾乎失明的情況下,對大清造船業念念不忘,這年的11月,曾國藩來到吳淞口,觀看江南制造局建造的四艘兵船組成的編隊演戲和水師操練,檢閱了槍炮操練和各種最新的水上戰鬥表演。也是曾國藩去世前完成的最後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