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或詠史,或感懷,或抒發對大自然的贊美,或寄托對人事的哀思,在他們筆下可謂是千變萬化。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縧”詩人賀知章用美妙的比喻和生動的描繪,讓我們仿佛看到了那婀娜多姿的柳樹,感受到了春風的溫暖和生命的力量。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詩人楊萬裏的筆下,荷花是那樣的嬌豔動人,荷葉與天空融爲一體,展現出無窮的韻味。在酷暑中,人們從荷花身上感受到了一絲清涼和甯靜。
“蕭蕭幾葉風兼雨,掃盡松花江上寺”,這裏沒有淒涼和悲苦,卻有對秋天的欣賞和感悟。落葉如詩如畫,將秋天的韻味渲染得更加濃烈。人們在落葉中看到了生命的不朽與輪回。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詩人柳宗元的這句詩將冬日的寂寥表現得淋漓盡致。然而,在這寒冷中,梅花卻傲然綻放,“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那種不畏嚴寒、傲骨铮铮的精神令人們爲之贊歎和敬仰。
除了大自然的美景,就連家禽雞都是它們詠物的對象,之前寫過10首詠物哲理詩,今天再寫10首,特點是題目都是以單字入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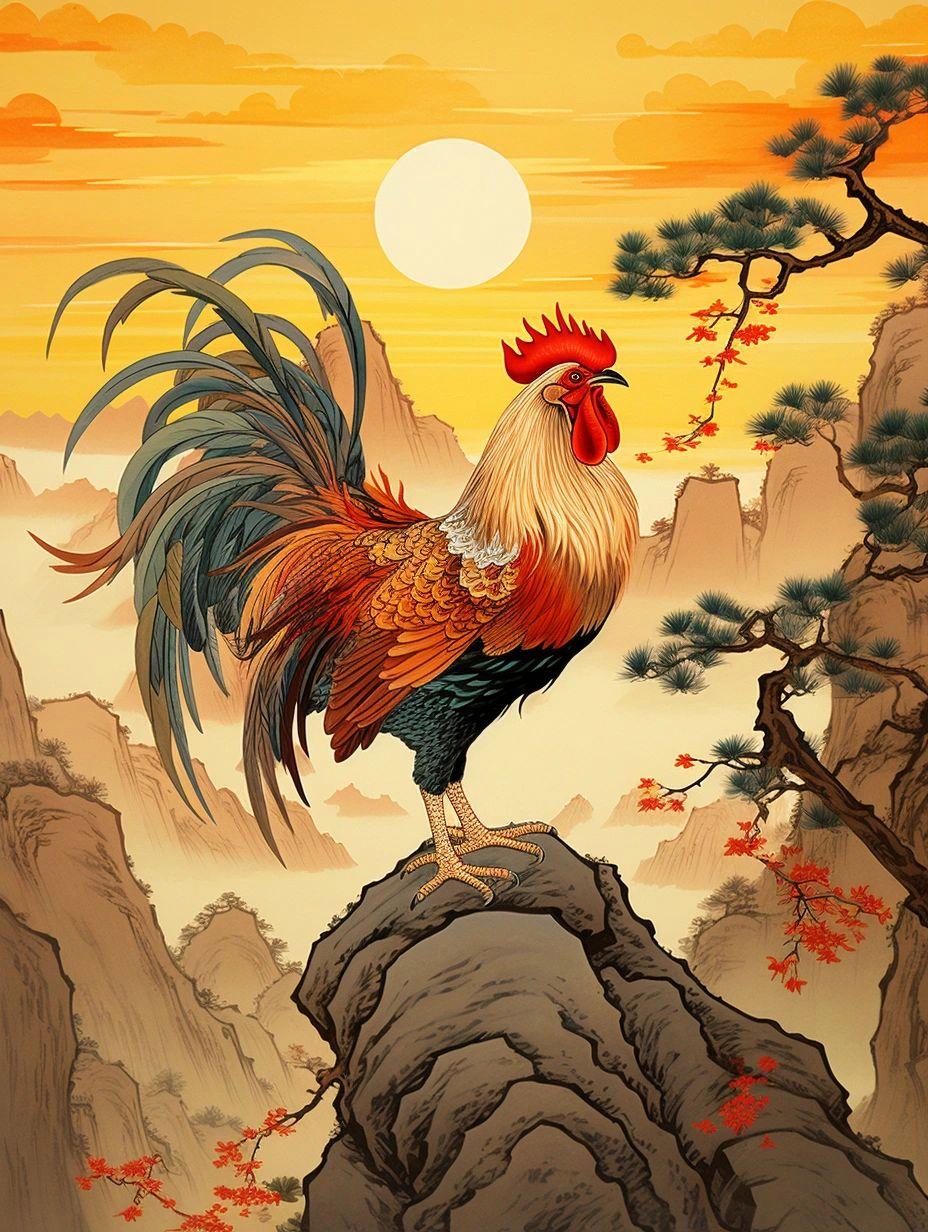
羽短籠深不得飛,久留甯爲稻粱肥。
膠膠風雨鳴何苦,滿室高眠正掩扉。
——宋·司馬光《雞》
雞屬家禽,爲六畜之一,隨處可見,可是人們對它是有褒有貶的評價,所謂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論長短。
早在《詩經》中就有對它的歌詠如《鄭風》的“風雨淒淒。雞嗚膠膠。”
唐崔道融有《詠雞》詩;“買得晨雞共雞語,常時不用等閑鳴。深山月黑風雨夜,欲近曉天啼一聲。”
唐人李賀有佳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
溫庭筠的“雞聲茅月店,人迹板橋霜”;
宋人梅堯臣的“五更千裏夢,殘月一城雞”,又有“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
司馬光的這首詠雞七絕,立意新穎,獨具一格,當爲傳世之作。全詩四句,從頭至尾沒有涉及到一個雞字,但卻句句都在詠雞,不止構思巧妙,用詞也頗爲講究。
雞是家禽,本來翅膀就很短,如今又關在深深的籠子裏,受著種種限制,沒有任何自由,哪裏能夠飛?可見,這雞已被主人完全監控,是地地道道的“家雞”了,其命運該是多麽可悲,怎能不令人大生同情之感??
“久留甯爲稻粱肥”?也許有人會問,這雞所以要長時間地守下去, 難道僅僅是爲了獲得豐盛的谷物,以來一飽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問題的症結不在于“稻,這就是作者的答案,他爲讀者所解梁”,而在于“籠深”,的感。
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合,此時仕途所受的挫折,在洛陽賦閑多年,難道僅僅是爲了編撰《資治通鑒》嗎?可見這兩句是有弦外之音的。
作者在這裏夾敘夾議,在描寫中表露情懷,抒發感慨:“膠膠風雨鳴何苦,滿室高眠正掩扉。”古時報曉,多靠雞鳴,尤其是在那風雨潇潇的昏暗之夜。
“雄雞一唱天下白”,能夠喚醒多少有志者聞聲而起,像西晉祖遜劉琨那樣,聞雞起舞,准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眼下卻有所不同了,人們都在關起門來睡大覺,雞又何苦多此一鳴,擾亂清夢呢?!
不難看出,這兩句是“含不盡之意,在幹言外”。明裏責雞,暗中警人:切勿貪戀安逸,還是奮發圖強爲好!

一世爲巢拙,長年與鵲爭。
欲知雲腳雨,先向屋頭鳴。
頸上玉花碎,臆前檀粉輕。
何時將刻杖,扶助老夫行。
——宋·梅堯臣《鸠》
鸠,鳥名,俗稱鹁鴿。
這種鳥天生性拙,不善于營巢,常常棲息于喜鵲的巢窩中。雖說安居是蠢頓些,然其心卻非常靈敏,每當雲腳低垂,天將欲雨的時候時,它便飛向屋頭,啼叫不止,向人預報陰晴。
歐陽修在其《鳴鸠》詩中所講的“吾老病骨知陰晴,每愁天陰聞此聲”,也正是這種情形。
陸遊在《臨江仙·離果州作》中說得更爲明確:“鸠雨催成新綠,燕泥收盡殘紅。”把鸠鳴報雨直接寫成“鸠雨”,足見其靈驗。
頸上玉花碎,臆前檀粉輕。”這無疑詠的是斑鸠,羽之美,顯得可愛。這朱頸斑鸠,胸前的羽毛呈粉紅色,鮮麗明豔,柔軟輕盈,煞是喜人,令人賞心悅目。
“何時將刻杖,扶助老夫行。”鸠杖,是老人的象征,吉祥之物。
由于此詩作于晚年,所以梅堯臣尾聯就鸠鳥展開聯想,想往安度晚年:希望獲得鸠杖,以安度老齡歲月,無災無難自然到老。

千形萬象竟還空,映水藏山片複重。
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奇峰。
——唐·來鹄《雲》
在大旱的日子裏,正當赤日炎炎,在地禾苗枯槁,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望眼欲穿之時,天上忽然飄來了雲彩;雲彩千變萬化,千形萬狀;有時,飄到江流上空,有時,隱沒大山深處;有時,變得只剩一片,有時,又重重疊疊地堆積。
人們的心也隨著雲的變化而變化,忽喜忽憂,七上八下,到頭來還是盼不到一絲雨下。而此時呢,雲彩卻安靜下來了,它躲在清靜的天邊,幻化出一座炫目的奇峰。
詩人此詩顯然不是爲寫雲而寫雲,而是借物喻人,通過描寫旱天的雲,諷刺朝廷中那些屍位素餐的高官顯宦,抨擊那些對人民疾苦漠不關心的封建統治者。
北宋章驚罷相後,有人作詩諷刺他說:“如峰如火複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幹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就是借詠雲譏諷他身居高位,卻無補于國計民生,解除老百姓的痛苦。
其實,在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裏,除了極少數的傑出的政治家和富于同情心的地方官外,絕大多數的統治階級成員,都是對人民的苦難無動于衷,對百姓饑寒漠不關心的。
《水浒傳》第十五回《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中,描寫的那位賣酒漢子唱的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腸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也生動地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勞苦大衆對旱災的截然不同的心情。

南北路何長,中間萬弋張。
不知煙霧裏,幾只到衡陽。
——唐·陸龜蒙《雁》
陸龜蒙生活的時代,是晚唐的懿宗和宗年間,這是唐王朝瀕臨滅亡、最黑暗最腐朽的時期。
此時,皇帝早已成爲宦官手中的傀儡:朝廷的激烈鬥爭依然如故,藩鎮之間的爭鬥愈演愈烈。
而皇帝則只知貪圖享樂,縱情聲色,奢侈無度。由于賦稅繁重,天災人禍,民不聊生,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終于演變爲全國性的黃巢大起義,加速了唐王朝的覆滅。
陸龜蒙這首詠物詩,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創作的。詩人采用比興手法描寫的南北雁,其實和杜牧《早雁》詩一樣,都指的是因家鄉戰亂而逃往南方避亂的黃河一帶中原人民。
只不過兩詩描寫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杜牧詩意在通過詠雁,表現北方仍然受到外敵的侵擾,勸說流寓南方的人不要回去;而陸龜蒙這首《雁》詩的詠雁,則是意在說明漫長的旅途充滿了危險,向南逃難的百姓還沒有到達目的地便大部分喪失了,這是多麽可悲啊!
詩人的言外之意是說,由于政治腐敗,戰亂頻仍,中國雖大,已沒有可供老百姓安身的地方了。
在只有二十字的小詩中,詩人連用“路何長”、“萬弋張”和“煙霧裏”等詞語來形容旅途的艱險和南飛惟的凶多吉少,表現了對生活在病人膏肓的唐王朝廣大走投無路的人民深深的同情與悲歎。

潇潇十日雨,穩送祝融歸。
燕子經年夢,梧桐昨暮非。
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
衮衮繁華地,西風吹客衣。
——宋·陳與義《雨》
“潇潇十日雨,穩送祝融歸。”雨下得不小,而且一連就是十天,可謂綿綿不絕,
那炎熱的夏天,將毫無疑問地被送走了,秋天即將降臨人間。
三四兩句,宕開一筆,離開雨而寫他物,是作者想象:“燕子經年別,梧桐昨暮非。”
十日潇潇之雨驅走炎熱,迎來秋涼,燕子將歸,又得一年才能返回,何其令人思念?梧桐經雨而凋零,即將紛紛飄落,會與昨暮大不相同。
這兩句雖寫詩人的感受,卻從十日雨中而生出,仍然沒有離開題目,含蓄而蘊藉。
接下來的兩句,承前而生發,繼續描寫自己的感受“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出句寫雨後秋涼,用“恩到骨”加以形容,表面上是感恩戴德,暗中卻含有怨望,當是反語,內心中還是不喜歡這蕭瑟之秋的。
爲什麽呢?對句寫窮居寥落,從正面直接道出。
當年司馬相如受困成都時,曾到了“家徒四壁立”的程度。詩人化用此語,意在告訴人們,自己窮居都城,萬事都很不順心,又遇蕭瑟之秋,和司馬相如有什麽兩樣?
寫到這裏,詩人尚覺得不足以抒發情懷,于是以更大的感慨結束全詩:“衮衮繁華地,西風吹客衣。”
在這繁華天比的京城中,眼下秋天已降臨,那陣陣寒涼的西風,在吹動著自己這位客居京華者的衣衫。只要仔細體味這聯請感慨的含義,頗有當年杜甫“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之感慨。

映空初作繭絲微,掠地俄成箭镞飛。
紙帳光遲饒曉夢,銅爐香潤覆春衣。
池魚鱍鱍隨溝出,梁燕翩翩接翅歸。
惟有落花吹不去,數枝紅濕自相依。
——宋·陸遊《雨》
在唐代杜甫絕對是寫雨好能手,在宋代陳與義寫雨也有一手。陸遊雖爲晚出,對雨也情有獨鍾,寫得頗有特色。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這首《雨》詩,是他五十二歲時寫的,當時在成都範成大的的幕中作事。
這雨說下即下,忽緩忽急,時小時大,變化不定。初來時,其細狀似繭絲,輕輕地飄灑著,如霧如煙,彌漫于天空之中;頃刻間,又急促地掠過地面,像無數箭頭在飛躍,跳動,觀之令人興奮。
陸遊頗能抓住雨的特征,一聯雙喻,貼切形象,觀察人微。特別是“掠”與“飛”兩個動詞連用,更能表現雨的氣勢,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
詩人閒聽雨,頗有感受:“紙帳光遲饒曉夢,銅爐香潤覆春衣。”不難看出,這雨詩是作者在枕上吟成的。
他忽而聽雨,忽而構思,忽而又進入夢中。等到睡醒之後,舉目觀看,只見所臥的紙帳,光線還是很陰暗,天亮得如此之遲,想是外邊仍在春雨飄灑吧?此時此刻,銅爐依舊燃燒著,散發出芬芳的香氣。
由于一夜春雨,衣服有些潮濕了,只好把它覆在銅爐上烘幹,以便白天穿用。
陸遊走出紙帳所看到的情景:“池魚隨溝出,梁燕翩翩接翅歸。”出句寫水中之魚,當爲俯視。一場好大的春雨,下得溝滿壕平,池水驟漲,似乎就要溢出堤岸,只見魚兒正皺地跳躍著向溪溝深處遊去,異常活躍。
由于雨過天晴 燕子飛飛,一個接著一個地返回梁間的巢裏,大概還擔心再有春雨濕了翅膀,古人詠雨常是魚燕並寫。杜甫就曾有“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等名句,陸遊這兩句詩顯然是受了杜甫的啓發,可謂善學前賢。
描繪雨後之景,轉而贊花:“惟有落花吹不去,數枝紅濕自相依。”夜雨過後,將落的花朵非但沒有飄零,反而因爲雨的沾濡,承受丁恩澤,色彩更加鮮麗,朵朵相依相偎,顯得是那嬌媚無限,楚楚動人。
杜甫有詩《春夜喜雨》“曉看紅濕處,不花重錦官城”,陸遊化用杜甫詩句,用了“吹不去”和“自相依” 兩個詞,感情更顯濃重,贊美之意溢于言表。
綜觀全詩,沒著一個“雨”字,但“雨”意卻從隙縫中透出,人的閑適,魚的活潑,燕的輕盈,花的嬌美,無不因春雨而生,觀察之細,體物之工,在詠雨中當屬上乘之作。

初見梁間牖戶新,銜泥已複哺雛頻。
只愁去遠歸來晚,不怕飛低打著人。
——宋·陸遊《燕》
燕人詩歌,繼“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後,曆代詩人吟詠不絕。
說到借景抒慨者,首稱唐代劉禹錫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就名篇而言,唐代鄭谷的《燕詩》:“年去年來來去忙,春寒煙暝渡潇湘。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閑幾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莺過短牆。”
宋代周紫芝的《燕欲來巢》詩:“亂後烏衣巷欲空,擬尋茅舍伴蓑翁。戲將雛去春風裏,銜得泥歸暮雨中。炙手不嫌門戶冷,傍人如獻語言工。明年記取來時節,應是桃花滿院紅。”
明代袁凱的《白燕》詩:“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這三首七律不論是狀物、抒情,還是寄慨、言志,都自然流暢,含蓄蘊藉,刻畫細膩,生動傳神,故被人稱爲詠燕詩中的精品。陸遊的這首七絕,和上述名篇佳句相比,絕不遜色,亦堪稱佼佼者。
燕子築巢,多在檐下梁間。一年一度飛來的燕子,初次見到主人的宅茅從窗到門,都煥然一新,自然是喜不自勝,怎能不在這美好的環境裏,大大地忙碌一番。
燕本來就是勤勞的益鳥,在主人屋宇“牖戶新”的鼓舞下它首先銜泥築巢,一旦大功告成,有了自己的“住屋”,便趕緊生養小燕,並每天飛來飛去,捉蟲甫育幼燕,忙碌得不可開交。一個“複”字。道盡了燕子的勞苦,含有一片贊揚之情。
“只愁去遠歸來晚,不怕低飛打著人。”這兩句雖然是從杜甫“銜泥點汙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中化出、但卻有自己的特點、絕非簡單的襲用。
因爲它不僅寫出了燕子疾飛迅掠時那種輕盈的姿態,而且更寫出了燕子捉蟲哺雛那種急迫的心情,表現了強烈的“母愛”,感人至深。從中透露出對燕子的贊美之意,其內容和感情與杜詩迥然有別。詩人體察事物細致人微,學習前賢富于創新,于此可見一斑。

稚子相看只笑渠,老夫亦複小盧胡。
一鴉飛立鈎欄角,子細看來還有須。
——宋·楊萬裏《鴉》
鴉,俗稱烏鴉,體形較大,羽色灰黑.喙及足皆強壯,多巢于高樹,其鳴啞啞,甚爲難聽。
故有些人將其視爲不祥之鳥。詩人對它多有貶斥。就連唐人王昌齡《長信詞》中的“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也還是贊中有貶呢!
而楊萬裏這首詠《鴉》詩別具一格,角度新穎,語言幽默,不涉褒貶,寫得十分生動,富于童趣。
“稚子相看只笑渠。”如此開篇,猶如高山墜石,突而下,令人驚異,不知其來。
這小孩子到底看到了何物,爲什麽要笑“渠”?真可說是丈二和尚,使你摸不著頭腦,不得不急于看下去,頓生懸念。
“老夫亦複小盧胡”盡管作者見多識廣、經驗豐富、但看到眼前之物,也不禁隨著稚子掩口而笑。
稚子看到稀有的東西,出自天真、好奇,笑是自然的,是童心的一種反映,不難理解。而經驗老成的詩人爲什麽也笑呢?
寫到這裏,稚子和老夫的笑,似乎已神完氣足,讀者的胃口被大大地吊了起來,于是詩人筆鋒一轉,刻畫鴉的形象,揭示父子兩人所笑的原因:“一鴉飛立鈎欄角,仔細看來還有須。”按照一般構思程序,往往是先刻畫物象,後書寫意念,所謂“觸景生情”講的便是這個道理,詩人則別出心裁,先寫意念,後寫物象。
原來有只烏鴉飛落在院庭的鈎欄之上,舉目細看,它居然也長有胡須!
在“稚子”眼中,烏鴉的胡須和人們的胡須沒有什麽區別,所以發出的是好玩的歡笑;
在“老夫”看來,烏鴉的胡須與自身的胡須頗爲相像,所以發出的是會心的微笑。
就是在這笑聲中,傳達出一老一少看到烏鴉胡須時的愉悅心情,以此收住全詩,真是妙趣橫生,大快頤朵,令人拍案叫絕。

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
只因誤識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
——宋·王淇《梅》
王淇是南宋末年不見經傳之人,一生留給後人的詩,也只有兩首。除了這首《梅》詩外,尚有一首《春暮遊小園》:“一從梅粉褪殘妝,塗抹新紅上海棠。開到荼蘼花事了,絲絲天棘出莓牆。”
這兩首都被選入舊時啓蒙書《千家詩),似乎可以和唐代張若虛“孤篇橫絕,竟爲大家”相比美,在文學史上是比較罕見的。
“不受塵埃半點侵”,以物喻人,盛贊梅花的高潔,絕非其它花卉可比。時值冬春交替之際,梅花在嚴寒中開放,“萬花敢向雪中出.枝獨先天下春”,潔淨、美麗,不受塵埃的沾染,這是怎樣的一種品格!
梅花率先開放,預報春訊,不受汙染,潔身自好,做人不也應該如此嗎?
次句“竹籬茅舍自甘心”。緊承前意,再贊一筆,寫梅花所處的環境,甘心淡泊,不計得失。梅花不論是植于何地,竹籬之旁也好,茅舍之前也罷,它都照樣生長,屆時開放,絕不計較處境,默默地向人們獻出美麗與清香。
這又是何等自我犧牲精神!梅花如此,一些安貧樂道、不爲名利所動的人,不也同樣是如此嗎?這裏的“自甘心”三字,視無情爲有情,暗示讀者,他是在借物喻人,不僅僅是在贊揚梅花。
“只因誤識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據《宋史·隱逸傳》記載:林逋早年浪迹江湖,後歸杭州,隱居在西湖孤山的梅嶺上,二十年不涉城市,終身不仕亦不娶,種梅養鶴,人稱“梅妻鶴子”。
其《林和靖詩集》有詠梅詩十首左右,名聯“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被譽爲蓋世佳句,極受歐陽修、司馬光等人的稱贊,王十朋甚至說:“暗香和月入佳句,壓盡千古無詩才。”姜夔則用“暗香”、“疏影” 爲詞牌,演繹成兩首詠梅長調,頗受好評。
如果梅花不與林和靖相識,受到他的稱頌,寫出了傳世名句,恐怕也不會有今天的地位吧?作者之所以正語反說,是采用“反言見意”的手法,欲揚先抑,寓莊于諧,這樣能夠使詩句橫生妙趣,收到從側面贊揚林浦的藝術效果。
小詩構思精妙,立意新穎,語言生動,韻律和諧,用擬人手法,以反語出之,以別開生面,富于情趣而取勝,在詠梅詩中,當稱名作。

養雞縱雞食,雞肥乃烹之。
主人計固佳,不可與雞知。
——清·袁枚《雞》
袁枚論詩主張“性靈說”,所以他的詩中有許多是寫“性情遭際”、風花雪月之作的,妨礙了對于國計民生的重,只是率意爲之。大題材的反映。但這並非說他作詩不認真,平心而論,他在創作上還是很嚴肅的。
他的詠物詩《雞》雖然它只有四句二十個字,而且通俗易懂,但卻是深入淺出的精品。前兩句說,雞的主人放任雞大吃飼料,不加展制,是爲了讓它迅速增肥煮來吃。
後兩句接著說,主人這計策固然很巧妙,但必須瞞著雞,要是讓雞知道了,計策就不好使了。
以雞爲題材的詠物詩並不罕見,但一般都是從雞的本身特性落筆來寫,如唐代詩人崔道融的同名詩:“買得晨雞共雞語,常時不用等閑鳴。深山月黑風雨夜,欲近曉天啼一聲。”,就是利用公雞能啼鳴的特性抒情議論的。
而袁枚這首詩卻從養雞人的角度做文章,把他寫成一個善于“吃小虧占大便宜”的陰謀家。顯然是以寫養雞爲比喻,諷刺社會上那些專門以小恩小惠誘人上當的爲富不仁者。
有的注釋家認爲,此詩“以養雞爲喻,意在揭露封建時代剝削者對待勞動人民施用小恩小惠以求大利的欺騙伎倆”。
生活在所謂“乾隆盛世”的袁枚,是否有這樣深層次的認識姑且不論,但袁枚這首詩的諷刺矛頭,顯然是和封建統治者一貫堅持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格格不入的。
封建統治者把治理百姓視爲“牧民”,就是把老百姓當作牛羊來放牧,要他們唯命是從的。如果讓他們了解“牧民”的實質即剝削與壓迫,自然不利于維護封建統治。
所以封建統治者總是美化自己,給自己臉上貼金,如把皇帝稱爲“天子”,是“奉天承運”統治人民的;把府、州、縣等地方官稱爲“父母官”,似乎那許多貪贓枉法、魚肉人民的官僚,都是“愛民如子”的清官、好官。
乾隆、嘉慶年間許多正統派詩人,都把袁枚視爲詩壇的“野狐禅”。從這首詩看來,“野狐禅”也有可貴的地方,而並非毫無是處的。

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不妥,聯系立即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