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丁茜雯 編輯 | 範志輝
“求你們別上趕著當牛馬了”。
5月20日,“別把志願者當成免費勞動力”、“某些演唱會志願者實爲低價兼職”兩個熱搜的出現,經由央視網及諸多地方媒體的參與,再度將演出市場的志願者服務推上風口浪尖。
隨著今年演唱會、音樂節持續高溫,志願者群體也大有供不應求的迹象,且頻頻爆發出更爲密集的中途跑路行爲,甚至廣發社交平台呼籲網友避雷。
比如上周末結束的王栎鑫北京演唱會、在五一期間結束的鳳凰傳奇鳥巢演唱會、時代少年團演唱會、4月舉辦的揚州七河八島音樂節等,均成爲散落在社交平台上備受吐槽的志願者“避雷”貼。

那麽,作爲演出市場中相對特殊的置換型人力資源,志願者爲何開始“避雷”音樂節、演唱會了?
志願者們圖什麽?近兩年演出市場如火如荼,也令一票難求的現象愈加頻繁。
僅在今年第一季度,全國2000人以上的大中型演唱會、音樂節近200場;五一假期,也有超過30多場音樂節、近40場演唱會在全國各地上演。
與此同時,搶票難、門票貴等問題也讓還在象牙塔中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望而卻步。在這種情況下,投身演出志願者服務崗位也被看作是“曲線救國”的絕佳選擇。
一般來說,面向社會公開招募志願者主要爲人力資源外包、主辦方招募兩種方式。
其中,演唱會志願者則多數由外包公司組織負責,人數需求相對較高。比如五一期間,鳳凰傳奇北京鳥巢演唱會便通過人力資源管理公司“歌華時代橋”進行志願者招募工作,而五月天、五條人、棱鏡樂隊等藝人演唱會也同樣通過這家公司進行志願者補充,該公司也是去年引起負面熱議的“五月天演唱會志願者夥食”、“五月天演唱會志願者待遇”熱搜的招募方。據五月天演唱會志願者透露,僅在去年,歌華時代橋通過鳥巢場所招募的單一場次志願者人數就高達1800人左右。
不同的是,音樂節則普遍爲主辦方自行招募、篩選、分配、培訓,需求人數也因音樂節規模浮動,但大多規模超過百人。比如即將在5月18日、19日舉辦的珠海草莓音樂節,便在近期公布招募志願者超過200人,去年福州說唱巅峰對決音樂節兩日演出招募志願者共406人。

年輕一代作爲如今音樂節、演唱會主要消費群體,同樣也與志願者人群有所交叉。
曾前後參與過五月天、鳳凰傳奇、草莓音樂節等多場演出活動志願者的大學生“黃油”提到,不管是演唱會還是音樂節,志願者都是沖著通過體力勞動換取入場券,“這是一種相對公平的交換,我們付出勞動換取免費入場的資格”。
也正由于對時間、體力有著較高的需求,年輕人也成爲演出市場招募志願者青睐的選擇,“不誇張說,幾乎所有演出都喜歡要大學生,因爲年輕有力氣、時間充裕、好支配,鮮有社會人士入選的”。
站在主辦方角度來說,志願者版塊也是免費的一次傳播推廣機會。通常情況下,出于距離、年齡等考量,志願者招募會面向周邊大學校園、本地人優先,而這種大型演出的參與活動也借由官方、本地生活媒體、校園媒體等進行公開,輻射人群遠遠高于其原有的受衆人群數量。

同樣的,志願者也是演出主辦方節約成本的最優選。
僅一場音樂節,便需要文攝、機動、藝人接待、後勤、檢票等數十個組別分工合作,多達百人團隊的需求也意味著一筆不小的人力開支。即便是演唱會,也因場館龐大、人數衆多等需求,設有座位接待、包廂接待、檢票等工種。
黃油向音樂先聲算了一筆賬,“比如五月天演唱會外包志願者招募有補貼的情況下是一天40元到80元左右,假設這場有200人領隊、1600人是普通志願者,就需要8萬元左右;而且演唱會還會有包廂接待志願者,硬性要求是漂亮、高挑的女孩子,還需要自備高跟鞋、絲襪、化妝,不得戴眼鏡,但提供補貼非常可觀,大約是不到300元一日。”
他也提到,即便有所補貼,“但藝人單位付給外包公司的人力費用也遠遠低于非志願者形式的小時工、日結工結算。因爲大多數情況下,很多志願者就是爲了沖著免費看演出來的,可以選擇不要補貼或是不要觀演,而檢票口的志願者通常是看不上演出的”。不僅如此,在志願服務期間所産生的住宿交通費用,也普遍爲志願者自行承擔,少有交通補貼。

此外,深入了解、參與演出組織的志願者,也承擔了一定的社交宣傳作用,這對于音樂節、演唱會而言,也是二次傳播、建立口碑的有利因素。
比如五一期間,天津泡泡島音樂與藝術節、北京草莓音樂節等便經由志願者在社交平台所發布的經曆總結,成爲諸多樂迷回味、發現意外入鏡,以及感謝志願者幫助的限定“小確幸”。參與天津泡泡島音樂與藝術節的志願者“雪子”便將泡泡島稱爲“烏托邦”,其也發文提到作爲交互組志願者組長的工作內容、舞台搭建過程,爲樂迷提供了另一個直觀了解泡泡島音樂與藝術節的視角。
當然,由于演唱會、音樂節分工存在著一定差別,志願者所參與的內容也不僅僅是關乎于檢票、接待等,甚至還可能成爲場內攤主的免費“小工”。
曾在某音樂節中“串了兩天香腸”的樂迷“戴安”就提到,由于攤主缺少幫工借人,其與另一位原爲官方飲品售賣點志願者的女生便被“借調”去烤腸攤。“我們也沒有辦理健康證,只是隨機性被領隊給到了攤位,攤主對我們抽空去上廁所、吃午飯還非常不滿,可我們也不像其他組有輪休換人”。戴安也指出,如果不是爲了最終能夠看到想要看的演出“第一天串香腸的時候,就想跑路了”。
不僅如此,除了擁有豐富志願者經驗的人員有機會接觸較爲重要的組別,其他人員分配組別時具有一定的隨機性,這也導致難得能夠看到演出的檢票位置被志願者們敬謝不敏。

黃油指出,“一般分在檢票組工作量較大,很難說有什麽機會去抽空看演出,如果是藝人接待組的話,還能夠提前看到試音彩排,只是不能夠主動與藝人進行合照簽名,否則將會被永久拉黑”。
除了免費觀演的需求外,部分志願者也通過該類大型演出活動獲取志願服務證明,“因爲蠻多大學生都有加學分的需要,又能看演出還能增加學分,所以志願者服務對于大學生來說吸引力更大”。
可以說,本著互換互利的平等原則,志願者人群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一場音樂節、演唱會成功舉辦的重要組成部分,卻也同樣面臨著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苦工遭遇。
爲什麽他們選擇跑路了?今年4月底,昆山時光Classic演唱會曾因拼盤演出貨不對板引起消費者抵制,同樣的,大量“280元一日”、“200元一次”的志願者招募信息也同樣遭到虛假投訴。而這種高價招募志願者的新型騙局也並非個例。

一方面,草台班子、一次性主辦方密集踏入音樂節、演唱會領域試圖分一杯羹,原本是互換平等原則下的志願者服務也愈加變味,逐漸成爲針對大學生的“精美網絡騙局”。
比如在閑魚、小紅書等平台上,明碼標價售賣張信哲、林俊傑、新褲子樂隊等藝人演唱會志願者名額的現象屢見不鮮,且無一不以免費觀演、補貼大額、工作輕松等吸引樂迷,黃牛的密集倒賣也令急于觀演的志願者難免上當。
不僅如此,據音樂先聲所了解,從幾百元到幾千元的“志願者工作證”也同樣成爲一大坑,甚至還能夠通過“充人數”觀演獲取一定的返利。當然,這些所謂的“特殊渠道”也需要上繳一定的押金,從20元至百元不等,押金上崗也成爲志願者服務裏普遍的“騙局”。
黃油表示,這種情況多發于演唱會志願者版塊,”音樂節很少有這種情況,但像是深圳海山日月音樂節就是因爲外包了志願者部分,才出現了收取押金、壓榨志願者只能工作無法看演出,最終結束很多天,執行人員也沒有退押金”。

但他也提到,除了押金外,部分演出還會以防止提前泄露的名義,要求志願者上交身份證、學生證、手機,演出結束後才會歸還,“其實是爲了防止志願者中途跑路。”
曾通過黃牛渠道購買所謂志願者名額的樂迷“小虞”也提及,由于五一期間沒有買到華晨宇日出演唱會門票,便在機緣巧合下試圖通過黃牛手中的志願者名額進場,“交了100塊的押金,但當天到崗後,證也是假的,個人信息也被騙走了,錢也沒退”。
據音樂先聲調查發現,志願者招募中的押金詐騙已經成爲普遍現象。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志願者曝光被騙經曆,包括押金難退、繳納培訓費用等。

此外,由于演出市場志願者報名允許個人報名、團體報名,不少高校也與企業達成合作,以學校社團綁定的形式爲演出活動輸送志願者,比如去年張傑、五月天等北京演唱會便出現該種模式。
戴安提到,她在參與學校社團名義下的演唱會志願者活動時,“基本上都能夠被分配到比較好的崗位,也有相對余裕的時間可以換班觀看演出”。不過,社團類型的志願者報名也並非均是如此,同樣也存在學校與企業合作以紀念工作證、學分、志願證明來佐以畢業證明的硬性條件,強制學生投入志願者活動,且工作條件十分彈性。
除了有可能陷入詐騙外,甚至還出現了志願者入選打榜機制。根據不少志願者反映,薛之謙、張傑、周傑倫等藝人演唱會志願者在收到入選通知後,便莫名成爲了“志願者選秀”,需要將含有個人信息的第三方投票鏈接轉發至朋友圈、社交平台等進行拉票,依據投票數確定最終入選名單。
這種方式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爲演唱會、音樂節的宣傳手段,但也令黃牛、詐騙者找到了漏洞,利用該種形式生成虛假活動招募,甚至令暗箱操作也更爲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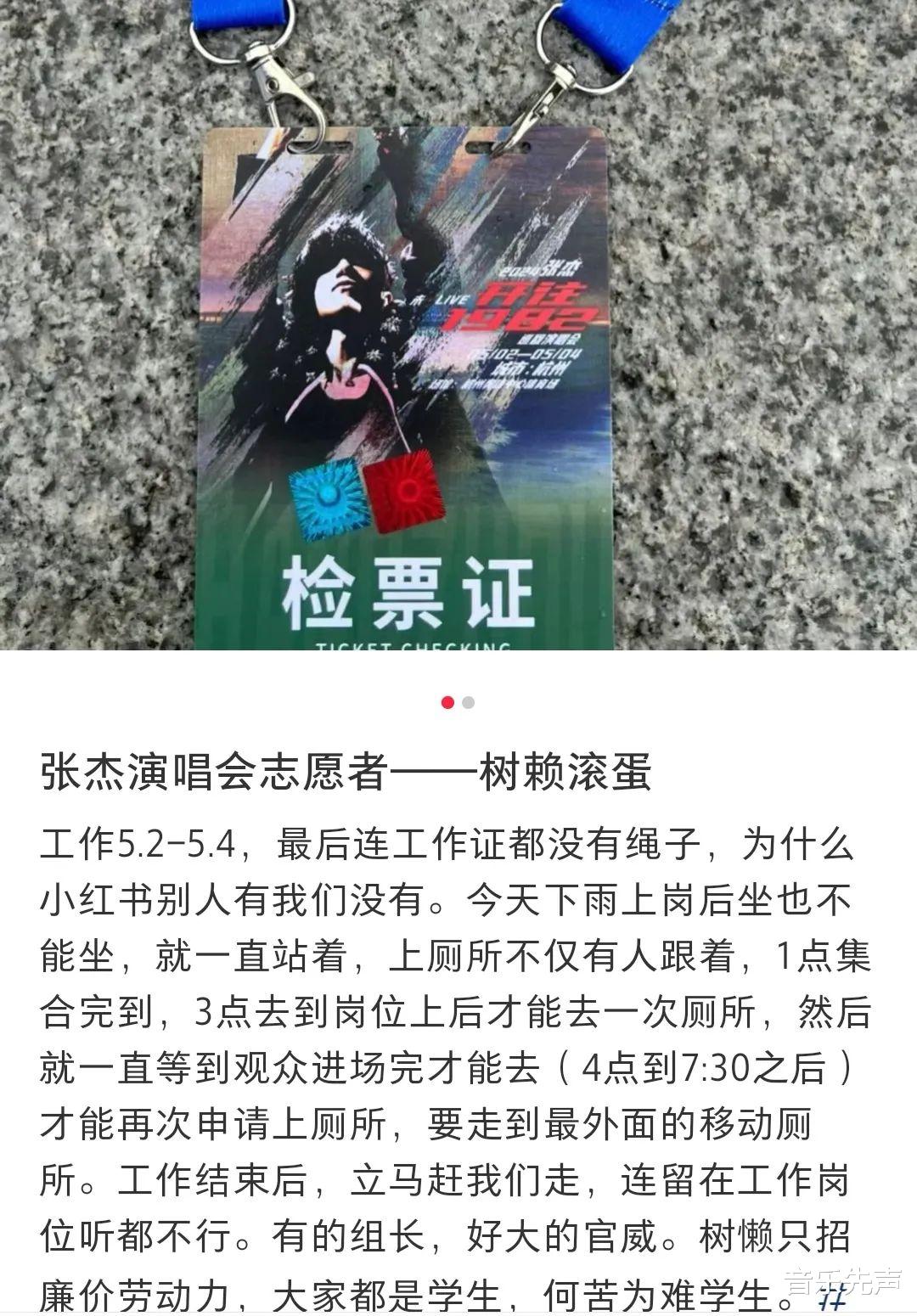
另一方面,諸如小程序“幫忙趣”、公衆號“不會上樹的樹懶”等所謂負責大型演出活動志願者招募的民間組織,近些年逐漸掌握一定的話語權,承接部分演出志願者服務。但據大量樂迷反映,這些招募平台存在著不正規、欺壓志願者,以及經常出爾反爾等問題。
比如通過幫忙趣報名參與志願者招募,需要繳納10元-20元左右押金,退訂則扣除50%手續費,且報名後則被劃分爲A、B、C三個班。對此,黃油也透露,這種押金也類似于“意向金”,“就像預售一樣,如果是在這些平台交上押金報名的樂迷,就不能像單純投遞個人簡曆那樣隨時可以拒絕offer,而押金繳納也能夠以更直觀的人數,幫助平台更大概率成功以中間商身份承接某場演出的志願者服務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志願者招募,其所對應的正規流程本應也是極爲嚴格的。一般來說,主辦方、票務方等均擁有團隊直接負責志願者招募、培訓、上崗等事項,如若委托托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負責,則相關企業需擁有人力資源管理資質。因此,部分活躍在網絡上所謂的民間個人渠道、團體渠道均有著一定的風險性。

同時,志願者服務中所存在的壓榨行爲,已然隨著演出的密集化不再是新鮮事。這其中,志願者也遭受著一定的職場霸淩,不得不因押金、志願證明等涉及自身的關切利益被迫屈服。
比如在4月舉辦的揚州七河八島音樂節,便有志願者發文指出被臨時增加處理散場後垃圾工作,且“不做就沒收工作證、志願證明”;而杭州其綠野仙蹤星巢音樂節也被志願者吐槽“工作人員頂替志願者合影名額,並將私生跟蹤藝人之事甩鍋志願者群體”。
不僅如此,據大量志願者投訴反映,不少音樂節、演唱會志願者還存在著志願者濫用職權、違規交易的現象。比如今年五一期間,湖州凡花音樂節便被曝光志願者以300元一張工作證的價格進行售賣,甚至還出現了志願者工作證換取內場前排、200元帶人進場的荒唐交易。
回過頭來看,演出市場背後的服務體系與受衆消費也是息息相關的,志願者的服務水平也成爲了消費者衡量演出的重要標准之一。畢竟,演出陣容是體驗的重要一環,細枝末節的公共服務同樣不可或缺,甚至影響更直接。
說到底,演出市場産生的巨大經濟效應促使著各路人馬湧入,但監管不規範、組織分工、綜合服務等方面仍然存在的漏洞,諸多亂象也在“鑽空子”的過程中顯露出來。而利益的風,終究也是吹到了流動在各個角落的志願者群體。
*本文圖源網絡,如侵權聯系刪改
排版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