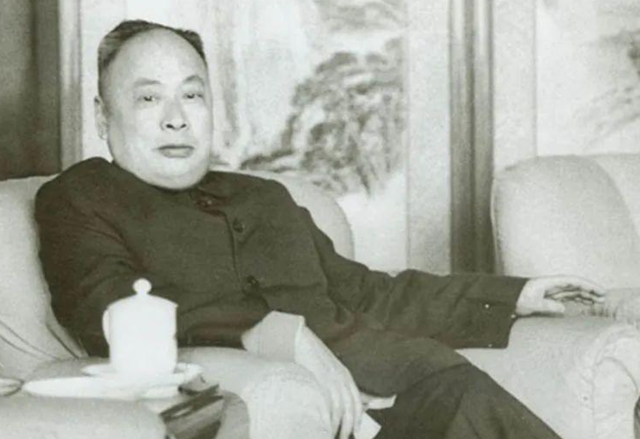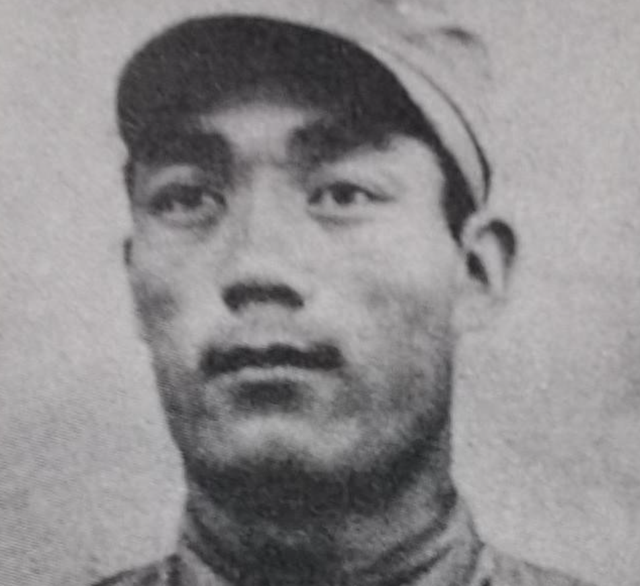繼續連接上一期。
a) 曆史因素。《關于建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的出台,使中國的技術之旅成爲現實(關于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導致成立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開展導彈和火箭研究。錢學森,被認爲是導彈之父和航空航天之父,領導學院。該研究所是一個協調中心,隨後建立了分支機構,這些分支機構將率先研究彈道導彈、地對空導彈(紅旗系列)和機載導彈(海防-2)。導彈和火箭研究被認爲是發展中國空間能力的基礎,特別是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和中國航天科工二研究院的建立。。從導彈發射成功,航天工業開始了長征系列,導致中國擴大了對建造月球探測器、空間站和航天器的進軍。這些尖端技術被認爲是艱難的鬥爭,

因爲從一個工業基礎薄弱的國家,經濟落後的國家,到一個軍事大國。擁有“尖端技術”的技術力量。當然有一個很大的實用主義,而選擇導彈,而不是空中力量,這取決于什麽可以實現與蘇聯的援助和決定模仿蘇聯的R-2導彈作爲蘇聯和中國之間的秘密協議的一部分(六個協議)的一部分。導彈火箭研究的曆史經驗,以及原子彈的爆炸,與准確預測尖端技術的決策勝利密不可分,奠定了中國科技工業的基礎,後來又包括中國的航天事業。最重要的是,領導層爲該國的重要問題提供指導。中國必須專注于與導彈相關的領域,以使其能夠生産尖端技術,例如民用火箭工業,用于所有戰區 (地面,空中和海上) 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反衛星能力等。在1059個項目中,這是第一次導彈試驗的代號,東風 (導彈試驗) 系列開始形成,在1960年11月5日第一次試驗後,中國開始著手各種導彈。
東風 這個名字是毛澤東在小說《紅樓夢》 (東風壓倒西風) 中取的。DF系列代表了中國的彈道導彈分支。第一次測試也重申了中國渴望蘇聯1959年時的技術。導彈和火箭研究代表了獲得技術的戰略以及作爲其戰略一部分的外國合作。盡管緩慢建立其導彈證書的過程權力需要時間,到冷戰後時代,中國已經開始在其彈道導彈中使用固體燃料技術。
b) 軍事因素。核導彈在中國軍事戰略中的重要性在後冷戰時代的巨大變化下。在目睹了海灣戰爭和精確打擊之後,領導層明白,目前的能力不會被對手所取代。可以造成同等損害的常規能力。在尋找答案時,他們發現當時負責核導彈的第二炮兵必須進行改革。雖然中國確實開始向空軍和海軍投入,但 “王牌” 或技術身份將使他們被視爲重要力量,這將是其導彈能力。20世紀90年代,他們開始整合常規和核導彈 (核常兼備),不僅是爲了核威懾,也是爲了戰略威懾。這種雙重戰略成爲一部分第二炮兵的作用,並在21世紀00年代初高科技條件下的軍事戰略指導下得到了加強。這一戰略的證據可以在1995的台灣危機中找到,第二炮兵在那裏進行了第一次威懾行動。台海危機1995年表明,

使用導彈實現其目標引起了人們對中國導彈戰略的潛在關注有限的戰爭也許是導彈能力的展示,在信息戰的條件下,這種將常規和核導彈整合在一起的戰略隨著雙重作戰,雙重威懾” 戰略 (雙重作戰,雙重威懾)。這就是分析美中戰略穩定的分析師看到核糾纏問題的地方。有時,混亂可能導致升級爲核武器。然而,中國人並不分離這兩個; 關鍵是要把各種類型的導彈變成一個可以同時做這兩件事的戰鬥系統,比如發射常規導彈,而不是爲核反擊而戰。早些時候,並不是所有的旅都裝備了雙重角色,但從21世紀00年代初開始,導彈旅就已經具備雙重能力。作爲最近的一個例子,DF-26具有雙角色的能力。可以對對手進行精確打擊的DF-17高超音速滑翔是某系統的一部分,該系統必須執行任務,核反擊,精確打擊和戰略威懾。
結論:曆史和軍事因素形成了一種技術身份,中國的導彈力量需要得到保護,例如,比中國開發的任何其他平台都多的是導彈現代化促進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伊恩·伊斯頓 幾乎將這一戰略稱爲 “基于項目” 的戰略,即中國選擇使用此類技術,而美國則使用基于平台的技術。他斷言由于平台劣勢,財務負擔和地理優勢,中國人采取了這一戰略,但是,事後看來,中國似乎選擇了基于彈丸的戰略來對抗美國。曆史和技術因素表明,當需要與蘇聯合作開發尖端技術時,導彈工業似乎是這種合作的選擇。蘇聯願意提供技術援助,並看到在更廣泛的技術發展中更具影響力。當然,由于資源有限和工業基礎薄弱,空軍在這一雄心中排在第二位。20世紀80年代,當中國精英開始認真考慮威懾和導彈的生存在美國核第一次打擊下,這種選擇導彈力量的政策仍然存在,
因爲技術身份已經確立,因爲它多年來建立的組織 (航空航天) 的實力與其他人。特別是在冷戰之後,當常規能力必須提高時,常規導彈被添加爲精確打擊的王牌。即使在中國經濟取得巨大增長之後,隨著空軍和海軍的能力,中國軍隊的戰略威懾依賴于其導彈力量。事實上,美國正在努力通過獲得這些技術的技術優勢來應對中國的導彈和火箭力量,從而實現更廣泛的戰略穩定。美國。換句話說,有一種努力迫使美國放棄基于核武器的冷戰戰略穩定,接受更廣泛的安全合作框架。對于這種努力,基于平台的設備力量是不夠的,因爲中國將無法實現所需的技術優勢與美國談判。此外,中國決策者將重點放在導彈防禦上,而不是其他許多美國技術專長上的反應,表明了對其在王牌技術中獲得技術優勢的戰略成功前景的擔憂盡管導彈防禦系統對其核武器能力的有效性尚不清楚,

但它反對部署這些防禦系統。此外,由于它可能會降低其第二次打擊能力,因此應該強調更先進的核導彈 (DF-41這是唯一一個致力于導彈防禦的導彈),而不是跨越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高超音速導彈的廣泛發展。因此,中國似乎不一定反對,因爲導彈防禦會影響其核威懾的有效性,許多專家這對美國來說是很難實現的。但這影響了其戰略威懾的效率。
有效性還是效率?中國的打擊能力和技術優勢。中國正試圖加強其二次打擊能力,如可靠性和生存能力。它對導彈防禦的擔憂迫使它發展具有穿透能力的導彈誘餌等對策。當研究認爲導彈防禦破壞了中國的核威懾時,他們認爲其威懾的有效性在導彈防禦下受到了損害。換句話說,中國在吸收第一次打擊後進行打擊的能力罷工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因此,它設想了一種核形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沒有能力對自己的國土進行損害限制,因爲他們剩下的導彈可能會被導彈防禦系統所抵消。因此,術語 “有效性” 表示結過對其核威懾能力的定向分析。這種評估雖然滿足了安全困境的理論,但高度懷疑其准確性,特別是在評估中國希望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使用核武器能力的方式導彈防禦。該評估在列出Chineseconcerns時令人滿意,這與中國的評估相關,
這些評估顯示出對與導彈防禦相關的各種技術及其增強美國進攻性常規技術的擔憂能力。這些擔憂中有許多是由于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開放性以及它在中國人的意圖中造成的不確定性所致。盡管中國人認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對繼承人的核威懾不容忽視,並以發展導彈防禦對策和MIRV能力作爲回應,nuclear45和常規導彈的多樣化顯示出反對導彈防禦和加強 “核-常規融合” 戰略的方向。我認爲,中國認爲它對美國軍事優勢的威懾姿態的效率受到影響。盡管中國認爲可靠和有保證的核威懾足以對抗美國,但證據表明,中國傾向于實現定性而非定量的對等。在這個例如,可以通過獲得技術優勢來實現質量上的均等。這種技術優勢與其保護技術身份的願望相稱,並且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與其威懾態勢相稱。它的軍工複合體,從開始就得到了高層支持要求它維持這一進程。
此外,導彈和火箭技術的綜合性將補充其保存資源以對抗美國的需要。威懾態勢是爲了與美國創造一種戰略穩定,在這種穩定中,質的對等可以推動美中兩國的共同脆弱性。比如說,長征系列和相應的民用試驗幫助其軍隊提高了導彈和反導彈能力。此外,更廣泛的導彈身份挑戰了美國保護其亞洲盟友的能力。
中國對導彈防禦的看法。這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爲,中國只是在對美國放棄限制其導彈防禦部署的核姿態變化做出回應——無法解釋更廣泛的軍事回應(比如增加常規導彈)。他們把它歸因于中國規劃者的條件,而不是理解或誇大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技術細節。第二個學派認爲,中國無論如何都會做出改變,不管美國有沒有導彈防禦系統。【未完待續】請繼續關注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