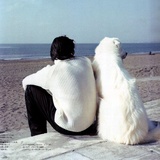在古代,有一句老話常常被人調侃:張飛和嶽飛,殺得滿天飛。
明明他們之間相差了幾千年,怎麽會相遇在一起打架呢,這句話又是怎麽傳出來的呢?

«——·故事發生的序幕·——»
在舊時嘈嘈雜雜無奇不有的川劇舞台上,還真有過那麽一段稀奇古怪又古怪稀奇的天方夜譚式龍門陣。

話說清末光緒年間,建昌(今四川西昌)總兵劉士奇生日,全城文武官員與之祝壽,于城內北街建生祠並演戲相賀。是日,大擺宴席,衆賓敬酒稱壽。
戲班班主跪請點戲,劉總兵乃一介武夫,不通經史,又兼酒醉,信口亂點《張飛殺嶽飛》,衆人雖知其妄,卻不敢駁。班主深感爲難,到台後與演員們計議再三,無有良策。
幸有一花臉演員挺身而出,立馬捉筆寫出人物、場次,分配角色,邊化裝邊和大家說故事情節,于是,一場戲便開鑼了。

先寫張飛接報關羽死訊,即命部下三日內打造白盔白甲,他要征吳替兄報仇。部下謀反,趁張酒醉刺殺之。張飛死後,天帝憫其忠義,封他爲“桓侯大帝",職司南天。接著,是秦桧、王氏設計,風波亭嶽飛父子遇害。嶽飛父子忠魂也來上奏玉帝,至南天門。
張飛阻擋,斥其身爲主帥當收複河山直搗黃龍迎還二聖,何以大勝金兵後,不去乘勝追擊反而中途班師自投羅網?嶽飛訴說班師實非本意,乃因有金牌道道相催。

張飛斥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況十二道金牌乃是秦桧假傳君命。你不察真假,致使半壁河山淪陷金人,則爲不忠;不顧千萬百姓,陷于水深火熱之中,蹂躏在金人馬蹄之下,則爲不仁;身爲主帥,真假不辨,則爲不智;你既還朝,不該帶嶽雲、張憲同歸,以致累及女婿、兒子同遭殺身之禍,則爲不慈。你不忠、不仁、不智、不過是一名愚忠的冤魂。”

嶽飛聞言不服,反唇相譏:“你不以蜀漢大局爲重,只重關公遇害私仇,強令部屬三日造成白盔白甲,酒醉之後鞭撻士卒,以致造成自己殺身大禍,先主猇亭敗迹,蜀國元氣大傷,是誰之罪?”
兩人鬥嘴,相持不下,于是舉槍大戰,殺得難解難分……這,就是蜀人口語中所謂“張飛殺嶽飛,殺得滿天飛”。
«——·關公戰秦瓊·——»
一折嘻嘻哈哈的古事“戲說”式鬧劇,頗近于當年侯寶林相聲中的“關公戰秦瓊”,荒誕不經,供人開懷而已。不過,倘若單就劇中人唇槍舌劍的對話來看,此戲嬉笑怒罵卻也自成文章,荒誕結構的背後並非全無寓意藏焉。
也就是說,它不似純屬戲班中人臨時應景胡編亂造之作,倒象是出自那些有一肚皮不合時宜的讀書人之手。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反正這段梨園轶聞已被今人輯入《川劇志》。

掌故歸掌故,俗語歸俗語。“張飛殺嶽飛”這句話直到今天仍活躍在民間口頭上,常常被人們借來譏諷那些講故事編戲劇不明史實、混淆時代、張冠李戴的信口開河者。
由此聯想到現今諸多借曆史題材創作的影視劇,在這些作品中,不知是因編導粗心還是識淺,前代人操後世語、後世事見前朝文的現象總是屢杜不絕,以至常常有明白人嗤之以鼻,奉上一句“張飛殺嶽飛”,更有不甘被愚弄的觀衆憤然撰文投書報刊抨擊之。
寫作之余,閑坐浏覽古典戲曲腳本,不意間發現這“張飛殺嶽飛”居然古來有之。
«——·流傳出諺語·——»
一首《長恨歌》從白樂天筆下誕生以來,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成爲文人騷客吟詠不盡的題材。這方面劇作,尤以《長生殿》爲明清戲曲中的佼佼者。
該劇末折《重圓》有道:“不知天上宮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劇中“生”是玄宗皇帝,“淨”爲道士楊通幽。稍具古典文學知識者皆知,此引數句實乃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寫于中秋月夜的《水調歌頭》詞中句,今赫然自唐人口中吟出,豈非咄咄怪事。

宋人詞被唐人誦,那麽,唐人典也能被先秦人用。元雜劇<伍員吹箫》第四折伍子胥唱:“想著俺蓋世雄骁,函谷關前看鬥寶。只爲一時窮暴,卻教俺丹陽市上學吹箫。誰承望淩煙閣重把姓名標,兀的個殺人場還許冤仇報……”
伍子胥乃春秋時期楚國人氏,而淩煙閣則是唐朝太宗皇帝專門建來爲有功之臣畫像的地方,二者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據《曆代名畫記》卷九載,貞觀十七年,著名畫家閻立本奉诏畫《淩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舊唐書》卷七十七《閻立德附弟立本傳》也明確寫道:閻立本“尤善圖畫,工于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淩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鹹稱其妙。”言之鑿鑿,不容置疑。

“淩煙閣”典故,又見于取材漢代昭君出塞故事的元雜劇《漢宮秋》,這次竟赫然出自堂堂漢家皇帝之口:“我則恨那忘恩咬主賊禽獸,怎生不畫在淩煙閣上頭?紫台行都是俺手裏的衆公侯,有那樁兒不共卿謀,那件兒不依親奏?爭忍教第一夜夢迤逗,從今後不見長安望北鬥,生扭做織女牽牛!”
類似“唐典漢用”的現象在<漢宮秋》中非僅此一例,如第三折灞橋餞別時,皇上戀戀不舍地舉起酒杯對明妃唱道:“你將那一曲陽關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捧玉觞……”
此所謂“一曲陽關”,典出唐代大詩人王維那有名的送別詩《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詩曰:“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該詩脍炙人口,于唐代就十分有名,流傳甚廣,許多詩人都曾提及它,如“最憶陽關唱,珍珠一串歌"(白居易《晚春欲攜酒尋沈四著作》),後人又進而敷演爲“三疊歌之”(《麓堂詩話》),元散曲中即有無名氏的《大石調·陽關三疊》。

細心檢視古典戲曲文本,你會發現類似現象多矣,連名家、大家亦不免。講西漢蘇武牧羊故事的《牧羊記》唱詞雲“楊六郎把住三關口”,說東漢蔡伯喈夫妻故事的《琵琶記》唱詞曰“我好似小秦王三跳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搞了半天,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兒呢?
會不會是古代劇作家缺乏文史常識呢?回過頭來認真想想,恐不盡然。中國古典戲曲向來重寫意抒情而不太計較肖實敘事,寫戲者但求達意暢快,遣詞造句隨手拈來,猶如當年蘇東坡以朱筆畫竹,信手爲之,求的是意氣宣泄暢達,得其神韻往往不免略其形迹。

再說,這些個詩詞、典故流傳世間而早已爲大衆百姓耳熟能詳,借之人戲既拈來方便又極容易得到觀衆(要知道,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都是識字不多文化有限的“下裏巴人”)認同接受,這也符合戲曲面向大衆之俗文藝本性;而看戲者只圖一時看得過瘾,走出劇場恐怕少有人會去咬文嚼字,有點象演講術,重要的是當場情感打動而不是事後邏輯思考。唯其如此,前人對之往往也就不以爲忤,少加追究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對于曆史劇創作,上述例子盡管是璧中之瑕,毛中之疵,今天的戲劇乃至影視創作者仍當引以爲忌,避而遠之才是。
也就是說,古有古的道理,今有今的規矩,我們沒必要在兩者之間強作攀比,也不必借古代人替現代人開脫而強詞奪理。今天,在理性發達和觀衆文化修養、接受水平普遍已高的今天,我們的大編劇大導演們恐怕還是該老老實實尊重曆史,在熒屏及舞台創作中少鬧這類“張飛殺嶽飛”式的笑話爲好。

不管怎樣,這些故事都是讓我們重溫曆史永雄事迹的一種特殊方式,我們要謹記,不要忘記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