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黃巾起義的打擊以及伴之而興的地方州郡勢力的崛起,東漢王朝面臨嚴重危機,一些有識之士如鄭太、橋玄等已認識到,漢政權搖搖欲墜,國將大亂。在此背景下,東漢末年至少出現了三次廢立皇帝的圖謀,但均以破産告終。
漢陽大族閻忠勸皇甫嵩廢漢自立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皇甫嵩以車騎將軍身份領冀州刺史,因平定黃巾起義之需,手握重兵,威震天下,下屬遂擔心其有功高震主之嫌,勸其廢漢自立。
《後漢書・皇甫嵩傳》載,信都令漢陽閻忠規勸皇甫嵩曰,“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因此主張汲取韓信毀滅之教訓,廢漢自立:“今主上勢弱于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吒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征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于前,大軍響振于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罴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于將興,推亡漢于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阪走丸,迎風縱棹,豈雲易哉?且今豎宦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閻忠是漢陽大姓,在涼州有很高的聲望。
由“庸主”“勢弱”“權重”及後論“衰世”“豎宦”等用語可以看出,閻忠認爲當時東漢朝廷深陷多種危機,皇權失墜,無法複興:皇帝乃昏庸之主,威權喪失;州郡長官掌握軍政大權,中央權力受到削弱;宦官專權,流弊難革;朝廷乃朽木,難以輔佐。因此,閻忠以韓信爲誡,苦苦勸說立有軍功的皇甫嵩廢漢自立以自保,並爲其擬定了廢漢步驟:“功業已就”—“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換言之,要因時而動,建功立業,宣示天命,一統天下,廢漢稱帝,而這些不過是“推亡漢于已墜”而已。
對于閻忠這番激動人心的勸說之辭,皇甫嵩不僅不欣喜,反而愈加恐懼曰:“非常之謀,不施于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雲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皇甫嵩不願也不敢采納閻忠之論,認爲此乃“非常之謀”,廢漢自立乃謀逆之大罪,與其招亡速禍,不如堅守“臣節”; 即便深陷讒言,也不願僭越君臣之綱。可見,皇甫嵩對東漢朝廷和自身有著清醒的認識,對君臣之關系有著深刻理解。其後,皇甫嵩由征西將軍升遷爲車騎將軍,再至太尉,足見朝廷對之倚重和重用,有效化解了皇甫氏之疑慮。

皇甫嵩
作爲地方大族的閻忠以汲取韓信的教訓爲由,勸立有軍功的皇甫嵩廢漢自立,至少可以與東漢劉氏平分天下。若閻忠所謀得以實現,則將開東漢以軍功篡權自立之惡例,自秦漢開創的大一統帝國,至此將再次陷入分割、分裂之危機。
冀州刺史王芬等謀廢漢靈帝立合肥侯漢靈帝光和末年的黃巾起義,使東漢王朝遭受重創,出于平叛之需,被迫下放部分權力,“改刺史,新置牧”成爲其標志性事件。但伴隨著地方州牧勢力崛起,東漢末愈發呈現外重內輕的趨勢,中央與地方關系惡化。在此背景下,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年)出現了地方長官與地方豪傑聯合謀廢皇帝之事。
《三國志・武帝紀》載:“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該史料透露出如下信息:其一,主謀身份特殊。冀州刺史王芬爲冀州最高地方長官,南陽許攸爲漢末著名謀士,沛國周旌史載不詳,蓋應與許攸略同,屬于地方名士。其二,衆多“豪傑”參與其中。東漢中後期,“豪傑”具有更爲豐富的內涵,大體包含如下人群:首先,占據地方經濟和壟斷地方選舉的豪族。楊聯陞認爲,所謂豪族,“並不是單純的同姓同宗的集圖,是以一個大家族爲中心,而有許多家許多單人以政治或經濟的關系依附著它。這樣合成一個豪族單位”。
這些豪族在地方上擁有較大能量,半遊離于體制之外,具有某種俠義精神。其次,俠氣張揚的黨锢名士。兩漢之際,遊俠儒家化大體完成,但俠風猶在,黨锢名士和遊俠在舍生取義、自我犧牲的英雄主義人格與行爲方式上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再者,地方長官,亦可謂之地方軍閥。史載,董卓之亂後,“豪傑並起”。這些“豪傑”範圍很大,既包括地方衆多豪族,也包括控制地方大權的軍政長官,如曹操、袁紹等。此外,“豪傑”有時又與“英雄”可以互稱,顯示出“豪傑”行俠仗義、獨立特行的內在氣質。
如袁紹逃奔冀州,董卓必欲除之而後快,侍中周毖等說董卓曰:“袁氏樹恩四世,門世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所引“豪傑”與“英雄”即對稱,含義略同,且前論袁氏門生故吏,則此“豪傑”應多爲袁氏門生故吏,且多豪俠。王芬所聯結之“豪傑”多爲半遊離于體制之外的俠義之士,更多地代表了“社會”的力量,以與“國家”相對應甚至相抗衡。其三,另立合肥侯。合肥侯爲東漢宗室,姓名、官職不詳。與上文閻忠勸說皇甫嵩廢漢自立不同,這次謀廢是從東漢宗室中另擇賢君。其四,曹操明確反對廢立。地方州郡長官與地方豪傑聯合起來,謀廢天子,另立宗室,這是此次廢立圖謀的重要特點。

黨锢之禍
王芬等謀廢漢靈帝,還與東漢中後期士大夫和宦官鬥爭這個大背景密不可分。衆所周知,東漢後期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政局混亂,引起朝野士大夫的激烈反抗,釀成著名的黨锢之禍。《三國志・武帝紀》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曰:“于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芬坐,楷曰: ‘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于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征之。芬懼,自殺。”由此可知,冀州刺史王芬與陳蕃之子陳逸、術士襄楷多有往來,密議國是。
陳蕃爲當時清流士大夫領袖,也是俠氣張揚的黨锢名士,得到太學生擁護,在第二次黨锢之禍中慘遭宦官迫害致死,其門生故吏遭禁锢。其子陳逸深受乃父影響,對于宦官專權深惡痛絕。“術士”利用天象預言將不利于宦官,黃門常侍等要遭滅族之禍,這對于深受宦官專權之害的士大夫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容錯過的絕佳時機,王芬等遂決意行廢立之事。由此可見融合方術、天文等在內的谶緯神學對東漢政治的影響。此次謀廢漢靈帝的參與人,除主謀者和衆多“豪傑”外,還有黨锢名士、術士等。他們爲滅宦官,而行非常之謀,欲趁漢靈帝北巡河間舊宅之際,起兵作亂。但其後漢靈帝聽從太史之言,未北行,故王芬等圖謀未能實現。
王芬等謀劃廢立之事時,曾拉攏曹操一同起事,但遭拒絕。史載,王芬等“以此謀告曹,蓋亦知操之爲時雄矣”。《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載曹操拒王芬之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睹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 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曹操認爲,廢立天子之事乃不祥之兆,事關重大,需慎之又慎,並以伊尹和霍光爲例,說明廢立之事發生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認爲被立之君的品行與威望、輔政大臣的忠誠與智慧等,都是決定廢立成敗之關鍵。但現在這些條件均不具備,王芬等“結衆連黨”,合肥侯沒有威望,此時行廢立之事,不過是徒增亂局而已。曹操推崇伊尹和霍光等輔政大臣之舉,而反對輕言廢立君主。曹操對于此次廢君行爲之看法,可視爲漢獻帝建安年間他挾天子以令諸侯、但終爲漢臣的心理基礎。
王芬還曾私下招誘華歆等商議,也遭到拒絕。《三國志・華歆傳》載:“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華歆以伊尹、霍光之舉爲例,認爲廢立大事,需要忠誠與智慧,遠非王芬等地方豪強所能及,因此拒絕與之合作,並力勸陶丘洪不要參與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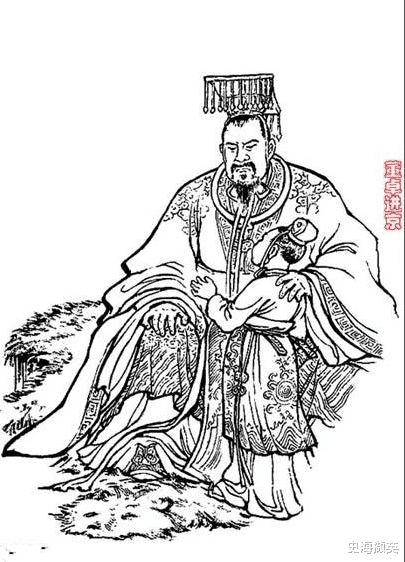
劉宏
由此可見,冀州刺史王芬等廢立漢靈帝之圖謀,根本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其失敗在所難免。漢靈帝雖然無道,但作爲東漢朝廷的皇統所在,對地方州牧的冒險行爲仍是極大的震懾。不過,王芬等謀廢漢靈帝作爲一次非常嚴重的謀反事件,對東漢君臣關系勢必會産生嚴重的消極影響,將刺激其他冒險之徒行铤而走險之事。
袁紹、韓馥謀廢漢少帝而立宗室劉虞袁紹爲渤海太守時,曾與冀州刺史韓馥謀廢漢少帝而立劉虞。袁紹出身于名門望族的汝南袁氏,門生故吏遍天下,在地方上具有巨大影響。劉虞爲漢室宗親,長期駐守幽州,和洽戎狄,安撫百姓,威信很高。《三國志・公孫瓒傳》載:“袁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于奸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袁紹與韓馥謀議的時間,當在董卓入洛之後、廢漢少帝立漢獻帝之前。漢少帝時爲董卓操控,所謂“制于奸臣”,即此之謂,故有袁紹、韓馥廢漢少帝立劉虞之議。
有關韓馥之所爲,《三國志・公孫瓒傳》注引《吳書》記載稍詳:“馥以書與袁術,雲帝非孝靈子,欲依绛、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雲:‘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谶》雲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于代郡,謂虞當代立。”韓馥在與袁術信中,表示欲與袁術共行代王故事。所謂“代王故事”,指西漢绛侯周勃與颍陰侯灌嬰,鏟除呂氏勢力,廢除少帝,迎接代王劉恒即位,是爲漢文帝。“代王故事”的實質是權臣掌握皇帝的廢立。
韓馥等謀廢漢少帝而欲立宗室劉虞,盛贊劉虞功德治行皆佳,並列舉了一系列劉虞當爲天子的谶緯事件:劉秀五世而據河北、中興漢室,而劉虞亦五世而據幽州,當能再次複興漢室;《谶》言當有神人出自燕地,而劉虞恰爲幽州牧;神秘玉印“虞爲天子”現于民間,則公開宣揚劉虞爲天子;兩日同時出于代郡,暗示天下將出現新天子。韓馥爲勸劉虞稱帝,多引謠谶爲證,可謂頗費心機。韓馥與袁術通信時,袁術所任之官職爲董卓加封的後將軍,但頗懼董卓,故韓馥此舉有裏應外合之意。其後,袁紹給袁術寫信時,表明廢漢少帝而立劉虞之鮮明態度。袁紹與韓馥事先私下密議,其後二人又先後致信于袁術,顯然二人對袁術寄予厚望,希望借助袁術之力達到廢漢少帝立劉虞之目的。但是,袁術又有自己的私心,不願意附和立劉虞之議,汝南袁氏的政治動向值得關注。
盡管韓馥、袁紹竭力勸立,但劉虞不爲所動。《三國志・公孫瓒傳》注引《吳書》:“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于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面對袁紹等勸進之議,劉虞堅決拒絕,認爲“國有正統”,作爲人臣不應僭稱帝號,否則就會亂了“正統”。“正統論”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的重要觀念。

劉虞
宋代歐陽修認爲:“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此實則較多地含有居天下之中、一統天下之意。劉虞“國有正統”之語,爲中國古代典籍中較早提出“正統”一詞者。劉虞所謂“國有正統”,意爲當時有正統之君,即便漢少帝爲奸臣所挾制,他人亦不宜再作非分之想。劉虞爲躲避反複勸進而竟欲逃亡匈奴,以絕衆望。此後,他在幽州牧任上更加盡職盡責,較好地處理了地方與中央的關系。“國有正統”一語,出自東漢宗室劉虞之口,對韓馥、袁紹乃至董卓等是一個嚴正警告,也是應對謀廢漢帝圖謀的有力思想武器。
因有“國有正統”觀念的存在,曹操反對這種立劉虞而廢漢少帝之舉,史載“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使得袁紹等心有顧忌,不敢妄動。因爲“國有正統”,即使劉虞本人不願也不敢接受勸進之議,史載“虞終不敢當”,“虞不敢受 ” 。 他非但不敢接受,反而痛斥這種僭越行徑。袁紹、韓馥遣使張岐詣劉虞處,使即尊號,劉虞厲聲呵斥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汙忠臣邪!”劉虞痛責勸進之使,認爲此乃玷汙忠臣之舉,現在應行“忠孝之道”,聚州郡義士,“以除國恥”。
那麽,袁紹等爲何執意廢漢少帝而立劉虞呢?實際上,袁紹等立劉虞廢漢少帝之舉,根本不是從天下、國家著想,而是存有一己之私,有其如意算盤。官渡之戰後,曹操向漢獻帝彈奏有關袁紹不臣之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曹操上疏漢獻帝雲:“大將軍邺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雲:‘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雲:‘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征,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玺,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于此。”
由此可知:其一,袁紹與韓馥早年欲廢除當朝天子漢少帝,而立劉虞爲帝,並擅做玺符,宣揚天命之數。其中包括劉虞當爲天子的一系列谶緯事件。其二,袁紹要求曹操將漢獻帝遷都于鄄城,以便于自己控制。袁紹以邺城爲據點,擅鑄金銀印,天下孝廉計吏拜見袁紹,而非前至許都觐見漢獻帝。計吏,又稱“上計吏”“上計掾”,在規定的時間內將本地上計簿送至京城相關部門審核,發揮著聯系中央與地方的紐帶作用。袁紹所作所爲,乃公然藐視朝廷,與中央爭奪對地方的控制權。其三,從弟袁敘與袁紹書信,鼓吹“天意實在我家”,即天命在袁家,袁氏當稱帝。“南兄”指據有南陽的袁術,“北兄”指擁有北方多州的袁紹。
若袁氏稱帝,當非袁術與袁紹莫屬。其始,袁術欲稱帝,進行了一系列努力,宣揚“袁氏受命當王”,失敗後,認爲袁紹年長位重,比自己更有能力稱帝,准備將玉玺送給袁紹,但因曹操阻道未果。不管是袁敘慫恿,還是袁術主動歸皇帝名號,即便袁紹本人也不能否認有稱帝之企圖。曹操所奏袁紹之事發生于官渡之戰後,誠然有落石下井、打擊報複之嫌,但袁紹先期謀廢漢少帝另立劉虞,以便控制朝廷之心亦不可否認。漢末汝南袁氏的政治動向值得關注:袁術先私下僭號,後公開稱帝,失敗後將帝號歸于袁紹,宣揚“袁氏受命當王”;袁紹承接袁術歸還的“帝號”和“袁氏受命當王”的天命宣傳,圖謀稱帝。

公孫瓒
謀立宗室劉虞,反映了袁紹、韓馥等漢末群雄的政治野心。劉虞後來爲公孫瓒所殺,或許從事實上證明,劉虞根本就不爲所謂的漢末豪傑和軍閥所尊重,立劉虞不過是汝南袁紹的幌子而已。《三國志・公孫瓒傳》載,“瓒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注引《典略》曰: “瓒曝虞于市而祝曰:‘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劉虞與公孫瓒在對待胡漢民族關系政策上有分歧,劉虞主張和輯戎狄,而公孫瓒認爲胡人難治,應該征討,二人遂不和以至于爆發公開沖突。公孫瓒汙蔑劉虞欲稱帝而殺之。劉虞聲望很高,公孫瓒殺劉虞時,宣稱劉虞若當爲天子,天當降雨,顯然劉虞被勸稱帝之事已爲時人所知。劉虞最終被殺,可見劉虞被勸稱帝實則是漢末軍閥的陰謀,欲借宗室劉虞之幌子,而行軍閥弄權之實。
由上可知,袁紹、韓馥等廢漢少帝、立宗室劉虞之舉,盡管有客觀實際,如漢少帝爲軍閥董卓脅持,漢天子威權掃地,但這種謀立新君的做法,實際上一仍董卓之舊,由地方軍閥掌握皇帝的廢立,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皇帝權威,並爲權臣控制皇帝再開惡例。
漢末廢立圖謀破産對曹操政治行爲之影響上述所論東漢末廢立皇帝圖謀,曹操的政治態度頗值得注意。王芬等謀廢漢靈帝,曹操拒之;韓馥和袁紹謀廢漢少帝而立劉虞,也遭到曹操抵制。曹操見證了這兩次圖謀由密謀到准備實施及其失敗的過程。閻忠規勸皇甫嵩廢漢帝自立之謀,由于僅僅停留在勸說階段,尚未付諸實施便胎死腹中,不爲衆人所知,因此不得詳考曹操之態度,但可以由曹操的一貫言行而推斷其一定持反對態度。以上三次廢立皇帝之圖謀及其破産,均發生于漢獻帝即位之前,對日後曹操處理自己與漢獻帝之間關系有著重要啓發、刺激和影響。
其一,對待漢天子,“廢”未必成功,“挾”可謂上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策成爲曹操水到渠成的必然選擇。東漢末幾次廢立皇帝圖謀的破産促使曹操充分認識到漢天子的重要價值,因此當謀士建議“奉天子以令不臣”,“奉主上以從民望”時,曹操當機立斷,將漢獻帝迎接至許昌。可見,當時曹操集團的政治口號是“奉天子”,而非“挾天子”,但政治口號重在宣傳和制造輿論,曹操其後確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實。當然,對漢獻帝作用的不同認識,也決定了曹操與袁紹不同的政治取向。作爲當時北方最重要的一方勢力,袁紹集團早就有謀士認識到漢獻帝的政治價值,向袁紹提議將漢獻帝劫持至邺,如沮授“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 不庭,誰能禦之!”
田豐“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以便獲取政治優勢,利于四方平叛。但郭圖、淳于瓊等反對,認爲若迎接漢獻帝,動辄請示,容易造成政治上的被動。優柔寡斷的袁紹最終沒有采納田豐、沮授等的建議。拒絕迎奉漢天子,表明袁紹在內心實已放棄了挽救東漢王朝的努力,已經放棄了蒙塵在外的漢獻帝,自己欲通過武力爭奪而得天下。不過,當得知曹操迎接漢獻帝時,袁紹竟然反悔,欲派兵攔截,以至後悔莫及。這場挾天子都許與都邺之爭,最終以曹操挾天子都許而畫上了句號。

曹操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將漢天子安置于許都後,尚面臨被其他勢力搶走的風險。董卓西北軍的多股殘余勢力,“還想把漢獻帝從曹操手裏搶回去”。曹操北征三郡烏桓時,“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則明確說明劉表遣將偷襲許都控制漢天子的可能性及其對曹操的影響。孫策趁曹操與袁紹對峙時,“陰欲襲許,迎漢帝”。包括袁紹本人,其後與曹操書信雲“可都鄄城,當有所立”,要求將漢獻帝遷都于毗鄰自己勢力範圍的鄄城,以便對漢天子施加影響。這些均從側面說明了當時漢獻帝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價值,也證明當初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政策的正確性。
事實上,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策確實收到了一定效果,如賈诩以“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勸張繡再次降曹,傅幹以“曹公奉天子誅暴亂”爲由勸馬騰不要與袁尚聯合攻曹,而應趁機攻袁。當曹操南征欲討伐孫權時,張昭勸孫權降曹,理由也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有關,故裴松之評曰,“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雖無功于孫氏,有大當于天下”。當然,關于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價值與作用,學術界有不同見解。呂思勉認爲,曹操之所以能有相當的成功,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挾天子以令諸侯,根本沒有多大的關系”。
東晉袁宏評曰: “時獻帝幼沖,少遭凶亂,流離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後生,未有過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懷匡複之志,故助漢者協從,背劉者衆乖,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爲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爲首。”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僅自己的地位高出一切官吏,而且行動也是‘名正言順’,造成了政治上極大的優勢”。從袁紹的後悔之舉、劉表和孫策等的搶帝圖謀來看,挾天子以令諸侯政策對于勢力尚處于發展中的曹操來說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其二,對待東漢帝統,廢漢自立未必成功,終爲漢臣可謂明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後,所面臨最棘手的政治難題是如何處理自身與漢天子的君臣關系,是廢漢自立,還是終爲漢臣。曹操選擇了後者。範文瀾指出,“士族阻礙著曹操代漢做皇帝,與其說是爲了擁漢,毋甯說是向曹操交換做官特權”。田余慶認爲,曹操“怕背千古罵名,不敢做皇帝”。日本學者金文京認爲,曹操“既想當皇帝又怕受非難”。柳春新認爲,曹操未能完成廢漢自立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現實的政治條件或政治實力”,而非司馬光所說的“畏名義而自抑”。曹操終爲漢臣,除了自身政治實力外,還應考慮東漢末地方大族廢立皇帝圖謀之破産對其內心深層次的影響。
一方面,廢立圖謀破産促使曹操實行桓文之舉。桓文之舉的實質是尊王攘夷,在諸侯爭霸的環境下,尊王以維護天子之權威。曹操贊賞桓文之舉,表明其不願廢漢天子的政治立場。曹操贊賞齊桓公、晉文公之故事,在其言行中一再流露。曹操《短歌行》其二雲:“齊桓之功,爲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又如《讓縣自明本志令》雲:“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曹操借此宣誓自己效法桓文,效忠漢室的決心。曹操甚至設立齊桓公神堂,以明其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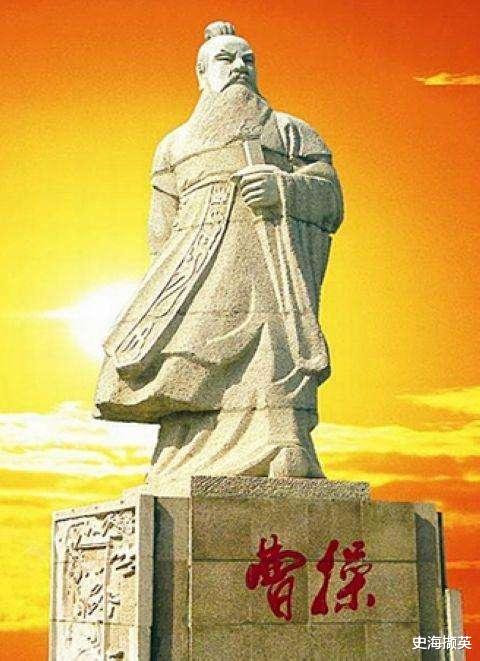
曹操
因此,有學者指出,觀曹操一世所爲,及《拒王芬辭》《答袁紹》《讓縣自明本志令》等文,應該說曹操也還是志在效桓、文之舉,奉事劉氏,複強國勢,實現天下統一的。黃仁宇認爲,“以曹操的希望,還是想保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于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爲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衆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虛名而處實禍’的危機”。
另一方面,廢立圖謀破産促使曹操推崇伊霍之舉。伊霍之舉的實質是盡職盡忠輔佐幼主,而不僭越君臣之關系。王芬等謀廢漢靈帝時,曹操堅決反對,並舉伊尹、霍光之例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意向。從漢靈帝至漢獻帝前期,曹操從內心是推崇伊霍之舉的,其後伴隨著勢力的增強和威望的提升,曹操以漢中央的名義封自己爲魏公和魏王,顯示其逐漸與東漢朝廷分庭抗禮,但當孫權來信勸曹操稱帝、群臣紛紛勸進之時,曹操卻仍雲:“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曹操終其一生未稱帝,其身份仍是漢之臣子,但其爲曹魏政權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由此可見,曹操贊賞桓文之舉,引領漢末割據勢力遵奉漢室; 推崇伊霍之舉,表達永爲漢臣之決心。漢建安年間,曹操勢力雖不斷增強,但最終沒有廢漢自立,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受到了漢末廢立天子圖謀失敗的刺激和影響。

東漢形勢圖
東漢末出現多次廢立皇帝之圖謀,大致可劃爲兩種類型:其一,東漢後期地方豪強勢力崛起,掌握地方軍政大權,對中央皇權構成嚴重威脅,多次冒險欲行天子廢立之事,王芬、韓馥和袁紹爲其代表。冀州刺史王芬等聯結地方豪傑,謀廢漢靈帝,而冀州刺史韓馥、渤海太守袁紹等謀廢漢少帝而立宗室劉虞,實際上仍是憑借地方軍政大權而幹涉皇權的舉動。其二,閻忠勸立有軍功的皇甫嵩代漢帝自立。對于立有軍功、掌握軍政大權的皇甫嵩來說,割據一方甚至代漢自立,也並非完全無望。皇甫氏選擇終爲漢臣,並不能杜絕日後此類圖謀再次泛起並冒險成功。東漢政權的崩潰及其後出現的分裂割據局面,早在漢末屢屢發生的廢立皇帝圖謀中即可見其端倪。
東漢政權的崩潰勢所必然,但漢末地方大族廢立皇帝的圖謀均遭破産。究其原因,當時東漢皇權盡管受到很大削弱,但“國有正統”的大一統觀念早已深入人心,東漢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仍具有強大的號召力,漢天子仍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義,成爲大一統政權崩潰前夕維系各方的一面旗幟,它猶如一條紐帶,制約著各方割據勢力,連接著東漢皇權和帝統,使之不至于完全斷裂。
總之,東漢末地方大族廢立皇帝圖謀之屢屢出現,反映了地方勢力的崛起、中央威權的喪失和君臣關系的惡化; 而圖謀之破産,又凸顯漢天子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價值,“國有正統”的大一統觀念深入人心。廢立皇帝圖謀之破産,成爲制約東漢帝國分裂的重要因素,對當時的君臣關系産生了一定影響,對曹操等對待漢天子的政治態度也産生了一定啓發和刺激,促使其摒棄“廢”天子之念,改用“挾”天子之行,“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爲曹操水到渠成的政策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