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廣陵散,
跨越兩千年,
從嵇康彈到了朱令。
而如今,
曲終人盡花已謝,
一宗懸案無結果。
無人伏法,
無人悔罪,
唯有萬千網友意難平。

2023年12月22日22時59分,朱令逝世,終年50歲。2023年12月24日中午12時,朱令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殡儀館舉行,其中一副挽聯寫道:“朱顔逢劫,令人扼腕,當年謎案留追憶;才女香消,舉世悲歎,此生命運意難平”。對此已近30年卻仍沒有結論的懸案來說,公衆“意難平”是對的,如果公衆對此事都已經“意平”了,那才是更令人絕望的了。朱令被投毒中毒一案,無論在法律程序上是否已經結案,也無論當事人是否已經去世,這件懸案不能就此塵埃落定,也不能就此銷聲匿迹無人追問,反而再次引發網絡大討論,我認爲這是值得欣慰的。因爲追究真相永遠是必要的、值得的。不過,此處的公衆“意難平”可能有兩層含義,其一含義是對真相未能揭露、真凶未能伏法的“意難平”;其二則是認爲真相已經被揭露、真凶已經被證實但卻未能伏法的“意難平”。大多數網友可能處于第二個層面的“意難平”:以最先提出該觀點的貝志城爲主要代表,朱令的同學舍友孫維成爲衆矢之地萬夫所指的嫌疑對象,包括貝志城在內的很多人不僅把她視爲“唯一嫌疑人”,而且下定論她就是凶手了。于是不僅在網絡上出現了針對孫維的大討伐,而且在澳大利亞出現了澳洲華人在當地政府網站投票申請要求當地政府驅逐孫維的行動(見包括鳳凰網在內的多個官媒、自媒體報道)。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網民和澳洲華人是受到自己胸中的一股正義感驅動的。但是,必須要說的是:正義感從來不等于正義。從正義感到正義之間,有一條深刻的、嚴謹的、審慎的邏輯線,任何一處出現了脫線、出軌,都可能導致了非正義。與該“正義群體”相對應的是,網絡上出現以方舟子爲代表的反對方,認爲將孫維列爲“唯一嫌疑人”乃至斷定她就是凶手的觀點是不妥的、缺乏足夠證據的,並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證。見《著名大V在十年前爲孫維寫的長篇辯護詞》、《孫維免費辯護師的最新一組反诘質詢:“貝志城爲什麽要撒謊?貝志城爲什麽不吊唁?貝志城在恐懼什麽?”》及相關文章。于是,針對“孫維是否構成唯一嫌疑人乃至凶手”這一主流觀點,形成了觀點鮮明的控辯雙方:以貝志城爲代表的控方vs以方舟子爲代表的辯方。跨越太平洋、大西洋的網絡法庭再次開庭,這起延續了近三十年的懸案再次成爲各路神探斷案的對象,各位陪審員一一落座。本文並不對此案進行個人判定,只對控辯雙方的觀點提出如下的審慎態度和評判原則:對于控方來說,只要指證的證據鏈中有一處漏洞錯誤,最後的結論就不能成立;對于辯方來說,只要提出的反證中至少有一處是正確的,他的辯護就能成立。即:控方必須鏈條完整、邏輯自洽,一環也不能缺,其論證結論具有唯一性,其指控方能成立;辯方只需要找到控方論證中的至少一個缺口指出鏈條不完整,其反駁便是有效的。如果不能夠接受此原則,或者對此原則有異議,以下內容就不必看了。再次提示:這不是一篇結論性的文章,但這是一篇邏輯推理的開始。(並提示:喜歡看沒藥花園之類文章的朋友,可能看此文會有情緒,但請你們克制,也請理解一下什麽叫邏輯推理文和意淫小說的區別。)那麽,貝志城等人對孫維的指證是否具有邏輯自洽、關鍵鏈無缺失、論證有力、結論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呢?這個問題可以轉換成一個前提性問題:貝志城的言論是否全部可信?貝志城在事實陳述、觀點描述中有沒有撒謊?這個問題可能立即就冒犯了很多支持貝志城的網友,因爲貝志城在他們的眼中是一個真正的“大善人”、“好人”、“英雄救美”式的人物,對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一種徹底的無禮行爲。但我請你們克制你們的這一沖動,並提醒你們有必要改變你們的思維模式:不要把“求善”放在第一位,要把“求真”放在第一位。“貝志城有沒有撒謊”,這個貌似不那麽重要的問題,貌似汙蔑了這個大功臣的不禮行爲,其實是解開該案的一個重要鑰匙扣:如果有充分證據證明一個人在某件事上撒了謊,即使像是不那麽重要的謊、邊緣性的謊(一個人撒謊一定是有動機和原因的),那麽他對該事件的其他內容的陳述的可信性都要降低,更不要說他對該事件的結論性看法。然而太多的人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一點、無視這一點,這本身就是可悲的。那麽,貝志城到底有沒有撒謊?這其實是早就已經有明確的、准確的答案的,在十年前就已經有明確而准確的、毫不含糊的無法推翻的答案的。答案就是:有,並且很多。本文並非是一篇完整分析貝志城言論的文章,無須列出全部的質疑點,只需要指出若幹個例證,就可以證明該結論。這些出自貝志城之口的前後矛盾、與事實不符的說法,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一些內容:1)“初中畢業後與朱令沒見過面”說貝志城的“初中畢業後與朱令沒見過面”及類似的說法,由貝志城在多個場合重複過多次。包括最近一次接受王菊采訪(2023年12的語言采訪),仍然堅稱:“我與朱令接觸只有初二那一年”。爲了確認這一說法,這個采訪錄音我完整聽了兩遍。然而這是十分不可信的。因爲,貝志城與朱令是初中同班同學、高中同校同學、大學臨校同學。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青蔥歲月年代,初高中同學、大學生們是十分熱衷于聚會的。我不相信、任何一個有點理性的人也無法相信,貝志城、朱令這個北京市的初中班級在初中畢業到大學期間都沒有過同學聚會;高中同學會沒有過同學聚會;都在北京上大學一清華一北大的初中同學、高中同學沒有過一次聚會;如果真是這樣,那這個班集體的關系得有多麽不好,不好程度遠超貝志城所攻擊的清華朱令班同學。如果有過聚會,那麽這兩個人,並非性情十分怪癖、十分不合群的兩個人,卻都沒有見過面。如果真是這樣,那只能說明他們倆關系並不好、很不好,聚會都避著走。如果是這樣,無法解釋朱令中毒後貝志城的積極奔走、熱情幫助,這絕非一個“大善人”三個字就能解釋得了的。基于上述這個原因,貝志城的“初中畢業後與朱令沒見過面”說辭即使不是100%說謊,也是99%在說謊。而被方舟子指出的貝志城在2002年發在雅虎群的帖子內容:“朱令經常去北大找他玩、一起上外語口語課、在朱令病發前見過面”等內容,才更符合初中同班同學、高中同學、大學臨校同學的同學關系描述。如果這個帖子內容確定是貝志城發的(貝志城的早期說辭之一),那就更證明了貝志城後來改口至今的“初中畢業後與朱令沒見過面”說辭是100%在撒謊了。

2)“朱令親口指證孫維”說另外一條非常關鍵的、被衆多媒體和正義群體網友多次引用、將嫌疑和指控對象直接指向孫維、被視爲孫維犯罪“鐵證”的話,是貝志城于2005年在《貝志城關于朱令事件的聲明》中所提到的第四點“聲明”內容:“朱令和朱令家人都深信孫維是凶手,記得多年前我去朱令家看望朱令時,朱令曾經喃喃自語說:我還把孫維當好朋友……難怪她在我休息(至第一次中毒後回清華)的時候老給我送咖啡喝。”

“朱令家人深信孫維是凶手”可能是事實,但是朱令本人是否有如此深信並有過如此雖然“喃喃自語”但卻清晰的表述呢?其實,我們根據衆多公開媒體的報導就能對此有所判斷。我隨便引用一例:2001年5月《三聯生活周刊》的一篇題爲《醫院:被延誤的病人和從不延誤的權力》的文章中曾如此報道:“朱令在1995年因铊中毒延誤治療留下了永久性後遺症,現在她已經100%傷殘,全身癱瘓、雙目近乎失明、大腦遲鈍及基本喪失語言能力。”一個已經喪失語言能力的人會有如此一長串的內容清晰的表述嗎?不能。在其他的媒體報道中,我們也能看到關于朱令在應激狀況下會發出“呀呀”聲音的報道,沒有任何報道證明朱令在受到如此嚴重創傷後還能如此語音清楚到他人能聽清語義清晰到能完整陳述事實、表達觀點的程度。並且,貝志城的這一說法也與他自己說過的“朱令中毒後只看過一次,就是在ICU裏看到她身上蓋著白布、渾身插滿管子,看了以後想拔腿而跑的那次”說法相矛盾。這兩個說法必有一謊。3)“樂隊競爭”說“朱令、孫維同在民樂隊有競爭關系”也是貝志城最先提出來、並且被確定爲孫維作案動機的重要“鐵證”之一。但這一說法也早已被證僞(貝志城似乎已經承認這一條說法是被證僞的)。原因很簡單:因爲朱令彈的是古筝獨奏和中阮伴奏,而孫維練習的只是中阮伴奏;古筝獨奏方面孫維根本沒有競爭性;中阮伴奏是團體性節目也不存在你上我下的競爭性。更關鍵一點,當時孫維已經退出民樂團了,即使朱令不上台演出,孫維也沒有上台演出的可能。所以這完全是一條徹頭徹尾的意淫式誣陷,但是在事實被澄清之前已經生效了、有效了,在很多網友那裏甚至有效到現在。4)“家庭背景、高層幹涉”說與以上幾條貝志城指證孫維的“鐵證”相比,貝指出孫家的“家庭背景、高層幹涉”一說是更能引爆網友情緒的一個炸彈,炸出洶湧澎湃的網絡激流。貝志城借其“公安朋友”的嘴說出的“孫家爺爺拉著當時最高領導的手爲孫維求情,請求最高領導人放了他孫女”、“而公安局長拍案而起,說放什麽放,打死了裝麻袋裏放出來”等等,這是在繪聲繪色寫小說了。且不說在1995年孫維並沒有成爲所謂的“唯一嫌疑人”受到審查和拘留,孫家爺爺是否在自己于1995年去世之前知道此事,單就“放了”和“公安局長的裝麻袋裏放出來”的語境都不能成立,因爲孫維當時根本就沒有被拘留抓捕,談什麽求情放不放呢?退一步來說,這條信息即使不能證僞,也無法證實。因爲這是貝志城的單方面一己之言,借其“公安朋友”的一己之言,就像他曾經借朱令的口指證孫維的說法一樣(前述2)。但是已有證據證明借朱令之口指證孫維是他捏造的,那麽又有什麽理由相信這條借“朋友”之口的指控不是捏造的呢?再退一步來說,即使此說成立,時過境遷二十多年後,中國權力格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的“保護傘”已經完全不能成爲保護傘,其對手也完全可以借此發揮。但是,爲什麽沒有?(不再展開了)。值得一提的是,貝志城在多次強調孫家的“高幹”背景繼而引導輿論時,卻從來回避談他自己的紅色家庭背景更強大更嫡系這一事實。5)“白馬酒店謬誤”說另外一條非常重要的、與事實不符的說法是:貝志城多次強調“《白馬酒店》一書裏對铊中毒的症狀和投毒方式的描寫都有大量錯誤,看了這本書能去下毒或者能診斷铊中毒的可能性很小。”然而真正的事實是:英國女作家阿加莎·克裏斯蒂于1961年出版的《白馬酒店》一書中對铊投毒方法和中毒症狀的描述被公認爲非常准確,甚至一度被當時的批評家批評該書是一本投毒教材。因爲本書,國外發生過很多起因爲讀了該書受到啓發而用铊投毒的犯罪行爲,也有警察、醫生因爲讀過該書而破案、診斷的案例。爲了證明這一點,我專門轉發了《白馬酒店》原作的部分內容,見:《<白馬酒店>中關于铊投毒及犯罪心理的片段節選》,以及基于該作改編的影視劇作品:《<白馬酒店>改編的英劇<白馬酒店>(Marple: The Pale Horse,2010)》。願意求證的朋友可以移尊求證。稍微翻一下這本書就能確知:《白馬酒店》铊中毒的症狀、铊投毒的手段、铊鹽的來源都有非常精准的描寫,完全不是猜測式的意淫型小說。在铊中毒的症狀方面,《白馬酒店》是這樣描述的:“每個人的症狀可能會有差別,起初可能會嘔吐、下痢,或者四肢疼痛,卻都有一點相同——遲早都會掉頭發。”“所有铊中毒的人都會大把大把掉頭發”(見上述引文,下同)。而朱令中毒後的症狀是:腹痛、胃痛、惡心、嘔吐、四肢及關節疼痛、嚴重脫發。在铊投毒的手段方面,《白馬酒店》是這樣描述的:“有人受雇給一家消費者調查公司事先向受害人做問卷調查:‘你喜歡哪種面包?府上用什麽牌子的衛生用品、化妝品?’然後在某一天讓投毒者扮成門房、或者查電表的人等等角色進入受害者房間,將受害者使用的這些衛生用品、化妝品、咖啡飲料換成加了铊的同品牌物品。”這與朱令案中被懷疑的投毒載體完全一致。在铊投毒的隱蔽性方面,《白馬酒店》是這樣描述的:“可是被害者遲早會露出一些生病的症狀。雖然找醫生來看過,可是卻看不出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他也許會問病人吃或喝了些什麽,但是卻不會懷疑病人用了好幾年的一般私人用品。”這與朱令案中被協和醫院誤診的情況十分相似。另外,在铊毒的獲取途徑方面,《白馬酒店》是這樣描述的:“铊被用來當脫毛劑——尤其是得了金錢癬的兒童。後來有人發現這種元素很危險,不過偶爾還是配合病人的體重,小心地用作內服藥。我想現在大多數都拿來當毒老鼠藥。這種藥沒有異味,容易溶解,也很容易買到。”“通常都用來制造老鼠藥,有時候也用來醫治兒童的癬病。很容易就可以弄到。”這一點描述與朱令案中帶給給公衆的信息完全不同。朱令案中人們的關注點都認爲铊的來源只能是實驗室,該書卻說铊的來源其實就是很普通的老鼠藥、治療皮膚病的藥。那麽,該書是在胡說嗎?當然不是。稍微通過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就會得到如下此類信息:“铊一開始的最大用途是殺鼠劑。在多次意外之後,美國于1972年2月經第11643號行政命令禁止使用铊殺鼠劑。其他國家也接連實施禁令。”“人們曾使用铊鹽來治療癬等皮膚感染病,以及減輕肺結核病人夜間盜汗的情況。不過此用途頗爲有限,因爲铊鹽的治療指數區間較窄,更先進的相應藥物也很快將其淘汰。”

要知道,《白馬酒店》這部作品是在1961年出版的,而美國禁止使用铊作老鼠藥是在十一年後的1972年,英國更晚。所以《白馬酒店》中對此說法是完全符合曆史事實的嚴謹說法,沒有任何破綻和不符事實之處。再說句公道話,如果阿加莎·克裏斯蒂是以猜想、意淫的方式寫這些偵破小說,她的作品絕對不可能有生命力,她也絕不可能成爲人類曆史上銷量最高的作家。她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謀殺案》等等經典之作怎麽可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成影視作品,影響了一代一代的偵破小說、懸疑電影?另外一個曆史事實是:阿加莎·克裏斯蒂的作品在90年代的中國大學生中非常流行,諸多90年代文科生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就《白馬酒店》提供的信息再稍微引申一點的話,我們有理由得出如下推論:既然《白馬酒店》裏的铊來源是老鼠藥、皮膚病藥,那麽朱令案中的铊來源是否也不能排除這些?美國是在1972年才禁止用铊做老鼠藥的,中國什麽時候禁的不知道但肯定要晚于這個時候,到九十年代還有這樣的原料或制成品的老鼠藥存在于民間,那是非常可能的事情,畢竟我國曾大規模地除包括老鼠在內的“四害”,想盡各種辦法除四害,這種原料應該並不是很難弄到的東西。那麽铊的來源就不能只限于實驗室了。這是不是非常合理的、不能排除的推論?總之,貝志城對《白馬酒店》的否定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他爲什麽要做出這種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說法?以上五條,已經充分地例證了貝志城曾經說謊並且多次說謊的事實。其他更多內容,包括求救的英文信到底是自己寫的還是美國人幫忙寫的、回信中關于铊中毒的比例到底有多少、到底有沒有一個暴躁的美國醫生打電話斷定那就是铊中毒、對國外回複郵件翻譯的說辭等等細節內容,是否具有其中不實的部分、捏造的部分,其實都不能完全排除。(如有必要,另文再論)那麽新的問題就來了:貝志城爲什麽要撒謊?爲什麽要撒這麽多的謊?有人故意回避這個問題,但這就是解開該案最大的問題。一個熱心做好事的人,一個純粹做好事的人,爲什麽要撒那麽多的謊?一個根本沒有必要撒謊的人爲什麽要撒謊?他有什麽難言之隱要撒謊?他有什麽利益需求要撒謊?一個與此案毫無關系的、中立的、熱心幫忙受害者的人爲什麽不能坦坦蕩蕩?這麽一個與案情無關的“旁觀者”、“幫忙者”,說了這麽多與事實不符的謊話,似乎只有一個目的:指向、引向“唯一嫌疑人”。無論是其直接的明示,還是有意的暗示、誘導、鼓動、煽動,都只是爲了引向這一個目的。爲什麽?如果要指證一個他人,有必要通過說謊的方式嗎?難道事實陳述不是最有力的嗎?


正如某網友所評論的:“貝的某些言論非常的不負責任,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情,總是拿一些道聽途說和完全站不住腳不值一駁的所謂證據來煽情,無論對孫維還是對朱令都是一種侮辱和傷害。”貝志城對這些質詢的反應是什麽呢?是“不辯”,是高姿態的“不辯”,是被其支持者稱爲“聖人模式”的“不辨”/“以不辨勝萬辯”/以不辯之辯爲高辯。不知道到底是不敢應對,還是不屑于應對。但是,無論不敢還是不屑于,都無法改變已經被證明是謊言的那些言論。那麽,采用了“聖人模式”的貝志城真的不在意這些質疑嗎?並不是:他憤怒地辱罵質疑他的方舟子是“狗”。

如果秉著幫朱令查明真相的原則,不應該去回應這些質疑嗎?回應這些質疑不是更利于查清真相嗎?用髒話罵人家是什麽意思呢?難道這些質疑是在無理取鬧嗎?他有先辱罵你嗎?

這樣的言論這到底是符合了其“英雄救美”的大善人形象,還是符合了其十年未變的人生箴言“以缺德服人”及其網名“一毛不拔”形象?(注:“以缺德服人”這幾個字是貝志城至少十年未變的某網絡賬號簽名檔內容)另外,貝志城的上述回應其實還體現了其習慣性給他人扣帽子尤其是政治帽子的思維模式。就像說孫維家背景(但從來回避談他自己家的背景更強大這一事實)一樣,給反駁他的方扣上曾經受到經倒台的政治人物支持的帽子。這些張口而來的指控有證明嗎?他不可能有(有的話現在完全可以抖出來,搞臭、搞死對方),然而他就這麽張口就來了,就像他張口就來其他謊言一樣。除了謾罵就是扣帽子,這是符合60年代紅小兵的一貫做法的。這種思維模式、表達模式是典型的扣帽子模式,並且旨在通過“發動群衆”“引發輿論洪流”去討伐他、打擊他。

一個被證明說了那麽多自相矛盾、與事實不符的謊言、假話的人,他的其他口供、舉證是否值得相信?尤其是那些沒有第二個人第三個能提供旁證、佐證的那些言論,比如貝志城假借“公安朋友”說的話,以及其提供的很多很有煽動性的信息、引起極大關注與反響、但均沒有明確指明出處,這些無人對證、無法對證的話,本著單方言論、“孤證不立”的原則是完全不可采信的。然而卻被廣大網友當成了“鐵證”。無視他已經撒了那麽多謊言,反而認爲這麽一個撒了很多謊的人的話是可信的。原因可能只是因爲他是那個“英雄救美”的“大善人”這一“第一印象”的根深蒂固無法撼動。這篇文章已經很長了,今天又是過年,我要盡快給這篇萬字長文收個尾,可能沒有時間檢查第二遍,但仍然會做到盡量地嚴謹。簡單說一下,除了那些被證明的謊言,在推斷“孫維是唯一嫌疑人甚至斷定就是凶手”這一邏輯鏈上存在的幾個重要漏洞之一:“孫維是唯一能接觸到铊的人”。這個說法雖然不是貝志城的單方面說法,但也是他多次強調並以此把孫維推上“唯一嫌疑人”位置的。但這一點其實早已經被證僞、被推翻了的,只是很多人不願意接受。如果再結合上述《白馬酒店》部分的分析,铊的來源擴充到老鼠藥和老鼠藥的原料方面,這一論點就更不能成立了。以及“多次攝毒是否等同于多次投毒”這個話題,其實《白馬酒店》早已給出了答案:不需要。投在化妝品、咖啡、奶粉、日常用品中的铊毒,只需要投毒者一次投毒,就能造成受害者多次攝毒。所以很多網友根據“2018論文”下結論說“小劑量投毒了25次”的說法是很難成立的,非常不具備可行性、操作性。再比如通過“2018論文”發現朱令的中毒時間是8月份(方舟子論證出是7月份),當時清華還是放暑假期間並沒有開學(9月6日開學的),所以在宿舍投毒的這一結論又出現漏洞。如果你要論證出當時朱令已經去了學校、孫維也去了學校、孫維提前進了實驗室並能拿到铊,這需要非常謹慎地提出這一系列證據,而不是嘴唇上下一碰說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必然就是這樣的。所以,到這裏,我要總結一下這些論證出“孫維是唯一嫌疑人並且肯定是凶手”的普遍性基本性邏輯方法:在多種可能性中找出一種可能性,然後用這一種可能性替換、掩蓋多種可能性,把這一種可能性視爲唯一性,不再考慮其他可能性的存在,繼而從這種唯一性假設推導出一個唯一性結論,然後說這就是唯一結論,蓋章發布。這就是這個推理、這類推理的最大問題:把可能性當成了唯一性,把單方面的口供當成了鐵證,只爲了符合自己的預設結論、符合自己的情緒傾向。通過假設一個唯一性,然後得到一個唯一性結論。而似乎忘了不僅要論證該結論的其可能性,而且更要論證其唯一性。網上熱傳的“沒藥花園”的六篇“推理文”就是這方面的典型。爲什麽要提這個號的文章?因爲一直有人給我說這個號的這組文章是邏輯嚴謹地論證孫維是凶手的巅峰文。我看了以後哭笑不得,不能相信我微信朋友圈裏有這樣品鑒水平的網友存在。



這個號上的這一組文章貌似引用嚴謹、邏輯推理,其實漏洞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可以說是意淫臆斷隨處都是,可以說滿篇都是,完全不是嚴謹的分析,而是預設立場、有罪推定,在諸多可能性中挑出一種可能性,然後把它當作唯一性、必然性去講故事。非常多地從一個謊言前提推導出另一個謊言結論,然而卻覺得自己論證嚴謹分析有力了。這種意淫式小說文我當然是不願看的,但如果有人認爲有必要,我完全可以指出這組漏洞百出的文章裏到底有多少個漏洞、意淫、謠言、猜測、武斷、臆斷、誣陷在裏面。爲了證明這一點,我隨手截屏舉個例子:比如,爲了論證孫家爺爺給領導打招呼,此文作者做出如下論證:如果孫維在1995年不知道自己被懷疑,她就不會在1995年給她爺爺說此事,她爺爺就不會在1995年給領導打招呼,而她爺爺在1995年就去世了,以後也不會打招呼,所以結論是孫維撒謊了,她在1995年已經知道了自己是唯一嫌疑人並且告訴了她爺爺于是她爺爺才給領導打招呼了要保護她。該作者完全不考慮另外一種情況:如果貝志城在這裏撒謊了呢?貝志城這個單方面言論有人能給出旁證和佐證嗎?沒有。沒有爲什麽可以直接采信並以此做推理狀?把讀者當成腦殘看待嗎?


再比如,該作者在提到“2018論文”時寫道:“該論文告訴我們最後投大量在中藥瓶中。”這就屬于隨口造謠亂謅,“2018論文”我前幾天已經全文轉載出來了見《“2018論文”到底是證實了孫維投毒還是證僞了孫維投毒?請看原文》,任何人可以拿放大鏡去看看此論文的作者有沒有得出該結論。該“投在中藥瓶中”的結論完全是這個號的作者自己意淫式推出來的,同樣是把一種可能性當成了絕對的唯一性,然後基于此繼續進行意淫式推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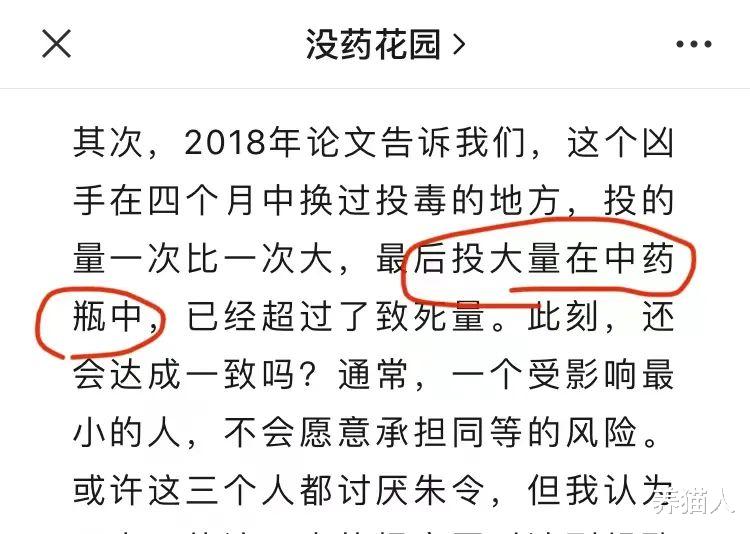
這個號裏該系列文的此類“湊結果”式推理太多了,比如基于“2018論文”爲了湊出“首次中毒”的時間,竟然毫無根據、毫無依據地提出了清華當年提前開學、朱令孫維提前到校、孫維提前進了實驗室這種說法。我不是說這種可能性不存在,我是說這完全不可能是唯一的可能性:如果當年清華沒有提前開學呢?如果當時清華提前開學了(比如所謂的小學期)家在北京的朱令住在家呢?或者住在集中班宿舍呢?如果當時孫維並沒有提前進實驗室呢?爲什麽、有什麽理由剔除掉如此多的可能性,就把唯一能湊出自己想要的結論的可能性當成了唯一可能性呢?把猜測當成了事實,把某一種可能性當成了唯一的事實,只是爲了“推理”出自己預先設定好的結論。這不叫推理斷案,這叫意淫。“沒藥花園”的這組文章裏,遍布了各種各樣的謬傳謠言,以及各種臆斷式的猜測,以及基于這些謠言和臆斷式猜測下的結論。所有認爲這組文章邏輯嚴謹有道理的人,都需要好好補一下邏輯課,請到我的公衆號後台交報名費、學習費、解答費、課後作業費。以及有必要再提一點:在這個案子中,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謠言充斥其中。這些荒謬的和過于荒謬的謠言可能由別有用心的人炮制,然後經由不明真相和難辨是非的人、有正義感但沒有太多分析能力的“正義群衆”去推動。截屏舉幾個例子:比如,有大V說在孫維的桌子上發現了铊鹽、在孫維的尿樣中檢出了铊。

比如,有媒體說有證據表明孫維曾購買過铊。

比如,有人說美國國會曾命令法官遣返孫維。

這些都是一望而知的低級謠言(爲什麽是低級謠言?問出這個問題的網友不要到我這個號上看文章了),然而被廣大“正義網友”認爲是真實事實于是四處轉發,同時伴隨著自己的正義感爆棚,覺得自己伸張了某種正義。只有極少數冷靜的頭腦能夠洞悉低級謠言的真僞,能辨別什麽是意淫文什麽是真正在的推理文。比如下面這個早在2019年發帖的華山客。



華山客提出的上述24條資料清單也是我比較認可的,是了解該案的一些基本參考資料清單。該清單的最後兩條全文我也已經轉發(見本文文末的相關資料部分)。不要拿什麽“沒藥花園”之類的意淫小說文跑來論證什麽,那是在侮辱你和我的智商。其實上述資料清單的前23條首次見諸于一篇2018年前的三萬字網絡長文《慢慢扒了朱令案真凶的皮》。相對于“沒藥花園”之類的意淫式斷案,這篇三萬字長文才算是冷靜的有理有據的案情分析論證文。我本想轉發出來,但不知何故一直轉發失敗,于是只好放棄。

這篇三萬字的論證長文我無法轉載出來,但是其中的一段話我認爲最有必要轉給讀者們:【在這個事件中孫維其實相當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在刑案中,控方才負有證明被告有罪的當然的舉證義務,其所舉出的證據是否真實有效及是否具有證明力才是決定指控能否成立的關鍵,所以我最關心的不是她的自辯,遊戲規則本來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控方證據不成立,即使被告不能證明自己無罪也不能認定其爲有罪,但是孫維及爲其辯護的清華學子們沒有想到的是,在這個網絡空間裏,遊戲規則並非如此,當廣大義憤填膺的網民坐上法官的位置,控方可以是匿名的,就算貝志城坐上控方的坐椅,當把“據說”、“有人告訴我”之類的當作有罪證據的時候,因爲出自組織網絡救助的義士之口,這些證據是可以被采信的,她不能自證無罪,是可以證明她有罪的,遊戲規則是顛倒的。】這段話與本文開篇關于控辯雙方的觀點相呼應,于是轉發在這裏作爲本文的結尾。好,最後的結束語。本文並非闡述一個結論性的個人觀點,只是在既有信息下做出的合理範圍內的有限推定。雖然沒有結論,但我們相信:1)真相只有一個。2)一定有一個凶手。3)這個至今沒有伏法的凶手現在正在觀察者網上的討論,嘴角時不時浮現出一絲淺笑,自信滿滿。再回到《白馬酒店》。其實這本書不僅對铊投毒的手法、中毒的症狀有准確描述,還對犯罪心理學有精到描寫,比如:“如果他靜靜坐著,什麽事都別插手,我們絕不會懷疑那位可敬的藥店老板跟這件事有任何關系。可是有趣的是,凶手偏偏做不到。本來他們可以坐在家裏,安然無事,可是他們偏偏過不慣安逸的日子。”“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凶手覺得寂寞,認爲像自己那麽聰明一世的人,居然沒有可以談心的對象,真是可惜。”“這就是他的虛榮心,典型的犯罪者虛榮心。”而《白馬酒店》原著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其實是:“從他一開始說謊,我就懷疑他。”(本文完,如有必要,會有後續)

(白色的铊鹽,黑色的背景)------------相關資料:
著名大V在十年前爲孫維寫的長篇辯護詞律師張捷十年前的回應文孫維免費辯護師的最新一組反诘質詢:“貝志城爲什麽要撒謊?貝志城爲什麽不吊唁?貝志城在恐懼什麽?”“2018論文”到底是證實了孫維投毒還是證僞了孫維投毒?請看原文黃光銳十年前的一篇重要博文:清華文藝社團的“集中班”和朱令案偵辦的巨大漏洞《白馬酒店》中關于铊投毒及犯罪心理的片段節選《白馬酒店》改編的英劇《白馬酒店》(Marple: The Pale Horse,2010)貝志城在2023年12月接受王菊的采訪錄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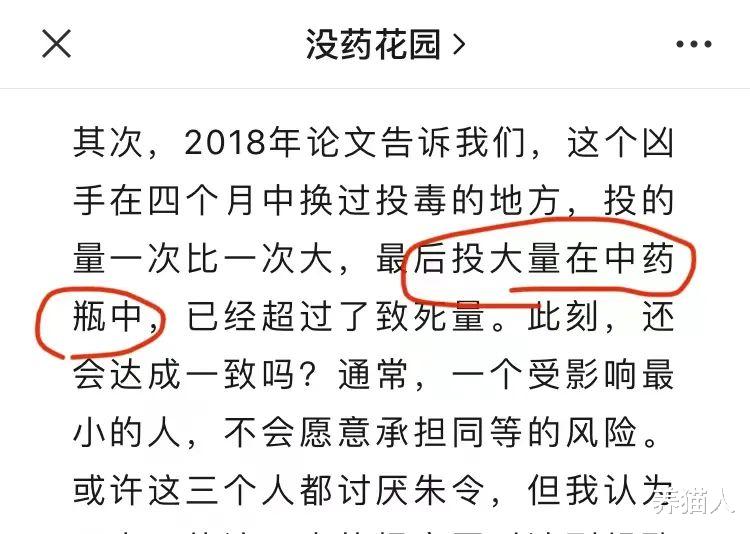









至少貝不是凶手,孫如果被汙陷可回國,拿起法律的武器來捍衛自己名聲和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