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是張隆溪教授新出版的一部文學通史。書中第七章名爲The Twin Stars of Tang Poetry: Li Bo and Du Fu, 意思是:唐詩的雙子星。雙子星實指李白 (701–762) 和杜甫(712–770)。李白,張教授不拼寫成Li Bai 而拼寫成 Li B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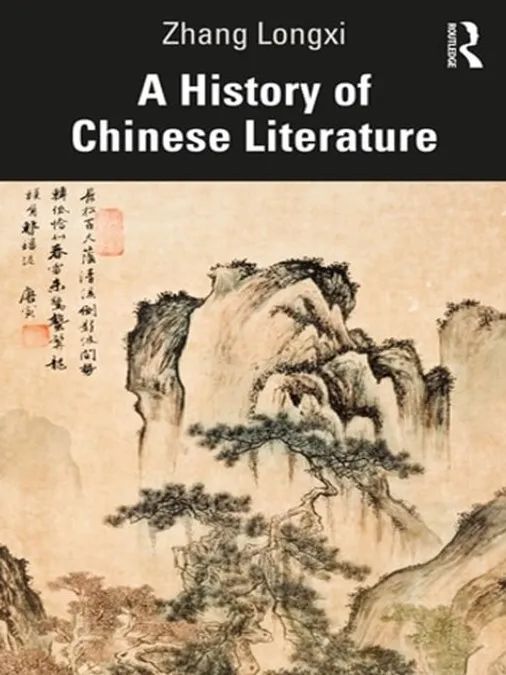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張隆溪教授認爲,絕句之體最適合李白(p.124),書中爲英語讀者介紹了李白多首絕句,並有簡短的點評。單論征引數量,書中的李白絕句多達十首(其他一般名家或僅征引一首),可知李白絕句受張教授看重。
劉大傑也說李白絕句“佳篇實在過多”(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民國廿九年序本,頁363)。李白絕句吸引讀者,應該是不在話下的(周嘯天《唐絕句史》,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
不過,李白絕句的內容如果用英語表達出來,譯文就未必受外國讀者喜愛了。
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新書發布及座談會上”,有一位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認爲: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是一部通人之作,傳達了兼通中西兩端的大學者的聲音,十分可貴。特別是以往西方學者翻譯詩歌時,經常有誤讀,造成啼笑皆非的場面。張隆溪教授以其深厚及兼具中西的治學功底,譯文信、達、雅,能引起西方讀者的共鳴。
以上言論,摘自2022年11月19日的星島網,可謂美言叠加、盡力揄揚。
可是,這篇報刊文章沒有爲讀者提供譯文實例,因此,我們無法了解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的譯文的水平高低。
本文填補這一空白,討論幾個翻譯實例。

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

張隆溪教授注意到李白詩篇之中,有好幾篇寫“離別”或者“送別”,包括以下這首送別孟浩然的:
At the Yellow Crane Tower my friendleaves westward
To Yangzhou in March with blossoms hazy and blurred.
The shadow of the solitary sail fades in the blue sky,
Only the Yangtze River flows to the end of the world.(p.125)
上面四行,是譯自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原作如下:

《李太白全集》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黃鶴樓在西(今湖北),廣陵在東(今江蘇)﹔廣陵就是揚州,“之廣陵”就是:到東面的揚州。因此,“西辭黃鶴樓”就是辭別西面的黃鶴樓,暗示“要東行”。下一句說到“下揚州”,補足了語義:“吾友辭別黃鶴樓,向東行,到東面的揚州。”請注意:向東行。
可是,張教授的譯文……my friend leaves westward/To Yangzhou……其中westward 意爲“向西”,如果westward 與次句連結,是說“吾友離開黃鶴樓,向西走,去揚州”。在方向上,原文說辭別後向東行, 譯文卻說westward / To Yangzhou (向西,到揚州), 實在顯得奇怪。
關鍵在westward是“向西”。說得淺白一點:go westward to somewhere的意思是:“往西走,到某個地方”。westward是副詞,表示“向西”,例如,某人從香港“前往澳門”,可以說“Go westward to Macau”。澳門在西面。
張教授的譯文第二行中有 To Yangzhou, 目的地沒有譯錯, 可是westward 令熟悉地理方位的讀者感到困惑: 孟浩然爲什麽要向西走?
如果讀者覺得有點亂,摸不著頭腦,那麽,請看看其他學者的譯文,例如下面這篇Seeing Meng Haoran Off from Yellow Crane Tow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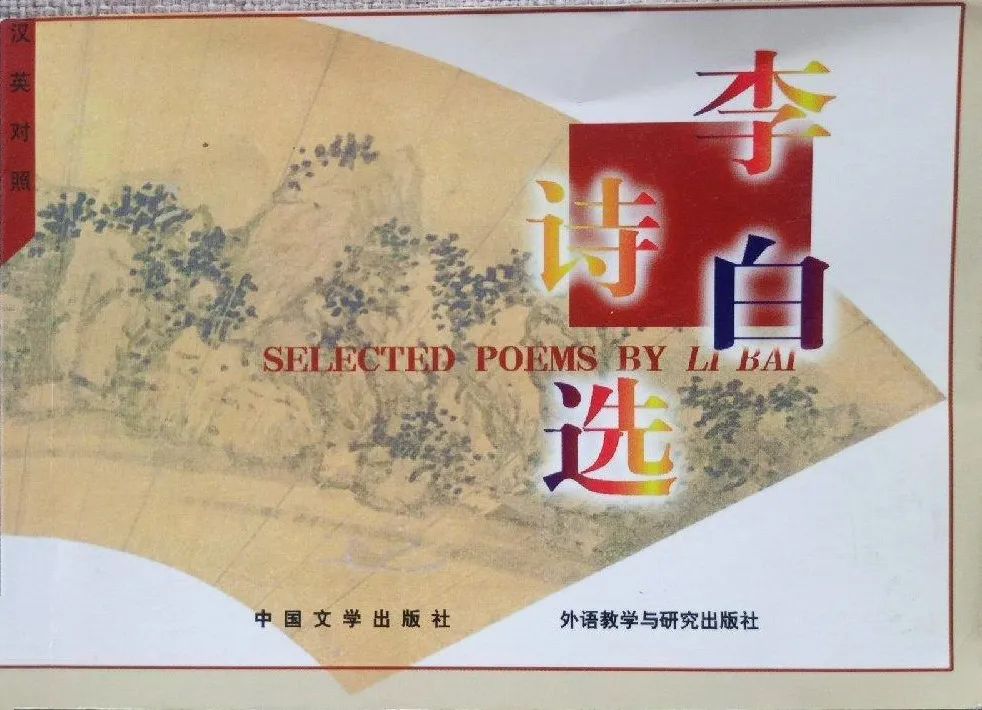
楊憲益、戴乃叠英譯《李白詩選》
At Yellow Crane Towerin the westmy old friend says farewell;In the mist and flowers of spring he goes down to Yangzhou;Lonely sail, distant shadow, vanish in blue emptiness;All I see is the great river flowing into the far horizon.(World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Vol. 5, No. 4; 2015, p.132)
上面是楊憲益的譯文,譯文風格有點“樸拙”,卻有一個好處:譯文句子成分之間的關系十分清楚, 例如 At Yellow Crane Towerin the west, 這譯文明明白白說了黃鶴樓在西面。向西面的黃鶴樓說再見(My old friend says farewell),一般讀者會理解爲“告別西樓”,也就是“故人”要向東走。
我們再看許淵沖(1921—2021)的譯文,可見許譯文清楚表明“離開西面”之意:
My friendhas left the westwhere towers Yellow Crane
For River Town while willow-down and flowers reign. His lessening sail is lost in the boundless azure sky,
Where I see but the endless river rolling by. (p.94)

《唐詩三百首新譯》
譯文的語義明朗(許淵沖等人《唐詩三百首新譯》,香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My friend has left the west 就是“吾友離開了西面(的黃鶴樓)”。
美國的學者也翻譯過這首《送孟浩然之廣陵》,這裏舉一個例。David Hinton 將詩題翻譯成 ON YELLOW-CRANE TOWER, FAREWELL TO MENG HAO-JAN WHO’S LEAVING FOR YANG-CHOU, 首兩句“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翻譯成:From Yellow-Crane Tower, my old friendleaves the west. / Downstream to Yang-chou, late spring a haze of blossoms (D. Hinton, The Selected Poems of Li Po, p.15)。這Hinton譯文中,leaves the west 指“離開西面”。詩題中 leave for Yang-chou指“去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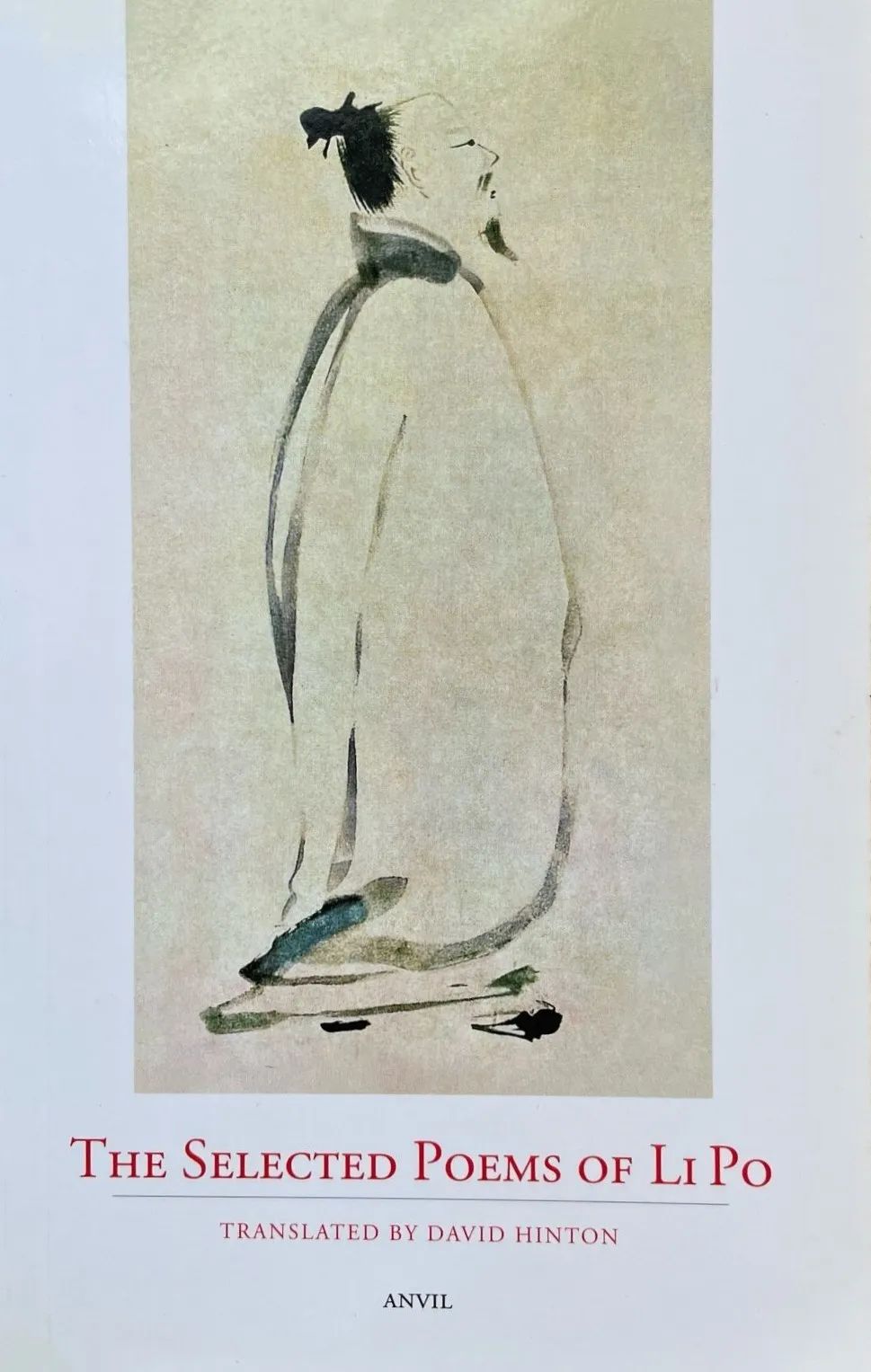
美國學者David Hinton 的李白詩選譯

李白又撰有《哭晁卿衡》,送別晁衡(698—770)。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呂,他是日本派遣到唐朝的留學生之一。張教授翻譯了《哭晁卿衡》:
My friend Chao from Japan left the royal capital,
And circled around Isle Penglai onhis boat eastbound.
The bright moon sank in the blue sea with no return,
All the white clouds look sad on the Cangwu Mount. (p.126)
日本晁卿辭帝都,
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
白雲愁色滿蒼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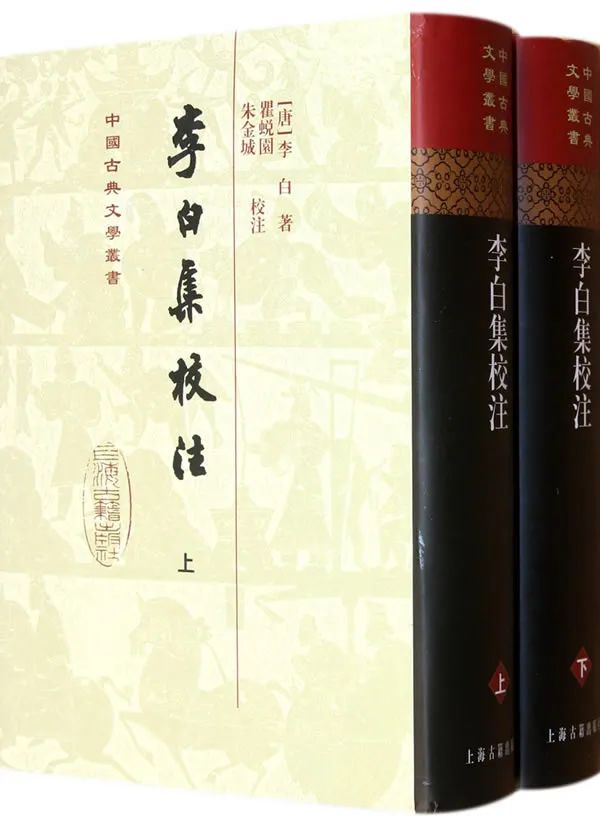
《李白集校注》
李白和晁衡交好,兩人的事迹成爲中日兩國友誼的見證(關于阿倍仲麻呂和大唐詩人之間的事,請讀者參看2023年12年13日“古代小說網”上《從哈佛博士非議〈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談起》一文)。
李白以爲晁衡(阿倍仲麻呂)在回歸日本的旅途中遇海難身亡,寫下了這首悼念詩。所謂“明月不歸沉碧海”,是以月亮下沉喻指日本友人未能回到日本,葬身于大海。
《哭晁卿衡》第一行寫主人公辭別帝京,第二行寫坐船東渡扶桑(渡海回到東面的日本)。這兩行,方向上和《送孟浩然之廣陵》的首兩行所寫如出一轍。譯文中的eastbound指“向東”,就是向東航行,回歸日本,這和由黃鶴樓走向揚州一樣,都是自西徂東。
譯文說eastbound, 方向沒有錯,但是,譯文中另外有個小問題,值得注意:his boateastbound,何以選用 boat 而不用sh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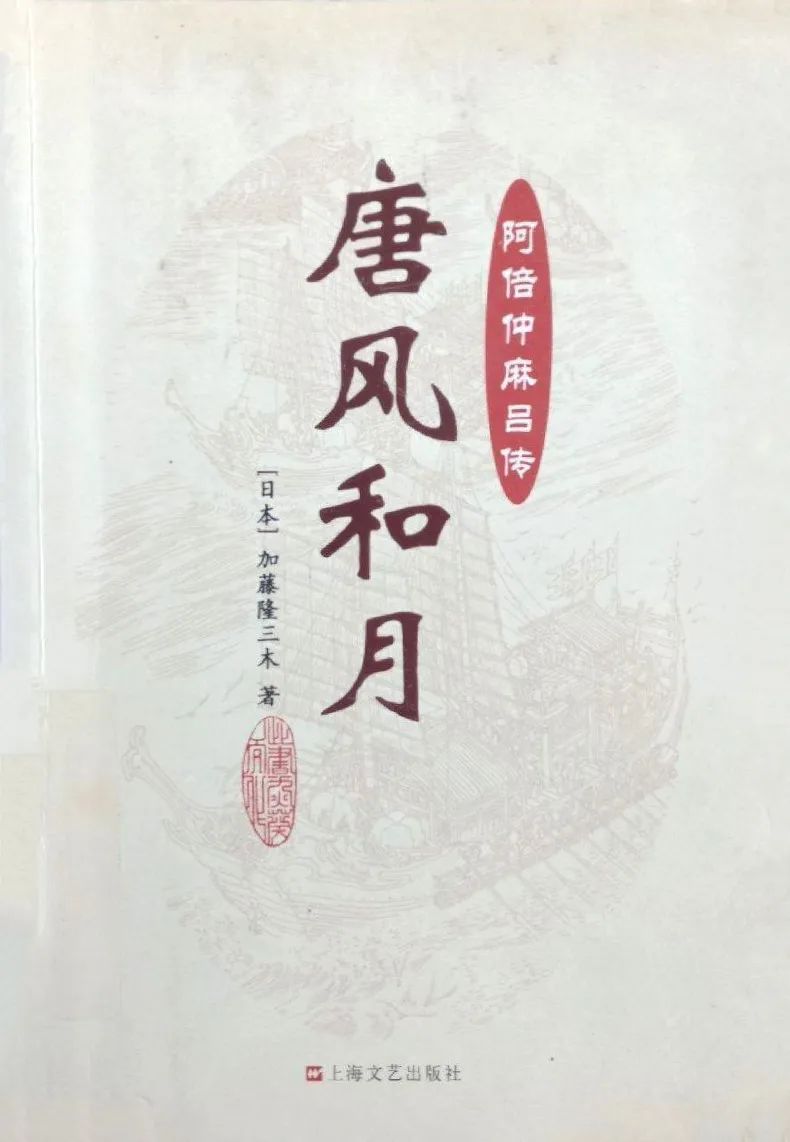
《唐風和月:阿倍仲麻呂傳》

Boats 一般指中、小型的船,古時這類船大多有賴船漿提供動力,未必有帆,而ship則通常指中、大型的船,如貨船、輪船、軍艦等,航行距離比較遠,甚至可橫跨海洋。《劍橋英語詞典》的釋義指出ship 是大的boat,特別供航海用:alargeboat for travelling on water, especially across the sea.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給ship下了定義: A ship isa large boatwhich carries passengers or cargo. 這說法可謂一針見血。大的boat就是ship。Ship可運乘客,載運貨物。
明成祖時,鄭和下西洋所用之主船(稱爲“寶船”)就不宜稱作boats。據南京紀念鄭和的一則碑文記載,寶船的排水量大概相當于2000噸左右。
阿倍仲麻呂須渡海回日本,當時,大唐和日本之間的海域海難頻生。世人知道:小船難敵大海上的大風巨浪,因此,阿倍仲麻呂如果不犯渾,自應選坐ship。
大唐鑒真和尚東渡日本的故事,可以幫助筆者解說當時(盛唐)渡東海之難。
鑒真和尚五次東渡日本,屢遇飓風,皆未能成功。他曾經遇到飓風觸礁,第五次更在海上整整漂流了14天。他雖然幸運保住性命,但是,也曾被飓風吹到海南島,完全無法自己控制航向。

傅傑《鑒真大師傳》,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鑒真第六次東渡在753年(日天平勝寶5年・唐天寶12年),他乘坐日本遣唐使返日的船,終于抵達日本,但是同行的第一船被風吹到安南,船上一百七十人被安南土人殺害 (傅傑《鑒真大師傳》,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頁152), 只有大約十人逃出生天。
張教授的譯文顯示,阿倍仲麻呂坐boat回國。這令人感到意外:阿倍仲麻呂沒有海難的觀念嗎?他爲什麽不選乘船體較大的ship?
阿倍仲麻呂所坐之船,船體的具體尺寸長短今天我們已經難以考證出來。所謂onhis boat是張隆溪教授替阿倍仲麻呂選擇的。其中his boat似乎還暗示:那boat是阿倍仲麻呂自己的。
李白寫“征帆一片繞蓬壺”。“征”字義爲遠行。阿倍仲麻呂恐怕不是坐上boat便打算遠行吧。唐中葉,渡東海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今人韓升撰《遣唐使和學問僧》一書,書中說到:隋唐時期,中日之間交通有三條主要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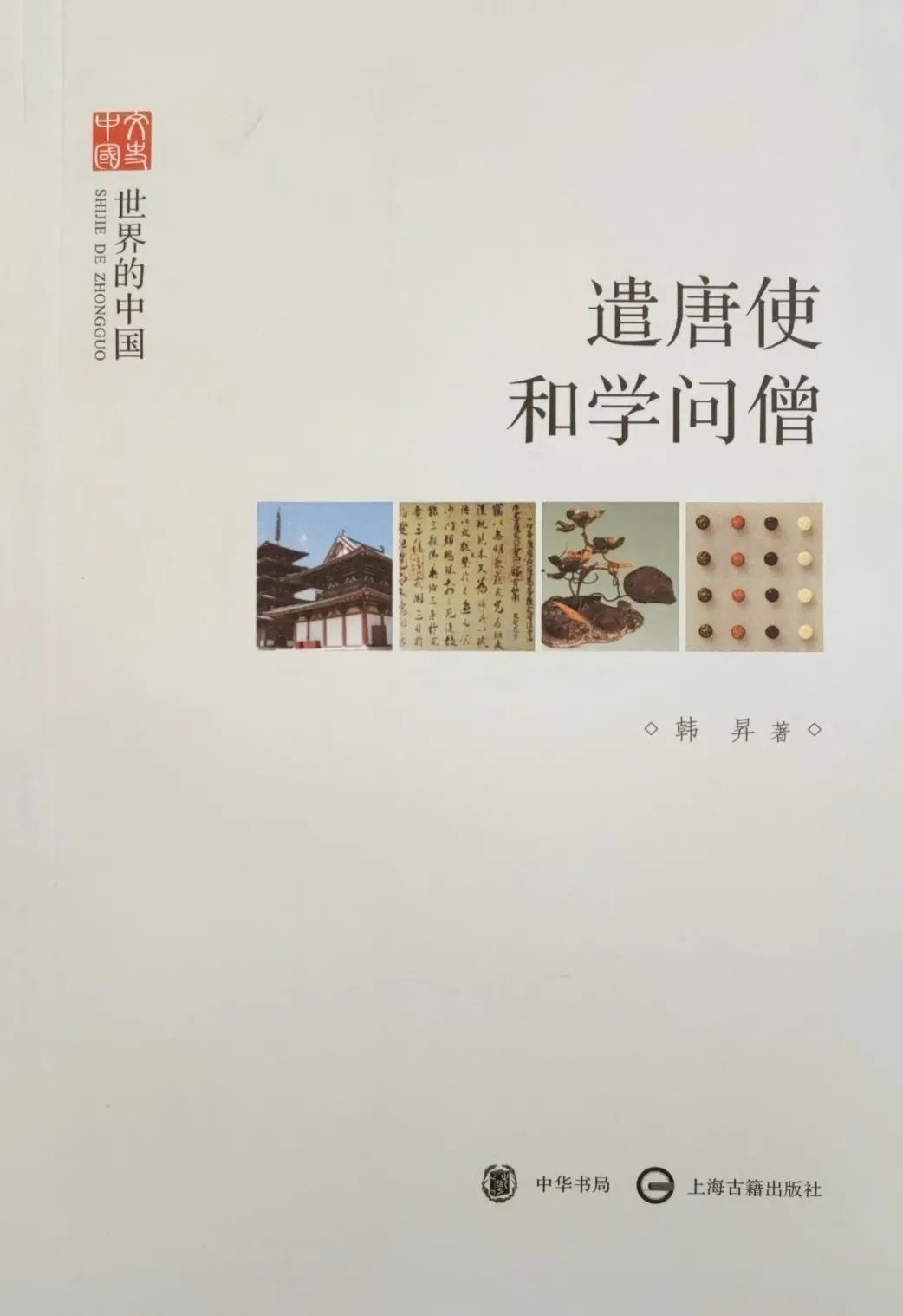
韓升《遣唐使和學問僧》,中華書局2010年版。
早期用“北路”,日人可經朝鮮半島入唐。可是,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兩國關系緊張,于是,遣唐使第二期,日本遣唐使不便再取道朝鮮,多改從九洲諸島橫渡東海,到達中土的長江口岸。這路線稱爲“南路”。
然而,南路不時發生海難,犧牲重大,所以日本又辟出“南島路”。故名思義,此路是先沿日本九州西岸南下,到九州的南方諸島,再橫穿東海到達明州(今之甯波市)。
其實,用“南島路”,同樣要穿越東海,沒有收到減少海難的多少效果,而且先到九州的南方諸島又費時,所以,日本遣唐使後來還是回到“南路”。
可見,海難是日本遣唐使要面對的嚴重問題,使團一旦遇上海難,性命都可能不保,那就談不上什麽跨國的文化交流了。
韓升說:“如果遇到順風,大約十日可達〔唐土〕”(韓升《遣唐使和學問僧》中華書局,頁28),順風尚且須用十日航行時間,我們很難想像阿倍仲麻呂坐 boat便去應付十日的航行,況且當時渡東海是“海難頻生”的(韓升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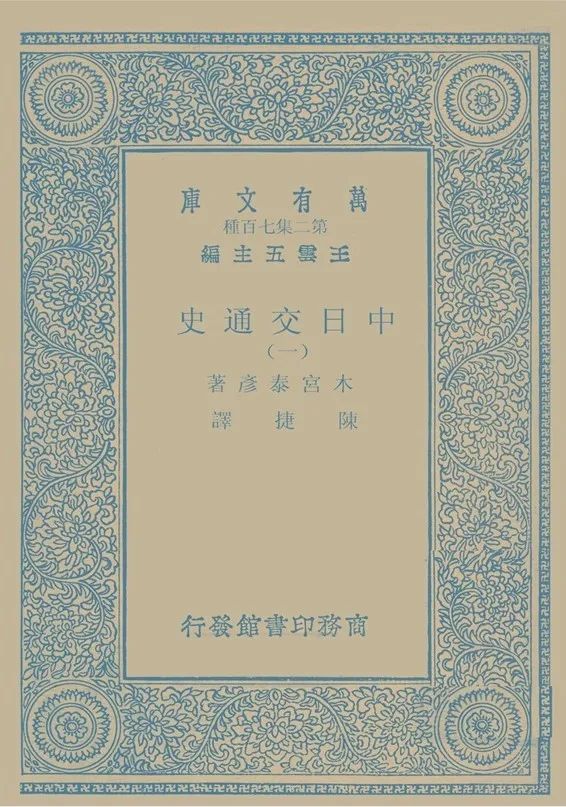
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
日本學者木宮泰彥撰《中日交通史》,記載:“文武朝後行南路之遣唐使,〔航海〕日數多而每次不免船破漂流……”(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176)。據木宮泰彥這說法,“文武朝”的船敵不過海上的大風巨浪,遇上了大風浪就算船身不解體,也會被沖得四處漂流。後來,航海技術有進步,情況才有所改善。
記載鑒真和尚事迹的《唐大和上東征傳》描寫海上的氣象:“風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濤再至,似入深谷。”小船在大海如果遇上如此惡劣的境況,很容易被怒濤吞沒。
當然,《哭晁卿衡》是李白寫的。李白要爲自己筆下的文字負全責。看了英譯文,讀者會不會得到以下印象:boat? 李白想像阿倍用boat橫渡東海?李白這人,沒有常識。
Boats的大小,也許沒有絕對的標准(不同時代,標准也未必一致),但是,一般而言, boat比ship細小,這是語言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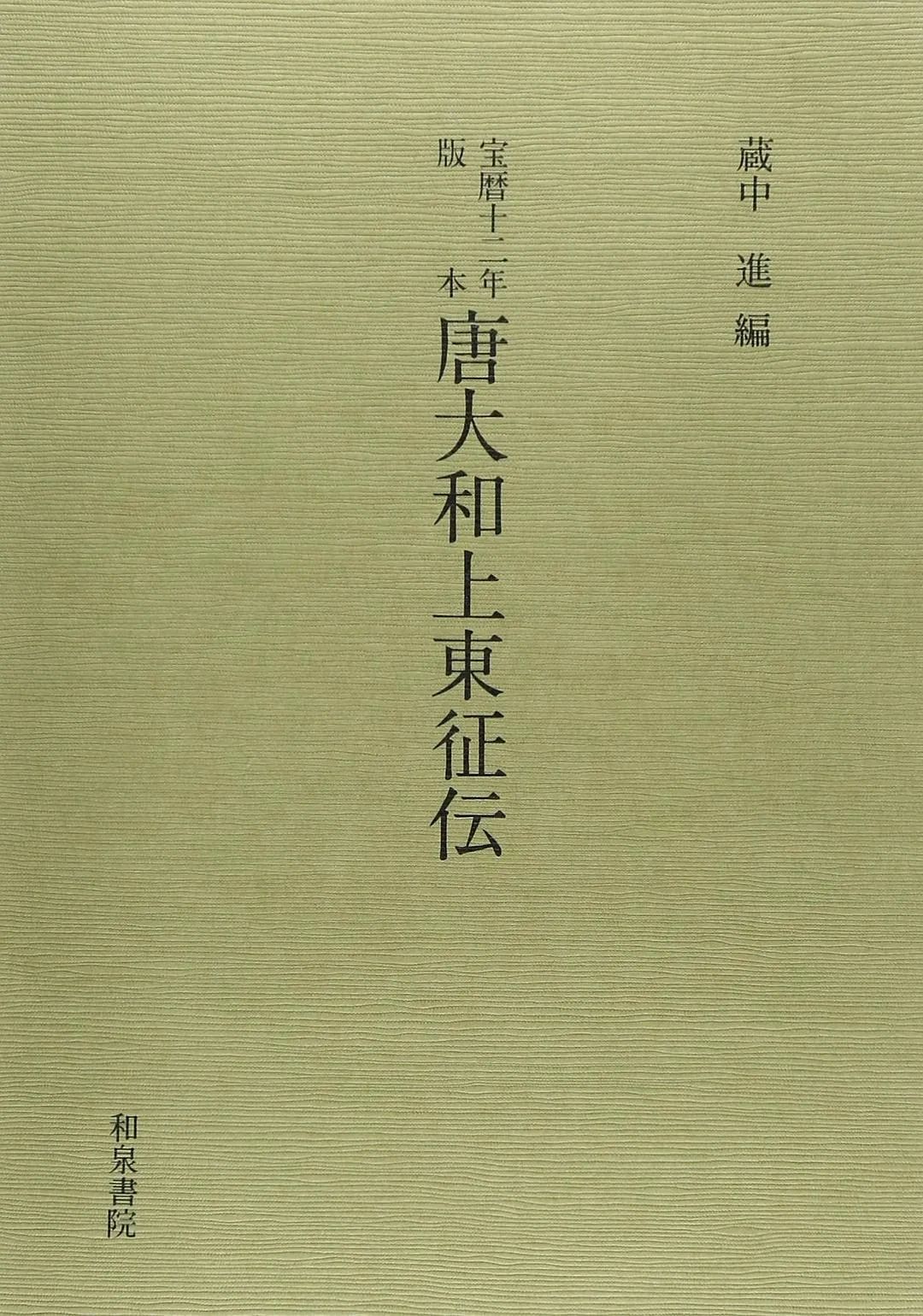
《唐大和上東征傳》
英國翻譯家Arthur Waley 將“征帆一片繞蓬壺”翻譯爲:A strip ofsailskirting its way round the magic islands of the East.(Waley,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p.61). Sail 原義爲帆,引申爲航行。 有趣的是,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一書中,涉及航海語境,張教授用boat﹔非航海語境中,張教授反而選擇用ship。
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李白用船,有特殊情況嗎?請看下文。

李白有一首《贈汪倫》(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頁1545),將無形的情誼與有形的千尺潭水相比,情真意切,是李白脍炙人口的佳作之一:
李白乘舟將欲行,
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
汪倫是李白的友人。據說,此詩成于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年),或是李白自秋浦往遊泾縣(今屬安徽)桃花潭時所作。桃花潭在今安徽泾縣西南一百裏左右。

《李太白全集校注》
一般而言,小船稱爲艇、舢舨、筏或舟,李白自己說是“乘舟”(沒說“乘船”)。然而,讀張教授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讀者看到:李白所乘,似非小船,因爲張教授選用了a ship:
Li Bo heard singing and stamping on the shore
When he was aboarda shipand about to leave.
The Peach Blossom Pond may be a thousand feet deep,
But not as deep as Wang Lun’s feelings for me. (p.125)
李白的原詩用字的是“舟”字,而舟給人的印象是小而輕,成語有“一葉扁舟”。以“葉”配“舟”,以“葉”狀舟體之小,示其輕巧便利。此外,也有“一葉輕舟”之習說,卻未見有人說“一葉輕船”。
如果李白是渡潭(“桃花潭”)離開,那麽,“潭”的主要特征是其深度,“潭”一般不如湖泊大(指水面的面積),甚少出現強風吹潭面便即波濤翻湧的險情,況且航行時間短,李白“乘舟”足以渡過潭水,因此,首句譯成 Li Bai abroada boatis about to leave 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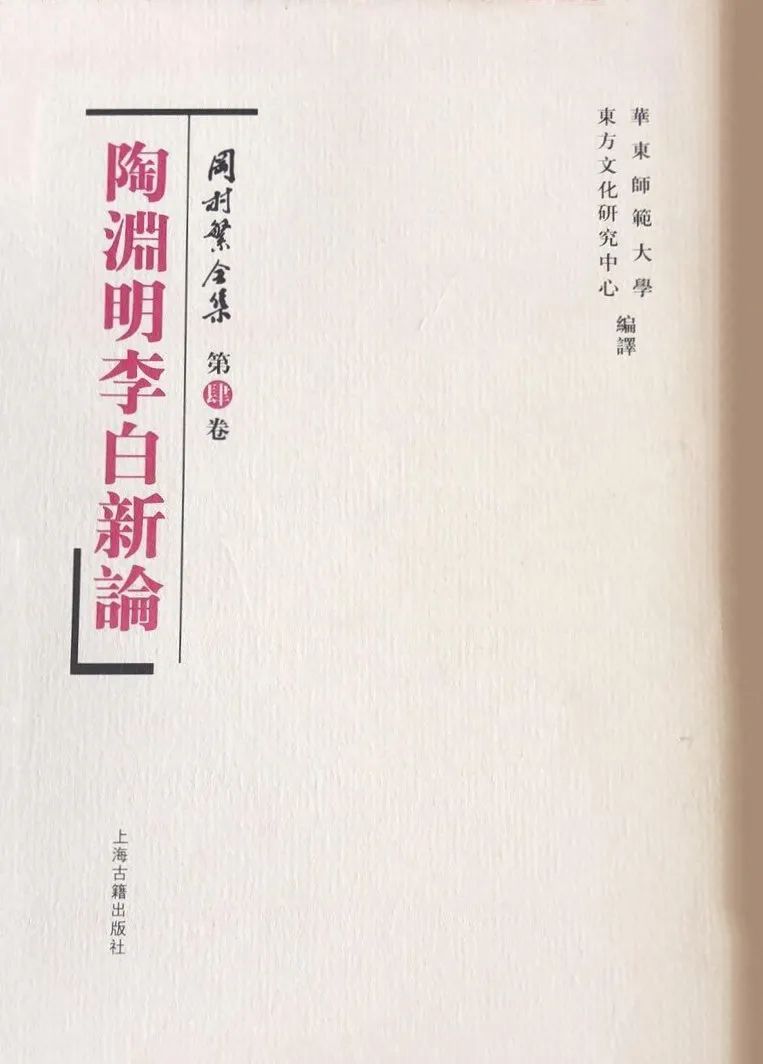
岡村繁《陶淵明李白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李白另一首名作《早發白帝城》也寫到“舟”: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裏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李白既用“舟”字,自然有他的道理:舟體較輕,用舟在水上遊走急行,比較靈活,這也配合李白抒發“過萬重山”的輕快感。這詩是李白遇赦後的作品(岡村繁《陶淵明李白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頁414)。 筆者認爲,詩人往往講究用字精准,李白贈汪倫筆下所書“舟”,恐怕不是大船。有一位譯者王大濂將“舟”翻譯成skiff: My skiff has passed by mountains, one and all, in cheers (《英譯唐詩絕句百首(英漢對照)》1997年, 頁47)。skiff一般指“小艇”。按:譯者王大濂用skiff,強調那“輕舟”甚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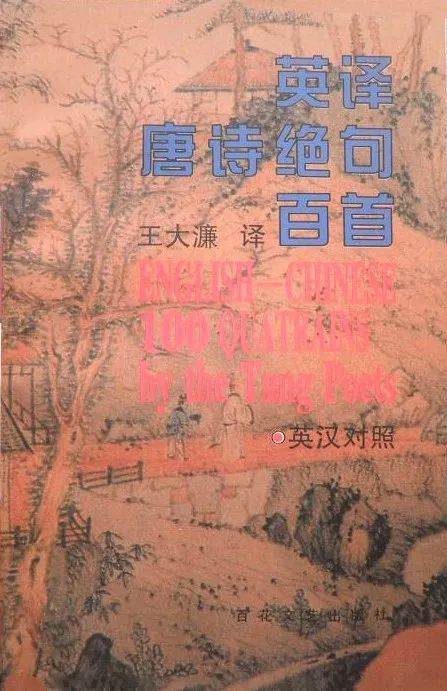
王大濂《英譯唐詩絕句百首(英漢對照)》,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杜甫的名作《秋興》中有一聯:“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孤舟是孤立弱小的意象。
宋代詞人李清照 (1084–1155) 《武陵春》說:“……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靳極蒼《李煜・李清照詞詳解》,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頁219)。舴艋舟,就是小船,李清照用輕舟之喻(喻體是舟)來反襯自己愁緒之重。

靳極蒼《李煜、李清照詞詳解》,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輕舟”和“舴艋舟”的作用,其實都是借外物之輕小來彰顯人的情緒(愁,竟有重量)。情和輕舟形成對比,或者互相襯托,這是一種藝術手法。
總之,“李白乘舟將欲行”的“舟”被譯成ship, 而阿倍仲麻呂(晁衡)渡東海之船卻譯成boat, 恐非得宜。

李白絕句,佳作甚多。羅仲鼎、俞浣萍《千首唐人絕句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選錄了李白三十六篇,數量爲唐詩人之冠。杜甫、王維,分別只有廿多首獲選。

羅仲鼎、俞浣萍《千首唐人絕句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其他英文版中國文學史,怎樣論李白? 孫康宜主編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1.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 4 “The cultural Tang”由宇文所安撰寫。在這一章之中,李白受到的注視大幅下降(p.307-308)。
宇文所安似乎有意脫離“以名家、名作爲本”的撰史傳統(文學正統觀),他沒有爲李白辟出一個專節,也沒征引脍炙人口的李白絕句(比較:宇文所安《盛唐詩》一書中,辟出一章即第八章論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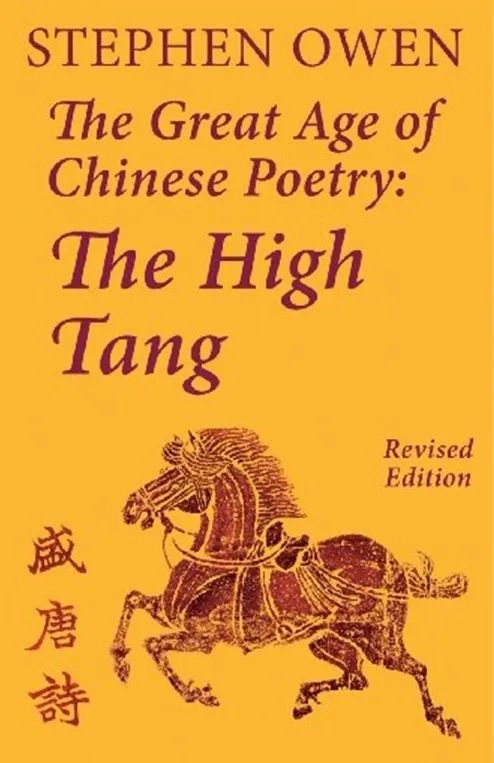
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另一部英文版文學史是Victor H. Mair 主編的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書中第十四章也談及李白(p.296-298)。此書第14章重視李白的樂府詩、古風、賦,最後也指出:Li Po is also hailed as an uncommon master of the briefest form of verse, the quatrain, ……(Paul Kroll語)。所謂the quatrain, 就是“絕句”。
和上面兩種英文版文學史相比,張隆溪教授書中第七章 (The Twin Stars of Tang Poetry: Li Bo and Du Fu) 就有設四個小節談李白,包括李白和杜甫的交誼。張教授這樣編寫,稍微有紀傳體史書的形迹。(日本岡村繁撰《李白新論》,其“新論”是敘述李白的一生遭遇,更像李白傳記。參看岡村繁《陶淵明李白新論》,2002年)。
張隆溪教授很欣賞李白絕句,他爲讀者翻譯了好幾首。翻譯涉及選詞用字,選對了字詞,能貼近原義,比如《早發白帝城》末句“輕舟已過萬重山”許淵沖譯成My skiffhas left ten thousand mountains far away.(《唐詩三百首新譯》,頁92) 許淵沖用了skiff, 大概因爲skiff確實較貼原義。另一方面,如果選錯了字詞,譯文會損害原作者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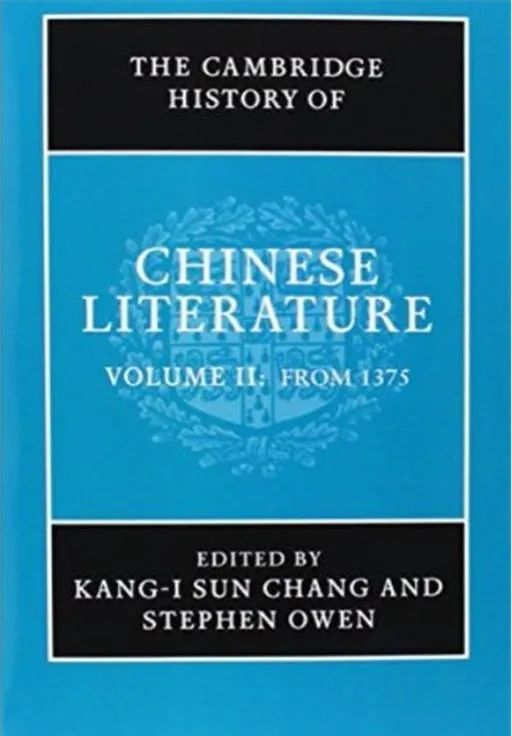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有時候,譯者的“選擇(詞語)意識”顯得不夠強,這可能緣自文學觸覺欠靈敏,也可能是因爲對“目標語”(target language)語義場的認知不足。當然,翻譯過程中(process)偶然失誤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張教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的Preface中說:How well translations in this book serve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is a question I leave entirely to the reader to judge. 這句話,再結合他在各演講中的論述,意思大致是:本書之譯文佳否,能否達意,能否做到讓中國文學爲“世界”所認識,皆由讀者自行評斷。
張教授說過,他撰寫英文版中國文學史,是希望域外讀者也能多讀到中國文學作品,所以,他書中征引作品不少。我們翻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見全書沒有一個漢字,因此,讓讀者讀到的,其實是經過翻譯的作品。 李白絕句的英譯版本,是否受英語讀者所激賞?譯文有沒産生不必要的聯想?

梅維恒主編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版。
這類問題是值得研究的,因爲翻譯將涉及諸多問題,例如,譯者的中介因素 (the translator as Mediator)也不容忽視。
本文只探討個別問題,僅能做到管中窺豹,筆者的目標也不是要全面評析張教授的翻譯。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引發的其他話題,當另文探討。

放二氧化碳!李白最拿手的是古風,張口就來,七句,八句,十句,十二句隨他!他最拽的、思想最深刻的詩,都在第二卷古風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