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和校長最後相會在病房裏。
1961年,台北。
中國目前最牛的兩所大學的曾任校長——梅贻琦和胡適,相繼因病住進了台大醫院。
期間,兩人常到對方的病房裏互相探望,聊聊往事。
胡適根據梅贻琦的病情研判,預感年長自己兩歲的老友,可能將不久于人世。于是,在交談中,他委婉地勸梅贻琦先准備一份遺囑,不論公事、私事,立個字據,給自己也給後人一個明明白白的交代。
梅贻琦聽完,默不作聲,胡適不好再說下去。

1961年,梅贻琦在病房裏探望胡適
人生無常。1962年1月病愈先行出院的胡適,竟在一個多月後的2月24日突發心髒病,走在了梅贻琦前面。
物傷同類。噩耗傳到台大醫院,梅贻琦深感悲痛,病情加重,幾度昏迷不醒。
苦苦支撐了兩個多月,73歲的梅贻琦在1962年5月19日與世長辭。
清理遺物時,秘書發現了病床底下一個手提包。梅贻琦生前經常隨身攜帶,視爲珍寶,但從未當衆打開,不知道裏面裝著什麽東西。秘書遂將手提包封存起來。
後來,當這個手提包在衆人面前被打開時,所有人都驚呆了,隨之熱淚盈眶。裏面裝的,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本,每一筆賬都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梅贻琦的夫人韓詠華說,梅贻琦沒有留下任何財産,所有的話都在病床上講完了,也就無需寫什麽遺囑了。
胡適是公認的大師,新文化運動的巨擘,但從來沒有人稱梅贻琦爲“大師”。他也從不覺得自己有資格稱什麽“大師”。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平淡無奇、兩袖清風的人,在任清華大學校長期間,爲清華請來了衆多的大師,爲後世培養了衆多的大師。
人們稱他,永遠的校長!

梅贻琦,1889—1962
11931年底,清華大學迎來了新掌門人。
在校長之位空缺了大半年之後,梅贻琦從美國回來,走馬上任。
當時而言,這不是一個好差事。在他之前,羅家倫、吳南軒兩任校長都铩羽而歸,且留下“罵名”。
當局起初並未想到梅贻琦這名“寡言君子”,直到校長人選考察了一大圈之後,發現實在無人勝任,才決定請他來試一試。
梅贻琦的內心是拒絕的,但他對母校有情結,最終決定把自己豁出去了。
政學兩界中人都知道,清華的校長很難做。
最難之處在于平衡各方的關系:教授想要自由學術和治校權力,愛國學生想要運動救亡,國民黨當局想要黨化教育進大學……
清華是美國用庚子退款辦起來的,還要考慮美國人的想法。
個中關系,錯綜複雜。
按時人的判斷,合格的清華校長,至少須獲師生、美使館、教育部同時認可。其條件應當包括:
1、清華“土著”出身,有人脈和器局;2、有美國背景,善于與美使館打交道;3、南京國民政府不反對,政治上無問題。梅贻琦是在符合上述條件後,獲得推薦上任的。時任教育部長李書華認爲,梅贻琦是個“很誠實而肯負責的人”。

清華大學
在就職演講中,梅贻琦說出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最振聾發聩的一句名言: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說,辦大學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研究學術,一個是造就人才。爲了實現這樣的目標,一個是要有設備,另一個是要有教授。
“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一個大學之所以爲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由此,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大師與大樓”論,並提出要延攬人才,尊敬在校的教授。
多少年來,大家都記住了他的“大師與大樓”論,但很少人知道,他演講的另一層主旨,是在教學生怎樣真正的愛國。
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爆發,東北淪陷,中日民族矛盾繃到極點。年輕人對政府的退讓政策相當不滿,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導致正常的大學教學常常難以進行。
梅贻琦在演講中專門提到,“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則”。但是,他特別強調說:
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爲國家服務。在接下來做校長的日子裏,梅贻琦要面對的,正是如何在政治與學術的博弈中,將清華建設成中國最好的大學。

一代斯文梅贻琦
2梅贻琦最大的特點是,他身上“官氣”淡薄,溫文爾雅的學者風度外顯,行事低調,待人謙和。
有人評價說,梅贻琦“像是一個偶然被放到校長位置上去的優秀教師”。
對此,清華的教授們看得分明,始終把他當成圈內之人。
早在1928年,清華學校正式升格爲國立清華大學之時,梅贻琦就是當時的第一任教務長。而且,這個教務長是教授們投票選出來的。
47張有效票,梅贻琦得到33票,高票當選。
他的夫人韓詠華說,那時清華教授中,有博士學位的大有人在,爲什麽選中了只有留美碩士學位的梅贻琦?“我認爲這是大家對他人品的信任。”
梅贻琦是天津人,在他10來歲時,家境衰落,而兄弟姐妹衆多。他是家中長兄,從小幫助撫育弟妹。1909年,20歲的梅贻琦以第六名的好成績,考中首批庚款留美生。次年入讀美國伍斯特工學院,專業是電機工程,4年後拿到學士學位後即回國。
在當時的留美浪潮中,許多人都入讀美國常青藤名校,並讀到博士才回國,而梅贻琦走了一條很偏門的道路。
一個主要原因可能是,他需要趕緊賺錢,幫忙養活一個大家庭。一直到他30歲結婚後,仍用每月三分之二的薪水接濟弟妹們。在他參加工作七八年後,他才重返美國讀了個碩士學位。
1915年,他應聘到清華學校教書,僅教了一學期,就告訴他中學時代的老師張伯苓,說他對教書沒興趣,想換工作。
張伯苓對他說:“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願意幹了,怎麽知道沒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當時只有26歲的梅贻琦,接受了張伯苓的勸誡,此後再未離開清華。

梅贻琦(左三)與胡適(左二)等人合影
在梅贻琦當校長的年代,中國大學的自由之風,以及蔡元培當年在北大奠定的“教授治校”規矩,已經開始遭到時代的沖擊。尤其是,國民黨當局一直想要在著名高校中找到能夠代表官方意志的人物,以便實現政治的滲透與控制。
連幾乎與梅贻琦同時執掌北大的蔣夢麟都說,他不信奉“教授治校”,只信奉“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毋庸置疑,這已隱然在加強校長的權力。
但梅贻琦卻把蔡元培當年在北大的作風,帶到了清華。
梅贻琦這樣形容校長的工作:“一個學校,有先生上課,學生聽課,這是主要的。爲了上課聽課,就必須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類,因此也需要有人管這些方面的事。一個學校的校長就是管這些事的人。”
這是一種打趣和謙虛的說法,但確確實實表現了這名大學校長骨子裏的服務精神。
他還經常說,他就是京劇裏的“王帽”,穿黃袍當皇帝,端坐舞台中央,看似地位崇高,無比威嚴,但其實只是個配角。
真正的主角,是大學裏的教授。
梅贻琦的法寶是三個字——“吾從衆”。身爲校長,奉行民主,不獨攬大權,校內大事皆由教授評議會民主決斷。他不愛說話,也沒人見他紅過臉,因此得了個“寡言君子”的名號。
曾在清華任教的蔣複璁說:“初以爲辦公事他不大內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
清華在梅贻琦的手上,不僅穩住了局面,而且增設工學院,師資越來越強大,迎來了校史上的黃金時代。
至抗戰前夕,已經從當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發展爲與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國最高學府。連曾任北大校長的胡適,都說過,清華的畢業生比北大的更搶手。

梅贻琦與夫人韓詠華
3時代卻總與梅贻琦過不去。
如我前面所說,梅贻琦執掌清華的年代,正是學潮的井噴期。民族矛盾與學生運動強烈對沖,當局所渴求的大學秩序,隨時被沖得七零八落。
難得有梅贻琦這樣的校長,對教授不爭權,對學生則有擔當。
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傳言軍警要進清華抓學生。
葉公超、馮友蘭等多名清華教授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議對策。大家焦急地等待校長表態,但梅贻琦始終不發一言。
馮友蘭說話有些結巴,迫不及待地問:“校長,你,你,你看怎麽樣?”
葉公超也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考慮此事而不說話?”
梅贻琦這才回答:“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
後來軍警果然進校抓人。
激憤的學生懷疑校方向當局提供了學生名單,遂圍攻教務長潘公旦。他們奪過潘公旦的拐杖,扔在地上,還要毆打他。
關鍵時刻,路過的梅贻琦看到這一幕,快步走到潘公旦前面,厲聲對學生們說:“你們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們如果認爲學校把名單交給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負責。”
學生被他的威嚴鎮住,悻悻離去。

“一二九”學生運動
在這之後,梅贻琦在集會上告誡學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
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們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准確 。”
末了,他表示:“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上的獨立。”
事實上,梅贻琦並不贊成學生搞愛國運動,他向來認爲,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好好學習,將來才能報效國家。
學生領袖要搞罷課,要把學生隊伍拉到校外,他決不答應。勸阻不聽,他就動用校規,處分學生領袖,甚至開除學籍。
但是,當當局要逮捕學生時,他總是通知名單上的學生立即離校,藏到安全的地方躲避風頭。他曾把一名姓郭的學生領袖藏在汽車後面的行李箱中,駛出城外,確保其安全。
真有學生被捕了,他也總是想盡辦法,進行保釋,絕不會坐視不管。
後來,學生們均能體會梅贻琦的苦衷。他們模仿梅校長的口吻編了個順口溜,還原了梅校長與當局周旋保護學生的應對之策: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爲,恐怕仿佛不見得。在梅贻琦任校長之前的20年裏,清華走馬燈似的換過十余任校長。期間,不乏學生驅趕校長下台的先例。但梅贻琦卻從1931年起,至1948年底離開北平,連任了長達17年的清華校長,地位和威望無可匹敵。
有人問他:“怎麽你能做這麽久的校長?”
梅贻琦只是風趣地說了一句:“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黴(梅)。”

劇照:祖峰飾演的梅贻琦,像吧?
4曆史的吊詭在于,國家的至暗時刻,誕生了大學的最高神話,迄今難以超越。
關于西南聯大的傳說和成就,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不用我再來說這所僅存在8年的大學有多牛掰。
當年,英國的科技史大師李約瑟參觀西南聯大後,深爲中國學人的水准所驚訝,並稱西南聯大等校“可與牛津、劍橋、哈佛媲美”。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西南聯大的實際操盤手正是梅贻琦。
西南聯大三校的校長,分別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在聯大成立之初,張伯苓就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著。”(意思是你做我的代表。)而蔣夢麟則放心地對梅贻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梅贻琦,字月涵)多負責。”還說,聯大的事,我不管就是管。
這樣,聯大三駕馬車中,張伯苓和蔣夢麟實際上當了甩手掌櫃,常年在重慶兼任國民政府的其他職務;三人中最年輕的梅贻琦,出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是西南聯大的實際負責人。
那時的西南聯大一座大樓都沒有,卻是大師如雲,精英遍地。梅贻琦的貢獻無人能比。
在抗戰之初,國民政府曾設想組成東南、西北、西南三所聯合大學,共赴國難,爲中國的高等教育保存火種。不過,東南聯大胎死腹中,西北聯大先和後分,只有西南聯大堅持到底,“八年之久,合作無間”。爲什麽?
西南聯大的成功,關鍵就在梅贻琦的格局、管理能力和奉獻精神。他擔得起大學的重任,是因爲他放得下的東西比別人都多。
三校合並,從體量上講就不對等。當時清華的規模最大,無論是設備、經費,都優于北大和南開。從人員比例看,清華、北大和南開之比大約是7:5:2。
我們知道,中國人骨子裏的斤斤計較、狹隘和權鬥貫穿整部曆史,從不因國難或其他困難而稍減。所以合並之時,清華人已經覺得吃虧,而北大、南開又覺得自己將被清華壓倒,這個事,處理不好,隨時就一拍兩散。
在人事方面,梅贻琦平衡得很好,這個學校去個教務長,那個學校去個訓導長,各個系主任基本上匹配得很微妙。
當時,聯大師生生活清苦,清華工學院用自有的設備成立服務部,用賺來的錢補貼教師生活。梅贻琦在年終分配時,顧念北大、南開的教師,也給他們多分了一個月工資。類似公正無私的行爲,梅贻琦經常幹。
即便如此,西南聯大也差點散夥。
國民政府在分配教育經費時,不把聯大看成三所學校,而當做一所學校進行分配,導致聯大經費緊張。清華有庚子賠款,但北大和南開向來指望政府撥款,這就使三校産生了矛盾。
最後,蔣夢麟說,不合作了,北大的經費獨立。他希望三校拆分,有利于向政府爭取經費。
梅贻琦也有些怨氣,曾向北大的鄭天挺說,讓蔣夢麟當西南聯大主席至少一年。意思是,要當家才知道這個一把手真的很難做。
西南聯大最終在經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合作並維持下來,梅贻琦實在受了不少委屈。

西南聯大
國民政府明知西南聯大是三校合作,卻故意在經費上只分一份,意在刁難聯大。至于原因,則是國民黨當局一直想控制高校,推行黨化教育。一個突出標志便是,黨、團組織開始進入西南聯大等高校,並硬性要求學院院長以上人員必須加入國民黨。
無黨無派的梅贻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委曲求全,加入國民黨,並成爲中央委員。
但他仍舊奉行學術自由原則,該頂就頂,希望減少政治幹擾,還大學以單純和甯靜。抗戰勝利後,他曾向教育部長朱家骅建議:1、大學可否不設訓導長?2、三民主義青年團可否不在校內設分團?
1945年,昆明發生“一二一”慘案。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爲死難者送葬,拄著手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並撰文號召“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迹”繼續戰鬥。
教育部長朱家骅爲此多次會見梅贻琦,開口便提清華的左派教授問題。當局的意思很明顯,即要梅贻琦免去聞一多、張奚若、潘光旦等左派教授的學校職務,甚至解聘更好。
梅贻琦壓力山大。但他始終虛與委蛇,未采取措施,直到1946年4月還續聘聞一多爲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倒是聞一多了解梅贻琦的苦衷,寫了長信力辭。
實際上,梅贻琦本人並不認同左派教授的觀點。他在日記中對聞一多等人的激進,“開謾罵之端”深感失望。但在大節之處,他仍盡力保護這些教授。
蔣介石曾爲此事召見梅贻琦,梅贻琦主動爲這些教授辯解,說他們最近的出格言行是一時沖動,原因是這些教授家屬衆多,生活非常困難,“于是愁悶積于胸中,一旦發泄,火氣更大”。蔣介石點頭,說生活問題確實至關重要。
梅贻琦對政治無興趣,但他並不傻。在最高領導人面前,把左派教授的政治立場簡單歸結爲經濟問題,旨在緩和雙方的對立關系。這是他爲人善良的地方,也是他作爲大學校長,守護學校、守護職員的天性所在。
梅贻琦曾說過,他對政治無深研究,但對于辦大學,他認爲:
應追隨蔡孑民(元培)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爲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爲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梅贻琦自任清華校長以來,就是蔡元培辦學理念的堅定追隨者。別人關心政治派別,他只關心學術自由。
然而,在動蕩的時局中,這種“超脫”的態度,常使他陷于無可奈何的苦悶之中。
1946年7月,聞一多被殺害。
梅贻琦悲憤欲絕。他一面妥善安排聞一多的善後,一面向當局交涉追查凶手,向報界發表談話,揭露特務的罪行。
爲防止類似慘案的發生,他將潘光旦夫婦、費孝通一家和張奚若安排到美駐昆明領事館避險。吳晗教授思想活躍,當局曾令清華解聘吳晗。梅贻琦一面拒絕,一面悄悄地通知吳晗離去。
對于聞一多遺屬的撫恤問題,梅贻琦也盡心盡力,每年都與國民政府教育部反複力爭。在聞一多夫人高孝貞率領子女奔赴華北解放區後,梅贻琦依然與各方交涉,請求從優撫恤。其爲人的厚道,可見一斑。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
51947年的清華校慶,是抗戰勝利後清華複校的第一次校慶。學校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後1909級,逐級向校長敬酒。
梅贻琦老老實實地幹杯,足足喝了40多杯。
清華人說,梅校長的酒量全清華第一。但事實上,這名老校長多次在日記中告誡自己要少飲酒。
他的好友、考古學家李濟說,看見梅贻琦喝醉過,但從沒看見他鬧過酒。
而這,可能成了梅贻琦在清華少有的快樂時刻。
1948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
梅贻琦搭乘飛機南下。南京國民政府再三邀請他入閣,並立即公布他爲教育部長,他堅辭不就,索性離開南京,暫住上海。
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此次南下,是爲北方各大學想辦法,不是來做官的。
他依然屬意教育,等到實在看清事無可爲,才決定出國。
他沒有直接去台灣,而是去了美國。
在紐約,他以清華大學校長的名義,掌管了清華在美國的基金。他要保證這筆基金的每一分錢都用于清華。
他從未忘記故國。
據說,他曾托熟人向北京的清華大學表示,可以用清華基金購置圖書、儀器。但鑒于當時情勢,這個建議沒有得到落實。
他早年在南開的校友周恩來曾發表談話說:“梅贻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
不知道梅贻琦是否聽到這個話,總之沒有回應。不過,1954年3月,他的兒子梅祖彥在美國完成學業後,決定回北京,爲新中國服務。梅贻琦不鼓勵,但也不阻止,尊重了兒子的個人選擇。

梅贻琦夫婦與兒子梅祖彥合影
台灣方面曾派人到美國遊說梅贻琦,讓他帶著清華基金回台灣。他總是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
他堅持不願拿錢蓋大樓,說清華的錢只能用于科學研究。
到1955年,他才只身回到台灣,籌建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就是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而這個新的清華,成了梅贻琦最後的寄托。
在他生命的最後年頭,他生病住院,竟然連住院費都交不起。如此清廉,讓清華校友潸然淚下。他們自發捐款,交齊了他的住院費。後來,同樣住院的胡適,也偷偷給梅贻琦捐了500美元。
梅贻琦逝世後,沒有留下任何遺産。僅有的,是兩岸兩個清華“同一個校長”的傳奇。
正如清華老校友所說:“他在母校十幾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貪汙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的地步,真是聖人的行爲。只這一點,已足可爲萬世師表。”

病床上的梅贻琦
他的事迹,在清華的新老校友中流傳。
西南聯大時期的清華曆史系畢業生孔令仁曾回憶說,西南聯大辦了一個附中,由于教學質量高,雲南省主席龍雲送女兒龍國璧去報考,結果竟然沒被錄取。龍雲很生氣,認爲梅贻琦不給面子,就派他的秘書長去疏通。
誰知秘書長久久沒有行動,龍雲氣不打一處來:“你還站著幹什麽?”秘書長說:“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龍雲一聽,氣都消了,從此對梅贻琦更加敬佩。
梅贻琦的夫人韓詠華說過,梅先生自己從不托人情去辦什麽私人的事情。
梅贻琦的一生只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奠定了清華的地位與校格。僅憑這一點,他已是那個年代最牛的校長,更難得的是,他的人格,讓他的校長之名臻于完美,至今讓人懷念。
著名教育家傅任敢評價梅贻琦的一段話,深得我心:
他愛學校,所以把他一生獻給了學校。他愛國家,所以在抗日時把他的兒女打發到遠征軍去。他愛國事,所以待人一視同仁,從無疾言厲色。他尤其愛青年,所以每次的學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護著青年的安全。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學校爲幌子而達到了自己升官發財的目的,我們便知道真愛學校之不易。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經大聲疾呼地叫人愛國救國,自己卻無貢獻,或且因而有所收獲,便知默默無言地做著愛國工作之難能。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辦學的人視辦學如做官,視學校如衙門,趾高氣揚,頤指氣使,便知一個大學校長之有禮地對待一切人們之可貴。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經愛護青年其名,出賣青年其實,或者愛護其名,放縱其實,甚至利用其實,我們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我們要有根基深厚的愛,育人才有著落。1962年,梅贻琦逝世後,治喪委員會建議把梅校長安葬在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
這個決定引起了一些爭議:如果每一位校長死後都葬于校園之內,那將來校園不就成爲校長墓地了麽?
治喪委員會不爲所動,仍然將校區內一個山坡上的一片相思林地劃作了校長的墓園,這就是今天的新竹清華大學的梅園。
治喪委員會表示:“我們認爲,以梅校長和清華的關系,不是任何一個大學校長和學校的關系所能比擬的。其他學校的校長,不可以校園做墓園,但是梅校長卻可以,因爲清華和他已經融成一體了。”

梅贻琦魂歸處:新竹清華大學梅園(新竹清華官網)
2005年,李敖在北京清華大學演講,說台灣有一個“假清華”,但有一位“真校長”。
世間已無梅贻琦。
參考文獻:
梅贻琦:《梅贻琦日記(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
黃延複、鍾秀斌:《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贻琦》,九州出版社,2011年
劉述禮、黃延複編:《梅贻琦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嶽南:《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贻琦傳》,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
[美]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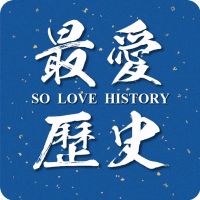
真清華已經搬走了,現在的只是占了原址的冒牌貨
獨立的人格,不論政治,學術至上,培養人才,愛國情懷
名族脊梁!
對,當年西南聯大寄居雲南,龍雲可是雲南王,梅校長這種風骨真是讓我輩汗顔。
我記得龍雲的兒子沒考上,龍去找梅說情,結果發現梅的女兒也沒考上,龍讪讪而退。
協和醫院是美國人投資的!美國人收利益了嗎?!
中國之脊梁者,中國之真正知識分子也!中國之教育魂魄者,如私人也!
蔣介石曾爲此事召見梅贻琦,梅贻琦主動爲這些教授辯解,說他們最近的出格言行是一時沖動,原因是這些教授家屬衆多,生活非常困難,“于是愁悶積于胸中,一旦發泄,火氣更大”。蔣介石點頭,說生活問題確實至關重要。
胡適先生固然牛掰 可作爲駐美大使期間,先生拿了幾十個博士頭銜 這確實是有點過于愛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