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薩沙曆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本文章爲薩沙原創,謝絕任何媒體轉載
有人說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隊非常懼怕福建軍民,這是真的嗎?福建軍民是如何抵抗的?1938年5月10日:日軍占領廈門。
確實如此。

福建是中國的重要沿海省份,也是中國比較重要的省份。
奇怪的是,二戰中的日寇沒有占領福建全省,僅僅占領了福州和廈門等沿海城市,基本放棄了福建內陸地區。
爲什麽會這麽做?
是有原因的。

其一就是,福建地形阻礙了日寇進攻。
早在清末,英國人曾強行開辟福州爲通商城市,然而沒多久就基本放棄了。
原因不複雜,福建大部分地區都是山地,交通相當不便。
福建北部的浙江省地形是多山地,叫作七山二水一分田。
福建就更誇張,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福建全省長寬都有500多公裏,其中高達75%地區爲山地,丘陵則有15%,兩者相加高達90%,平原只有10%。

關鍵福建的山地不是北方那種單純的黃土山或者岩石山,地形非常複雜,植被還非常茂盛。
沒有鐵路時代的福建,省內運輸完全依靠公路,准確說是山路,是非常困難的:福建民間,有“閩道更比蜀道難”的說法。北宋熙甯十年(公元1077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由江西到福建,他六月從老家江西南豐出發,八月才到福州。直線距離僅300公裏,途中竟整整走了兩個月。曾鞏應郡守程師孟之邀作《道山亭記》,文中就先用了一大段筆墨來吐槽,記述這一趟行程的山路艱辛,走得太不容易了。“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驿乃一得平地。”“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發,或側徑鈎出于不測之溪上。”“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踬也。”
資料中這麽寫:在福建民間,有“閩道更比蜀道難”的說法。從關中入川的路線雖然異常險峻,但越過秦嶺、進入蜀地之後便是內部交通便利的四川盆地,號稱“天府之國”。
入閩的道路則不同,福建北有仙霞、西有武夷、南有博平諸大山脈蜿蜒邊境,把閩地和外界割裂開來;閩中則有鹫峰、戴雲兩山脈,從東北至西南貫穿腹地,山地和丘陵約占全省總面積的90%。閩地的河流也大多自成系統、互不貫通、獨流入海。

可以想象,當年近六旬的曾鞏從江西翻過縱橫550公裏、平均海拔1000米的武夷山脈後,滿目依舊是丘陵山巒延綿不絕時的心境。
直到清代,福建全省才有五條出省驿道和七條縣際驿道。那麽,這幾條道路狀況如何?閩浙、閩贛、閩粵,每一條驿道都需翻越連綿不絕的山林溝壑,一路山高水險,野獸蛇蟲出沒,更可怕的是沿途強盜土匪衆多,危機重重。
到了新中國建立,福建省內交通運輸仍然是大問題:據《福建省志·交通志》記載,截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福建全省69個縣市,有46個縣市不通汽車,其中有18個縣沒有一寸公路,勉強可通車的公路只有945公裏。民營汽車運輸企業由1933年最高峰時的110家降至28家,全省僅剩客、貨車863輛,其中大部分破爛陳舊,停駛待修。

福建省內交通困難,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出現了大量不同方言:現代漢語有七大方言,福建就有五種,閩語、客家語、贛語、吳語和官話。而閩語又包括閩北語、閩東語、閩南語、閩中語四種,同一語言中,又有腔調發音的不同。在福建,兩個村子明明只相隔一座小山、一條小河,方言卻可能有極大不同,互相雞同鴨講。

第二,福建的資源匮乏。
福建山區從古至今,也不是什麽富裕的地方。
山區的出産很少,資源也匮乏。退一步說,就算山裏有資源,也難以運出來。
明代之前田少人多出産少,福建山民連生活都非常困難。
一旦遭遇荒年,福建山區就會出現大面積饑荒。由于地形原因,政府救災都很困難,饑民大量餓死也不稀奇。
爲什麽宋元明清時期,全國甚至全世界都有不少福建商人或者打工者?
就是山區養不活這麽多人,只能背井離鄉討生活。

紅薯這種重要的作物,本來生長在美洲,被西班牙殖民者帶到了殖民地菲律賓種植。
有趣的是,紅薯之所以傳入中國,就是因爲福建人的自救。
明代一個秀才陳振龍,目睹家鄉福建長樂無田無糧,無可奈何下只能放棄科舉考試轉而經商,先養活自己再說。
陳振龍在菲律賓經商成功,賺了很多錢,卻在1593年接到老家遭遇大旱災的消息。
陳振龍已經將妻兒接到菲律賓,不會因此餓死,卻心憂炭家鄉人。
自古救急不救窮,福建各地饑荒已經持續了上千年,總要找到解決的辦法。
聰明的陳振龍突然想到了菲律賓山區種植的紅薯,這豈不是福建人的救命糧食?
紅薯的藤蔓郁郁蔥蔥,一鋤頭下去能挖出一大串的果實,産量十分大。關鍵是,紅薯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烤著吃,煮著吃,飽腹感很強,很耐餓。
而紅薯最牛逼的在于抗旱,同像魚一樣需要水的水稻相比,紅薯幾乎不喝水。
同時,紅薯還能夠大量在山地種植,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和人工培育,産量又很高。
這種適合在缺水山區種植的東西,簡直是福建山民的救命糧。

陳振龍冒著生命危險,好不容易將紅薯帶回福建,由此改變了當地的生態。
很快,福建的大多數地方都種上了紅薯,饑荒問題也被解決了。巡撫金學曾在陳振龍紅薯種植方法的基礎下,寫出了我國第一部薯類專著《海外新傳》。而由于菲律賓當時屬于番邦外國,所以又把紅薯叫做番薯。在饑荒年間,有句話叫做:“鄉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意思是大多數百姓在饑荒年間都是靠紅薯活命的。
上面扯了這麽多,只是說明福建山區的資源匮乏,甚至糧食都不足。
在日寇看來,占領這些山區的意義不大。不能借此搶奪到財富和資源,日軍又何必全面出兵?
所以,日軍占領了福建沿海一些城市以後,就沒有繼續深入內陸。

第三,福建人不好惹。
不要說古代的福建,就算改革開放前的福建,同今天也有很大區別。
福建的鄉下由于常年閉塞,非常保守。
即便宣揚了多年的馬列主義,共産主義思想,鄉民的宗族觀念很強,只相信同姓血緣。
同姓的鄉民多聽族長的,不聽政府幹部的。
同時,福建山民性格凶悍,好勇鬥狠,可不好惹,最好的表現就是宗族械鬥。

清代學者趙翼說 :“閩中漳泉風俗好名尚氣”、“民多聚 族而居 , 兩姓或以事相爭 , 往往糾衆械鬥 , 必斃 數命 , 當其鬥時 , 雖爲翁婿、甥舅不相顧也。”
清嘉道間的張嶽崧也說 :“閩之漳泉 , 粵之潮嘉 , 其俗尚氣好鬥 , 往往睚眦小忿 , 恃其族衆 , 聚黨至千百人 , 執铤刃火器 , 訂期而鬥 , 死傷相屬 , 或尋報複 , 世爲仇雠”。諸如此類的記載與說法在沿海地區的方志中屢見不鮮 。
直到民國時期,福建宗族械鬥是尋常事,當地人毫不稀奇。尤其是很多敵對宗族,早在明代時期就已經械鬥結怨,之後互相仇視數百年,直到今天還有不能通婚的族訓。
在清代,福建宗族械鬥已經成爲動搖政府統治的嚴重問題。很多宗族內的男性,有百分之七八十參加過械鬥,搞出人命更是稀松平常。
清代統治者唯恐地方失控,一再嚴厲打擊:雍正皇帝不得不于雍正十二年頒布訓戒漳泉械鬥的谕旨 , 文說 “朕聞閩省漳、泉地方 , 民俗強悍 , 好勇鬥狠 , 而族大丁繁之家 , 往往恃其人力衆盛 , 欺壓單寒 , 偶因雀角小故 , 動辄鄉黨械鬥 , 釀成大案。及官司捕治 , 又複逃匿抗拒 , 目無國憲。兩郡之劣習相同 , 而所屬之平和、南勝一帶尤爲著名 , 此中外所共知者。”
只是,曆代滿清皇帝的各種政策全然無效,地方上該打還是打。

到了清末民國初期,宗族械鬥更是誇張。除了械鬥武器轉變爲火器以外,打鬥時間也從幾小時或者一兩日,變爲數十天甚至數月。有的宗族大規模械鬥,可以斷斷續續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從爸爸一輩打到兒子。
光緒年間晉江的都、蔡兩個宗族械鬥 ,雙方械鬥時間持續長達6年之久 , 死亡300余人 , 傷者無數,時田無余谷 , 民不聊生。
關鍵在于,這種規模宗族械鬥還不算非常大的:在沿海地區的諸多械鬥案件中 , 影響面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的械鬥當屬仙遊的“烏白旗械鬥”和泉州的“東西佛械鬥”。 據施鴻保《閩雜記》記載 : “烏白旗之始 , 起于仙遊洋寨村與溪裏村械鬥 , 洋寨村有座大帝廟 , 村人執廟中烏旗領鬥獲勝 ; 溪裏村有天後廟 , 村人遂執廟中白旗領鬥亦勝。由是二村械鬥常分執烏白旗 , 各近小村附之 , 漸及德化、大 田、南安等處 , 一旗皆萬余人 , 烏旗尤強。”烏白旗械鬥不僅播及閩南廣大地區 , 同時對莆仙地區的影響也頗大。且延至解放前夕。
泉州的“東西佛械鬥”則更爲複雜 , 傳說是 清康熙年間施琅和富鴻基兩家族挑起的 , 漸蔓延 至泉州市區、市郊外及晉江、惠安、南安各鄉。只因口角細故 , 導致大動幹戈 , 據吳增《上香山》詩描述 : “東佛去取火 , 西佛去接香 , 旗鼓各相當。最怕相逢狹路旁 , 狹路相逢不相讓 , 流 差蓦地相打仗 , 打仗打死人 , 石片彈子飛如塵。 東家婦 , 西家叟 , 茫茫喪家狗 , 孩子倒繃走 , 神 魂驚去十無九。後年五六月之間 , 怪汝又去上香 山。”
滿清統治者煩惱于福建宗族械鬥,地方官更是苦不堪言,甚至不惜辭職回家,還四處抱怨:“無日不鬥、無地不鬥、無族不鬥”。

民國時期,宗族械鬥規模稍小,仍然多如牛毛:民國年間 , 泉州東門外 田園坑與後園爭奪水源發生械鬥持續 7 年之久。 晉江陳埭西邊村與高岑村因爭奪沙塘引起械鬥 , 延續15年 , 雙方各有死傷 , 連孩子都不能幸免。
這些宗族械鬥可不是只是針對敵對宗族,而是誰敢來惹事就打誰,連政府軍也不放過:民國十三年 , 安海發生黃、顔、張械鬥 , 駐泉州北洋軍閥孔昭同派兵彈壓 , 結果反遭張林村村民的武裝反抗 , 軍隊反被打死27人 , 其中一名是連長。
福建宗族不好惹,而日軍是聲名狼藉的獸人軍隊,所到之處都是燒殺淫掠。
以福建山民的性格,肯定要同你拼命,絕對不會坐視不理。
日軍攻打廣西、湖南期間,當地民衆也是奮起抵抗。
以攻打廣西爲例,幾乎村村都有民團鄉勇襲擊日軍,老頭、少年都操起土槍射擊,日本人到處挨打。
可以預計,只要日軍深入福建山區作戰,一定會遭遇同樣的情況。更要命的是,福建山區簡直就是中國版的阿富汗,是非常適合打遊擊的聖地。當地鄉民熟悉地形,利用山地頻繁襲擊日寇,後者根本沒有辦法。
即便不在山區,福建人也是不好惹的。

大家看看這個戰例。
日軍在1944年突然第二次攻打福州,全市軍民立即撤退,只留下消防大隊進行滅火。
沒想到,日軍進軍速度很快,部分老百姓沒有來得及撤退就被包圍,包括消防大隊的戰友和民衆。被包圍的民衆,除了《南方日報》社福州分社、一些外籍人士,還有協和高級護士學校的護士。這些女護士如果落入日軍手中,後果不堪設想。
可惜,國軍正規軍都撤退了,情況十分危急,只能讓負責滅火的消防大隊自行援救。
消防大隊哪裏有救人的能力,只能向當地鄉民要求幫助。由于日寇在福州附近燒殺,引起了鄉民的極大仇恨,人人都願意打鬼子。
一瞬間,青年團福州戰地青年服務隊、福州青年國術社、閩侯縣民衆抗敵自衛隊等五花八門的團體都願意參加行動,很快拉起了300多人。
人數似乎不少,武器極爲差勁,只有一些老舊步槍,一挺有故障的輕機槍,所有人都沒有作戰經驗,有的甚至不會開槍。
在300多突擊隊員反攻入福州城時,一些當地民衆竟然紛紛拿著土槍、大刀、長矛甚至扁擔,主動加入部隊,一起參加反攻。
經過殘酷的肉搏戰,他們終于救出大部分被圍困的平民,斃傷日寇20多人。

突擊隊畢竟不是正規軍,戰死29人之多,受傷數十人。犧牲的除了突擊隊員,還有自發參戰的民衆,包括用竹扁擔殺敵的劉太平,手執木棍作戰的16歲少年鄭烏鼻,以及高擎國旗沖入敵陣搏鬥、年僅14歲的小學生柯雲炳等。
看看,拿著木棍扁擔都敢同日本人幹仗。
這段時期,日軍在福州到處遭到打擊:日軍“不敢單人出行,出則武裝結隊”,“入夜即告戒嚴,蓋敵懼怕我突襲之故”。
這還是在地形平坦的福州,如果日寇深入山區又會如何?
其實,日軍曾經做過評估,認爲占領福建全省需要駐紮10萬以上軍隊。由于存在運輸瓶頸,日本根本無法維持這麽多駐軍的日常物資消耗,只能放棄了。

最後說一句,薩胖的祖籍是福建。
聲明:
本文參考
圖片來自網絡的圖片,如有侵權請通知刪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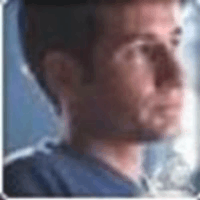
凶啊[笑著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