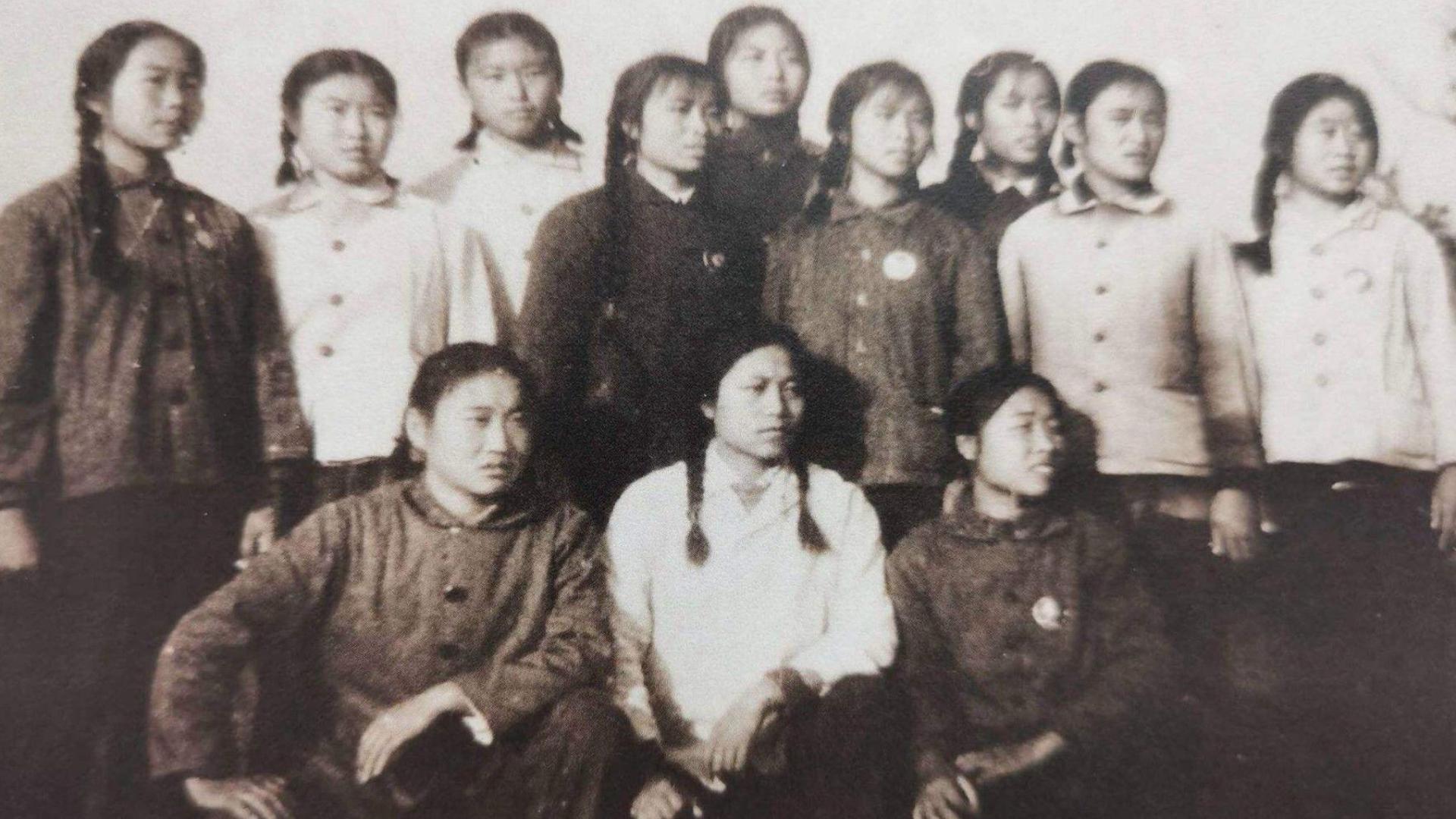1969年3月18日,一輛敞篷大卡車滿載著30多名知青,在陣陣冷風中緩緩駛進了黑龍江省富錦縣福民大隊的村子。車上的年輕人個個面色嚴峻,緊緊裹著棉襖,眯著眼睛,防備著北國的嚴寒。
到了目的地後,大家簡單整理了一下行李箱,互相攙扶著下了車。只見村子裏道路結了厚厚的冰,房屋的屋檐上挂著一串串冰淩,松花江的江面也早已被嚴寒封死。
一位身穿大氅的劉大嬸走了過來,那張布滿皺紋的臉上堆滿了和煦的笑容,就連她的眼角也因爲這濃濃的笑意而微微起了皺。

"哎,你們可算到了。聽說你們是從溫暖的南方來的,這會兒還適應不適應啊?"劉大嬸親切地打量著一行人,然後招呼大家先到她家歇息。
年輕人們連忙應聲,三五成群地跟著老人走進了一間小小的平房裏。房間裏只有一間小炕,擺著幾張舊木床和一張矮幾,但暖氣卻是充足的。大家圍坐在矮幾外,咂吃著熱氣騰騰的稀飯,感到渾身暖和起來。
一位娃娃臉的姑娘放下了碗筷,忍不住抱怨:"唉,沒想到來到這裏第一件事就是吃這些東西,以後的日子可就夠苦的了。"旁邊一位同齡人用手肘撞了她一下,小聲說:"這就是村裏普通人的夥食,不知吃的是什麽就先別嫌棄了。"
劉大嬸見狀搖了搖頭,柔聲說:"我就是村裏的五保戶,家裏也確實還沒有吃的,哪裏還能拿出什麽好東西來招待你們。等過兩天吧,你們也習慣了,咱們再好好聊聊天,今天就先歇息吧。這裏的日子雖然苦些,可人心卻是暖和的..."
第二天清晨,劉大嬸一聲雞鳴就醒了過來。她溫習了一遍農諺: "三月雷聲四月鳴,棚裏不去可傷情"。于是連忙做了些豆腐腦和鹹菜,准備給年輕人補充些營養。
待大家吃過早飯,她就催著大家去村口廣場集合,聽生産隊長安排今年的春耕計劃。看著年輕人們魚貫而出,熱血沸騰的樣子,她不禁感歎:"時代不同了,咱們做農活可要靠這些年輕力壯的新朋友了。"
生産隊長是個四十來歲的老者,滿臉皺紋,頗有些威嚴。他先是向來自城裏的知青們解釋了村裏的規矩,然後提出了今年的計劃。
第一批工作就是要先把拖拉機修好,爲春耕做准備。大約一半人要分頭去修理好幾台舊拖拉機,另一半的人則要負責備耕、澆地等工作。
計劃確定後,大家分了兩撥,一撥人立即開工准備修理拖拉機,拾掇起生鏽的鋼鐵和零件;另一撥人則從劉大嬸家領了鋤頭、鍬頭等工具,徒步前往幾裏開外的農田。劉大嬸看著他們漸行漸遠的背影,禁不住緊張起來。
下午三點半,修理拖拉機的人回來時,個個疲憊不堪。他們已經連續工作了六七個小時,中午也只草草吃了一口稀飯,就立即投入苦力活中。而劉大嬸早已在炕上鋪好了硬板,擺上了新切好的鹹菜和酸蘿蔔絲,等待著大家歸來。
年輕人們一進屋,就被滿屋的香味迷住了。一位體格相當高大的年輕人無意中掃了劉大嬸一眼,發現她此時正在用破舊的毛巾擦著因勞累而沾滿汙漬的雙手。那雙手上滿是老繭和傷痕,剛才在拉鋤頭時又磨出了新的血痕,看起來十分猙獰。
年輕人一時有些慚愧,默默吮吸著菜湯,消化著這一切。今天的體力活實在太過吃力,他幾乎要累垮了。而作爲一個七旬老人家,她卻一如既往地照顧著大家的飲食起居。他默默地想,以後一定得好好孝敬老人家才是。
經過兩個星期的努力,終于到了春分時節,天氣幹燥溫暖,終于可以開始大規模的春耕農活了。生産隊裏所有的成年勞力和知青們,都被分成七八個小組,分頭在各處開墾農田。
年輕人們個個精神抖擻,背上行李箱,拎著鋤頭鍬頭,在劉大嬸的催促下踏上了去向農田的路。沿途那些枯黃的樹杈已經開始微微發芽,清晨的霧氣籠罩著整個村子,清新而溫暖的氣息撲面而來。
到了農田邊,大家便開始分工作業。有一幫人在田邊重新修整著已填埋的水渠,以備灌溉用;有一幫人在徹底翻松土地,去除垃圾和石塊;還有一幫人專門在場邊集中裝填著麻袋施肥......
女孩子們也是個個幹勁十足,和男生們一起撸起袖子苦幹。她們全然忘記了自己曾經嬌貴的身份,卸下了粉黛重新露出了粗犷的本來面目。由于都是夥食太單一、勞作又太過吃重,她們的臉色都暗黃暗黃的,看起來很是憔悴。
而這個時候,劉大嬸的作用也就體現出來了。她總是首先到田裏來,端著一盆盆剛剛熬好的粘糊糊的高粱米飯和熱騰騰的蘿蔔菜。一到中午,大夥就像趕場的牲畜一樣,一窩蜂地把她的盆盆盤盤給圍住。
看著這群年輕人狼吞虎咽的樣子,她總是溫和地笑笑,叮囑他們慢點吃,給他們添上滿滿的一碗。看著他們年輕英俊的面孔上洋溢著朝氣,她也感到一股莫名的欣慰。
不知不覺,這樣的日子就過去了半個多月。期間,大家的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繭,卻也逐漸適應了這種艱苦的勞作生活。能夠一同同甘共苦,對于這群年輕人來說也是件極好的事。
到了四月下旬,時常有暴雨驟來,農活也就時常中斷。一次接一次的陰雨天氣,不但使農活無法進行,更讓眼前的糧食儲備捉襟見肘起來。
看著最後一點口糧,老大娘也開始焦慮了起來。她這一年的收成向來不太好,所以只能指望著生産隊及時調撥口糧。可是由于天氣惡劣,調撥也就無從談起了。
一天夜裏,老大娘獨自躺在炕上輾轉反側,聽著雨聲砸在窗戶上,她的心也跟著砰砰直跳。她實在沒想到今年會陷入這樣的困境,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左思右想,她終于下定了決心。
第二天一早,看著送行知青們上工的幾乎空空如也的口糧,她立刻拿出了自己藏在底箱裏所剩無幾的幾袋高粱米,准備與大家共同分享。
盡管她早已做好了這樣的准備,但當真正拿出來時,她還是不免有些心疼。但她更希望年輕人們能夠紮實地吃上飯,免受挨餓的痛苦。于是,她強壓住了心中的不甘與猶豫,端著盆盆粥來到了田間。
"哎,大娘,您怎麽又端來這麽多粥啊?"一位男孩子詫異地問道。老大娘笑著說:"是啊,我看咱們昨天晚上太少了,所以多做了些。快快吃吧,今天工作還很多呢!"
大家一邊吃著,一邊對視著,心裏都明白大娘在想什麽。看著她的眼神,大家心頭一陣溫暖,又痛下定決心要早日增産糧食,好好報答這位慈祥的老人。
就在這時,有人捧著幾個箱子走了過來,看樣子像是剛從車站接的包裹。"你們看,家裏人給咱們寄來了些吃的!"那人高興地說著,小心翼翼地打開了箱子。只見裏面裝滿了各種家鄉的幹果、鹵味和點心,看上去讓人食指大動。
大家見狀紛紛圍了上去,個個拿起來聞著,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有人連連贊歎:"太好了,這下大夥可以改善一下夥食,好好吃一頓了!"
看到大家如此高興,老大娘也止不住笑意。她招呼大家將東西拿出來分享,自己也湊到跟前,殷勤地將一大把花生米裝進了懷裏。大家見狀都紛紛把手裏的食物遞給大娘,示意她也應當多拿一些。
老大娘擺擺手笑著說:"夠啦,夠啦,你們自己先吃吧。"說著,她將手中的些許幹果遞給了一邊的一位瘦小青年,溫和地說:"小武,你就拿著先墊墊肚子吧。等下我回去還得給你們年輕人們做些熱乎飯。"
大家見狀都不禁熱淚盈眶。看著大娘如此無私慈祥的模樣,每個人心裏對這位年邁的老人都升起了一股深深的敬意和親熱感。

九月金風送爽的時節,生産隊新建的集體戶終于落成了。這是一間長約二十米、寬十米的磚瓦平房,中央有一個八九平方米的大炕,周圍擺放著雙層雙人床位,再配以兩張長條桌椅和一個大櫃子。屋裏雖然陳設簡單,卻也看上去舒適寬敞。
這一天,知青們把自己的行李箱從劉大嬸家一一搬了過來。他們打掃了一陣子衛生,又把自己的被褥疊好擺放在各自的床位上,對這個將成爲自己新家的地方可謂是期待已久。
天剛擦黑的時候,劉大嬸來到了這裏。她拎著一大包行李箱,面帶微笑地環視著大家。大家連忙把她請到了床邊坐下,有的人連忙沏上溫熱的泡菜湯,有的人忙著在大炕裏生上爐子 。
"大家好好的,可別這麽費事啊。"劉大嬸說著,伸手摸了摸旁邊正在忙活的一個姑娘的頭發,"我來 這就是想看看你們的新窩,順帶跟你們道個別罷了。"
"大嬸,您說什麽呢?"一位青年人連忙攙扶著她站起身來,"您就好好坐著,別張羅了。等會兒爐子熱了,我給您沏上一壺香噴噴的紅糖水,您就喝了再走吧。"
劉大嬸這才笑著重新坐下,拍了拍自己的膝蓋,長長歎了口氣。"唉,我就是覺得你們離開我家,心裏也是過意不去啊。我們可是一塊兒挺過來的,感情也是格外深的。不過現在你們有了自己的地方,我也就放心多了。"
說著說著,她便不自覺地落下了眼淚。大家見狀也都哽咽起來,個個低下頭去,不好再去直視她。
"大嬸,您就放心吧。"有人終于開口說,"我們雖然搬出去了,可您永遠都是我們的親人。以後我們一定要經常來看您,您也要常來我們這兒坐坐啊。"
"是啊大嬸,您就像我們所有人的親媽一樣。" 旁邊又有人附和著說,"您就放心吧,我們一定會好好孝敬您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安慰著老人,氣氛終于變得溫馨而親切起來。就在這時,爐子也熟了,大家簇擁著將老人讓進了炕裏。老人捧著熱氣騰騰的紅糖水,望著眼前這群年輕朝氣蓬勃的面孔,心裏無比慰藉。
翌年的三月,生産隊召開了一次動員大會,號召村裏的年輕人都要參加國家的建設,爲祖國的強盛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大會上充滿了振奮人心的呐喊聲,大有"惟予國家,國無求我"的豪情。
坐在人堆裏的呂志軍,一時激動得熱淚盈眶。作爲一名知青,他也曾參與過前幾年村裏各項建設的辛苦工作。如今國家召喚,他自然是第一批報名的人之一。
事後,呂志軍第一個就來到了劉大嬸家,把自己的決定告知她。老人聽後也只是笑笑說:"哎,你們年輕的,去奮鬥一番也是好的。不過以後可得常回來看看我啊。"
兩人就此相擁而泣,像極了一對母子。老人緊緊抱著他,似乎怎麽也不願放手。呂志軍也是一次又一次地親吻著老人的臉頰,祈禱著上天能夠保佑這個親人平平安安。
"大嬸,我一定會給您寫信的,時不時了解一下您的情況。等我幾年後回來,一定也要第一時間來看您!"呂志軍握著老人的手,鄭重地說。
老人慈祥地點點頭,握了握他的手。"去吧,去好好幹你的大事業吧。小明,你是我看著長大的孩子,你的前程自然是很光明的。我這把老骨頭,終有一天也要離開人世的,到時候就讓我安心地走吧。"
一個月後,呂志軍和其他幾位同伴就離開了富錦縣,奔赴了遙遠的部隊。在火車上,他時而回想起生産隊的場景,時而又想起劉大嬸慈祥的目光。他在心裏默默祈禱著,願這位老人家身體一直健康,希望下次回來時,還能再見到她。
轉眼之間三年就過去了,呂志軍已經是一名英勇的陸軍士兵,在無數次實戰中鍛煉出了堅韌的意志。如今他已是個英勇的戰士,爲國家和人民的解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離別時的勉勵一次次在他的腦海中浮現。他想起了當年劉大嬸對他的叮咛,想起她那慈祥而憔悴的面容,便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回到富錦縣,看看這幾年她過得如何。
于是,呂志軍很快就動身前往了富錦縣。但是令人沒有料到的是,當他找到劉大嬸的生産小隊時,卻得知這位老人已經離世。他雖然早有這方面的心理准備,但當真正聽到這個噩耗時,他還是無比悲痛。
他立即循著村民的指引,找到了劉大嬸的墳墓。在呂志軍印象中,當年那位老人已經九旬高齡,所以離世其實也不算太早。
但想到她那麽慈愛的性格、那麽辛苦的一生,呂志軍就禁不住熱淚盈眶,當初還說要爲大嬸養老送終。她的一生本該是幸福安康的,結果卻這般離世了。
呂志軍立即按照當地風俗,准備了祭奠老人的一切物品。他買了一些老人喜歡的熟食,打掃了墳墓周圍的環境,又准備了三牲酒等祭品。他還特地找來了一個引路人,請其先行誦經超度。
待一切准備就緒後,呂志軍便焚香跪拜,口中嗫嚅著祝福老人在天之靈的诰言。他祈禱老人在天之靈保佑自己、保佑祖國太平,永世不會忘記她的恩德。"大嬸,您就永遠平安吧!有多遠我都願意來看您,只是不曾想您會先離開了。不過您也放心吧,我定不會令您的教誨生白,一定靠自己的雙手,好好建設國家,還您當年的一片心意!"
呂志軍良久良久地跪拜不起,淚水不住地滾落在早已凝固的墳土上。等他終于止住了哭泣,天色已經黑了下來。他又在墳前點起了一支蠟燭,在月光的映照下,呂志軍的臉上洋溢著孩子般單純的憂傷。

劉大嬸離世後,幾年間呂志軍一直在軍營裏默默服役。每每想起老人家的教導,他就覺得自己應該更加勇猛地戰鬥,讓自己成爲一名光榮的戰士。時間繼續流逝,他慢慢也就從一名年輕的新兵成長爲一名老資格的班長。
退伍前夕,呂志軍打算再次回到富錦縣看看。他買了一個嶄新的陶瓷骨灰盒,希望能將老人的骨灰重新安葬。
可是當他來到老人的墳墓時,卻發現早已有人將骨灰移走了。他四處打聽,才得知老人的一位親戚已經將她的骨灰重新安葬在了鄉下一處小山上。
呂志軍只好作罷,暫時將陶瓷骨灰盒收了起來。他又在墳前祭奠了一次,更新了祭品,訴說了這幾年來他在軍營裏的種種經曆與心路曆程。即便無法得到老人的骨灰,他心中的那份孝心也永遠不會消減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