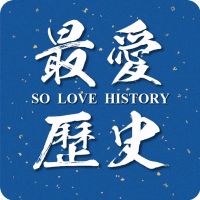多年以後,當司馬遷放下撰寫《史記》之筆時,他大概仍會想起那個令他蒙羞的時刻。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九月,他被以“誣上”的罪名逮捕入獄。“誣上”等同于後世的欺君之罪,在漢朝應判腰斬。但此時,他所收集整理的《太史公書》(即《史記》),僅僅撰寫了一小部分,還未達到流芳百世的巨著規模。
《太史公書》是其父司馬談臨終前叮囑他一定要完成的史書。對司馬遷來說,撰寫此書不僅是對曆史的負責,更有延續父親遺願的意義。眼下,面對生死關頭,他只能從絕望中尋找希望。
所幸,漢朝對于死刑的執行界定並非一成不變。根據當時規定,有兩種情況可以免死:一種是交錢贖罪,即“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而另一種則是承受“腐刑”,通過去勢失去做男人的資格。
司馬遷彼時爲太史令。漢朝官制規定,太史令爲秩級六百石官員,每月祿米僅有70石。在漢朝,豐年時米價一般在30—50錢(五铢錢)/石。也就是說,司馬遷不吃不喝,一年收入最多爲42000錢,要一下子拿出50萬錢罰金去贖命,難過登天。
所以,被捕入獄後,司馬遷沒得選,只有承受“腐刑”才能活下去。
01天漢元年(前100),奉命出使匈奴的蘇武被扣押,漢武帝大怒,決定再征匈奴。
此時,曾令匈奴人聞風喪膽的衛青、霍去病等名將均已謝世,大漢有兵無將。漢武帝只能沿用過去的思路,起用寵妾李夫人之兄、曾破大宛獲良馬的貳師將軍李廣利爲帥,以三萬步騎協同作戰的模式,進攻匈奴。
考慮到李廣之孫李陵曾任建章監和貼身侍衛,又有多年在敦煌、張掖屯兵練武的經驗,且曾深入匈奴腹地勘察地形,漢武帝認爲他更適合擔任李廣利大軍的後方運糧官。所以,待朝廷點完將後,漢武帝又將李陵召回朝,要他爲大軍籌備出征糧饷。
但是,李陵在入朝拜見漢武帝時,卻明確表示自己不願意給李廣利當後勤部長。
李陵的理由很直接,他是“飛將軍”李廣的孫子,祖上三代都是沖在最前線替漢朝打仗的先鋒,如今,僅讓他做個後方糧官,有辱李廣子孫的家族使命。當然,或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李廣利打仗向來平庸,難有勝仗,李陵若充當其運糧官,難出戰績,不利于振興當時已趨沒落的李廣家族。

李廣畫像
于是,李陵請求漢武帝另賜一隊兵馬給他。他願意率著這支“別動隊”,繞到匈奴人的後方,發起致命一擊,以配合李廣利在前方的攻勢。
沒想到,漢武帝拒絕了他的請求。
李陵並未死心,他繼續表示,自己願意率領麾下那支在酒泉、張掖等地備戰練武的5000人部隊先行,爲李廣利大軍占據先機。李陵手裏的這支部隊是清一色的“丹陽兵”,以步戰善射聞名。漢武帝本來擔心“以步禦騎”容易招致敗仗,可李陵卻信誓旦旦地表態,自己有完勝的把握,希望漢武帝盡快授其兵權,直搗單于庭。
這下,漢武帝大喜,遂令李陵率軍先行出征,再命強弩都尉路博德領兵做李陵的後備。這個決定卻遭到路博德的強烈反對。
路博德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他認爲自己從前曾爲伏波將軍,滅過南越國,打仗是一把好手,老將怎麽可能充當他人的配角?但他對漢武帝說出的理由是,李陵選擇在九月秋收之際發兵,犯了兵家大忌,他不願看到漢軍將士爲此而送命。無奈,漢武帝只能取消了路博德接應李陵的計劃。
不幸的是,李陵此次出塞,竟遭匈奴主力包圍。他揮師搏擊、殺敵數千,卻仍難逃被包圍的命運。在匈奴左、右賢王主力八萬騎兵的圍攻下,李陵“矢盡道窮”,只能將解困的希望寄托在李廣利身上。
然而,就在李陵大軍遭遇圍困之際,他的手下管敢卻率先投靠了匈奴人。管敢是李陵軍中的斥堠(偵察兵),十分熟悉李陵軍隊的兵力部署。管敢向匈奴人泄露了李陵的底牌,導致李陵未能等到援軍便已全軍覆沒。戰後,李陵害怕被漢武帝問責,遂投降了匈奴。
消息傳來,漢武帝大發雷霆。而朝中大臣也多是見風使舵之輩,陛下盛怒,他們也有多狠罵多狠,唯獨列席朝會的司馬遷,一言不發。
司馬遷的反常,引起了漢武帝的注意,便點名詢問其看法。
司馬遷說,自己與李陵年紀相仿,又同朝爲官,雖然平日裏工作沒什麽交集,但“仆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仆以爲有國士之風”。
針對李陵投降一事,司馬遷堅持認爲,李陵雖戰敗,但他的所作所爲已公諸天下。他是個十分看重家族聲譽及愛惜名節之人,他活著投降匈奴,應該只是暫時性的權宜之策,以待將來在適當的時候報答陛下的知遇之恩。
司馬遷絕對不會想到,正是自己這段爲李陵辯白的發言,徹底激怒了漢武帝。

漢武帝劉徹。圖源:影視劇照
漢武帝誤認爲,司馬遷對一個敗軍降將的“洗白”,旨在指責李廣利、路博德等後方大軍救援遲鈍,由此引申,則是漢武帝用人失當,才導致本該取得的勝利變成了失敗的惡果。
一念及此,漢武帝也不給司馬遷解釋的機會,便給他定了個“誣罔主上”的罪名,下獄論死。
02問題來了,司馬遷替李陵辯白是否站得住腳呢?也就是說,李陵的投降行爲到底是真是假?
學界的主流觀點是,李陵先假投降,後迫于形勢而真投降。但反過來想,李陵一開始或許就是真投降,只不過他的表現並不像其他投降者那樣卑躬屈膝,反而是帶著一種悲壯和無奈,恰恰是這種“悲情英雄”的鋪墊造成了司馬遷的誤判。
據《漢書·李廣蘇建傳》記載,李陵從遭遇匈奴大軍圍困到完全戰敗投降,中間曾有過一段糾葛掙紮的過程。那時,面對匈奴大軍的合圍,李陵率軍邊打邊撤,最後被匈奴兵斷了後路,堵入一處峽谷之中。匈奴單于並不打算放過李陵,遂在峽谷兩側的峭壁上埋下伏兵,等李陵率軍進入其提前布下的“口袋陣”後,再“乘隅下壘石”。經此一戰,李陵的5000步卒死傷慘重。即便如此,李陵自始至終都堅持力戰。直到雙方戰至黃昏時刻,看到身邊的兄弟一個個倒下,李陵這才身著便裝只身出營,並制止手下跟隨:“便衣獨步山營,止左右:‘毋隨我。’”

李陵畫像
按照北宋史學家司馬光的解讀,李陵此時單獨出營並非爲了乞求投降,而是想憑借個人之力刺殺單于,以期改變戰局。然而,這種行爲不僅與李陵作爲軍隊統帥的身份背道而馳,還可能進一步加劇雙方矛盾。後面李陵去刺殺單于的結果,大家也都知道——“良久,(李)陵還,歎息曰:‘兵敗,死矣!’……于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 。”
此時,擺在李陵面前的兩條路,一條是在軍中自戕,另一條是回去接受漢武帝對戰敗者的處罰——斬刑。而斬刑這條路,他的祖父李廣當年率軍出征匈奴時,就已經替他嘗試過了。史載,李廣當年率軍自雁門關出擊匈奴,因遇匈奴單于主力圍困,爲匈奴兵生擒。後來李廣詐死,偶然劫得匈奴良馬,逃回漢朝。漢武帝見後,立即讓廷尉府逮捕李廣審訊問罪。廷尉府官員認爲,“(李)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最終,李廣靠同事、親朋及自己的家資,才得以交錢贖罪,貶爲庶人。
如今,曆史的陰影再次籠罩在李陵的頭上。他應當十分明白,失兵回漢朝,或許仍有機會苟活于世,但重振李氏家族的希望從此熄滅了。
于是,據《漢書》記載,李陵刺殺單于失敗後,曾有一名軍吏勸解過他:“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于將軍乎?”軍吏所說的“浞野侯”,正是曾流亡匈奴十年的漢將趙破奴。趙破奴與李陵類似,也曾率萬騎部隊深入匈奴腹地展開“斬首行動”,但出師不利,爲匈奴左賢王所俘。直到李陵率軍出征前夕,趙破奴才攜家帶口回到漢朝。朝廷對他的處置也比對待李廣寬容,漢武帝沒有怪罪趙破奴,反倒以禮相待。
聽完軍吏的話,李陵立馬制止手下的勸降意圖:“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
毫無疑問,如果司馬遷知道此事,他必然會結合李陵之前的表現,進一步鞏固其心中李陵擁有“國士之風”的看法。
可曆史的事實卻總是讓人失望。在隨後的突圍過程中,當李陵看到副將韓延年突圍失敗選擇自殺殉國時,他卻又宣稱“無面目報陛下”,出人意料地選擇了投降匈奴。前後反差,匪夷所思。
據史書記載,李陵到了匈奴後,備受單于禮遇。當時,他的同僚好友、出使未果的蘇武正被單于扣押在北海(今貝加爾湖)一帶牧羊以消磨意志。李陵得知此事後,一直“不敢(訪)求(蘇)武”,甚至被單于督促著前往北海勸降時,他也表現得異常擰巴。
見到蘇武後,李陵當即自剖心迹道:“(李)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系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李)陵?”——你蘇武不願意投降的心情和毅力,怎麽可能超過我呢?又說,當今皇上年歲已高,朝令夕改,大臣無緣無故被誅滅者達十多家。在漢朝,自身安危都無法保證,還談何忠君保節呢?見勸說蘇武無用,李陵又說:“嗟乎,義士!(李)陵與衛律(此前威脅蘇武投降匈奴的胡人)之罪上通于天。”並做勢要與蘇武訣別。

蘇武畫像
如果不深入剖析李陵投降的影響,僅從他的行爲和言辭入手觀察,讀史之人更多看到的只是他的忏悔與自責。司馬遷與李陵同朝爲官多年,即使沒有任何交集,僅憑軍報上的寥寥數語,也很難不受同情心的影響,對李陵在前線的慘狀和投降後的痛苦産生深深的同情。
因此,司馬遷共情了李陵的遭遇。
而漢武帝卻始終將信將疑。李陵投降後,天漢四年(前97),漢武帝又以公孫敖爲因杅將軍,讓其率步騎4萬配合李廣利出征匈奴。這一次,公孫敖的運氣沒比李陵好多少。他帶出去的4萬部隊,多數折損于匈奴主力之手。撤兵回朝後,公孫敖遭到了漢武帝的問責。爲了減輕自己的罪名,他只能將這一切的過錯歸咎于李陵,胡謅一語:“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
公孫敖的話並無依據,且最後被證實替匈奴人練兵的,是另一名漢朝降將李緒,而非李陵。但那一刻,漢武帝顯然已經完全泯滅了他對李陵的最後一絲信任。他將李陵留在漢朝的族人盡數殺光,替李陵求情的司馬遷也受此牽連,獲罪下獄,徘徊在生死邊緣。
03李陵投降匈奴,司馬遷仗義執言受腐刑,這些都是載入史冊的事件,然而,隨著兩人的故去,不同的聲音出現了。
東漢學者衛宏在《漢書舊儀注》中說:“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司馬)遷蠶室。”照此說法,在司馬遷受腐刑一案中,李陵投降匈奴只是誘因,更深層的原因是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過分指責和揭露景帝、武帝父子在位時的過錯。不巧的是,該篇後來被漢武帝禦覽,憤怒的漢武帝當即令人刪去。李陵投降匈奴後,司馬遷替其求情,漢武帝便借故發火,將司馬遷處了腐刑。
往前追溯,衛宏的觀點實際上源于西漢末年的宗室劉歆。

《山海經》,劉歆曾爲之作注解。圖源:網絡
劉歆是西漢學者劉向之子、楚元王劉交的五世孫。他在《西京雜記》中稱:“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複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複用其子孫。”
可見,太史公一職是在漢武帝時確立的,此前錄史之人皆是家傳。如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便是漢朝獨一無二的太史公。在漢朝,太史公一職雖位在丞相之下,但國家發生的一切大事,底下的人呈報中央,都得先拿一份給太史公備案,而後再交予丞相處置。所以,太史公拿到的,都是朝廷的一手資料。而錄史者,又向來要求使用春秋筆法,司馬氏錄史直言不諱,盡說景帝、武帝父子的龌龊事,漢武帝豈能容忍而不拿他開刀?
劉歆認爲,“李陵之禍”爲漢武帝提供了處置司馬遷的借口,同時也激起了司馬遷日後的怨恨。這種怨恨,在他受刑之後再次爆發出來,從而導致其再下獄,最終身死獄中的結局。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在位期間,將太史公這個官職改爲太史令,只是履行太史公此前負責的文書工作而已,而且不再任用司馬氏子弟爲史官。
那麽,劉歆、衛宏等人關于司馬遷受腐刑一案的說法,是否可信呢?
翻開《史記·孝景本紀》,在文章的末尾,司馬遷發表議論說:“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複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這段話的意思是,漢文帝在位期間原本已天下太平,但是到了漢景帝時代,他卻錯用晁錯激化矛盾,釀成“七國之亂”。要不是後來漢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謀略,允許諸侯王將自己的土地分封給子孫,諸侯王之禍估計很難平息。這難道不是朝廷在安危之際施用謀略的最好例證嗎?
這麽看來,在司馬遷眼中,後世公認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漢文帝的功勞,而漢景帝的能力甚至都不如自己的兒子漢武帝。但話說回來,劉歆、衛宏等人主張的是司馬遷貶低孝景、孝武這一對帝王父子,從現存史料分析,這種結論似難成立。不知目前流行的《孝景本紀》是否遭到刪改,跟司馬遷最初的版本已有不同?
總之,自東漢起,劉歆、衛宏的觀點愈發流行。
讀罷班固的《漢書》,漢明帝劉莊得出一個觀點:“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他認爲,司馬遷針砭時弊過于激烈,雖然可以留名于後世,但或多或少都貶損了當世的君王,實在沒有半分忠臣義士的影子。
王肅是漢魏之際的經學家,司徒王朗之子,師從大儒宋忠。他認爲,班氏父子在編撰《漢書》時就曾說過,司馬遷寫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如此才有“實錄”之美名。既然錄史需要秉筆直書,漢武帝看完之後,“怒而削之”,也是人之常情。

王肅之父、司徒王朗。圖源:影視劇照
對此,《後漢書·班彪傳》載班彪之言稱:“太史令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班彪之子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也說:“而十篇缺,有錄無書。”按照司馬遷自己的說法,《太史公書》應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
班彪、班固父子治學嚴謹,且去司馬遷不過百年,想來所言非虛,當時流傳的《史記》已經缺失了十篇文字。但他們自始至終從未留下有關《史記》遺失的時間、篇目及原因。
對于《史記》遺失的詳情,《漢書》注家之一、三國時期學者張晏認爲:“(司馬)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這一意見,成爲現代學界關于《史記》遺失篇目的公認觀點。
但由于司馬遷生卒年仍有爭議,《史記》失書與漢武帝是否有關,時至今日仍衆說紛纭。
04學界還有一種觀點認爲,司馬遷受腐刑無關任何人,也不是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言“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而是他想要以此抗爭漢武帝晚年殘暴的統治。
古代文學研究大家徐朔方認爲,依照王國維對司馬遷的生卒年考證,司馬遷遭逢“李陵之禍”時,年已47歲。司馬遷膝下至少有一個女兒,其女後來嫁給了西漢丞相、安平侯楊敞。楊敞出身弘農楊氏,其祖上是赤泉侯楊喜。當年,項羽兵敗垓下,就是這位楊喜與其他五名漢軍將領在項羽自刎後分得其屍,揚名天下。

烏江自刎。圖源:影視劇照
楊敞的正室、司馬遷的女兒司馬氏是曆史上少見的“女強人”。昌邑王劉賀在漢昭帝駕崩後稱帝,在位27天,據說做了不下一千件的荒唐事,惹得朝堂怨聲載道,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開始密謀廢立。楊敞是霍光的親信,行動開始前,楊敞害怕得要死,回家便將廢立之事向妻子和盤托出,結果司馬氏告訴他:“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可見,司馬氏在大事面前有多果斷決絕。
而司馬遷受腐刑時,其女早已嫁作楊敞妻。司馬遷一年工資雖不足五萬,但遇到這種大事,女兒出于人之常情,又怎會對父親見死不救呢?徐朔方指出,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司馬遷覺得自己沒錯,拒絕花錢自贖;二是,司馬遷看不慣漢武帝的行爲,想通過此等賭氣的行徑,喚起漢武帝內心的自我審視。
漢武帝晚年是個什麽狀態呢?
據史料記載,晚年的漢武帝內心極其矛盾,一方面仍如年輕時那般豪邁雄闊,以追擊匈奴、征伐大宛爲己任,大力開拓漢帝國的疆土;另一方面也擔憂“亡秦之迹”的再現。因爲他早年立的太子劉據“仁恕溫謹”,一旦即位,必然是個仁孝守成之君。所以,相較于“老太子”劉據,他更喜愛與自己性情相似的幼子劉弗陵。
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作祟下,漢武帝不得不重新審視他與太子劉據之間的關系。自從太子就宮後,他爲劉據設立了博望苑,太子身邊就“使通賓客,從其所好”,甚至還有不少他的反對派給太子出謀劃策。顯然,父子二人在皇權的爭奪上愈演愈烈。

晚年的漢武帝。圖源:影視劇照
衆所周知,太子劉據是皇後衛子夫之子。其背後,衛、霍外戚集團勢力自然不容忽視。可是,在外戚身份以外,衛青、霍去病等更是以征伐匈奴而聞名的大漢軍事實權人物。對于一位以“皇權至上”爲信條的大一統君主而言,政治權力的轉移,對政治生命而言是致命的。換而言之,如果軍方配合太子劉據介入皇權爭奪,漢武帝的統治將面臨提前結束的風險。
很不湊巧,李陵身後的李氏一族也是大漢聲名赫赫的軍功世家。爲了消除身邊潛在的風險,漢武帝有理由故意不給李陵軍隊,讓其自募人馬出征匈奴,待其打不下去要撤兵時,再以道義及命令阻斷他的退路,使之最終走上被迫投降的終點。只是他沒想到,明明滿朝文武已盡說李陵的不是,司馬遷卻還要出來當“刺頭”,聲稱李陵有“國士之風”,逼迫他撤銷治罪李陵的決定。這樣,不治司馬遷之罪,也就說不過去了。
太始元年(前96),受盡腐刑與牢獄之苦的司馬遷終于出獄。考慮到自己還要繼續述說黃帝以來的曆史,他只能忍著身心的苦楚及天下人的冷眼,重新找漢武帝要官。不知是否仍心存惱怒,漢武帝給了他一個略帶羞辱但又俸祿優厚的官職——中書令。
在漢朝,中書令是秩級“千石”的官員。但在司馬遷之前,承秦所置,此官只用“宦者”。面對如此羞辱,司馬遷只埋頭苦撰《太史公書》的剩余篇目,直到太始四年(前93),其著基本完結。
這時,埋藏在司馬遷內心多年的憤懑,才終于找到一個宣泄口。
在封筆《史記》後,他寫了一篇《悲士不遇賦》: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複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韪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籲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炤炤洞達,胸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唯恥;朝聞夕死,孰雲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司馬遷在賦中一歎“士生之不辰”,二感不甘于“沒世無聞”,心態像極了曾以《離騷》寄托懷才不遇、命運多舛的前輩屈原。

司馬遷畫像
但在那個他認爲“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的年代裏,他從未輕言放棄,哪怕死亡在前,哪怕極盡屈辱,他依舊選擇了與手中的“史筆”共進退。也正是這種忍辱負重的精神,終使《史記》獲得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至高地位!
參考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4年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2007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2009年
內藤湖南著,夏應元譯:《中國史通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王子今:《秦漢史:帝國的成立》,中信出版社,2017年
施之勉 :《太史公行年考辨疑》,《東方雜志》,1944年第16期
徐朔方:《考據與研究──從年譜的編寫談起》,《文藝研究》,1999年第3期
韓兆琦:《司馬遷自請宮刑說》,《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
金璐璐:《漢武帝對司馬遷<史記>影響考論》,《文藝評論》,2012年第2期
楊有禮:《秦漢俸祿制度探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
劉淑穎:《漢代徙刑的嬗變與刑制改革》,《湖湘論壇》,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