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哲學?
書架上的一個“非熱門”類別、一種關于人和世界的論說……假如按這些年流行的學科“鄙視鏈”來看,它大概也是沒落的“衆學科之王”吧。
哲學開始于仰望星空。以西方哲學爲例,最早的哲學家往往也是天文學家,古希臘的泰勒斯、畢達哥拉斯、阿那克薩戈拉,都是如此。
阿那克薩戈拉(約公元前500-前428)出身貴族,但他主動放棄了繼承家業,把財産全部分給親戚,自己過著與世無爭的隱居生活,潛心研究自然。有人大惑不解地問他:“你活著爲了什麽?”他回答說:“爲了研究太陽、月亮和天空。”對方繼續追問:“難道你不關心你的祖國嗎?”他指著頭頂的天空說:“我非常關心我的祖國啊。”
以宇宙作爲自己的祖國,並不只有阿那克薩戈拉這一孤例。大名鼎鼎的犬儒派哲學家第歐根尼,敢于讓亞曆山大大帝不要擋住他的陽光。他靠著一根手杖和一個背包,四海爲家,還發明了“宇宙公民”(cosmopolite)這個詞。哲學家的思想疆域是超越國界的。兩千多年後,德國哲學家尼采同樣振聾發聩。他不僅宣告“上帝死了”,還聲稱:“哲學家不是時代的嫡子,而是時代的養子。”哲學家只是恰巧生活在某個時代,他的老家是永恒。
他們不斷追問世界本源和人生意義的終極問題,不斷拓寬人類的認知邊界。他們相信,“未經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過”。
學者、作家周國平,17歲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後來在中國社科院哲學系博士畢業,並留任哲學系研究員,終生從事哲學的寫作和翻譯工作,留下了衆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從懵懂無知的年紀開始接觸哲學,遍讀西方哲學史上的經典著作。許多人覺得哲學枯燥晦澀,毫無實用價值,他卻樂在其中,欲罷不能。他被那些智慧的頭腦所吸引,不由自主地進入他們思考的問題之中,跟隨他們在一個個奇妙的精神世界裏探險。

周國平 ,生于1945年,當代學者、作家,是中國研究哲學家尼采的主要學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守望的距離》《善良豐富高貴》《妞妞:一個父親的劄記》等。
如今,他已年近八旬,但仍思維敏捷,辯才無礙。他耗費四年時間,完成了人生中最重磅的著作,三卷本的《西方哲學史講義》,洋洋八十余萬言。從公元前6世紀一直寫到19世紀,對2500年的西方哲學史做了梳理,從古希臘的泰勒斯一直寫到近代的尼采,辨析了哲學與神話、宗教、科學、美學、政治的關系問題。這套書延續了他一貫生動簡潔的文風。在這套新書出版後,我們也專訪他聊了聊究竟什麽是哲學的魅力、哲學(史)與知識。在他看來,現代哲學背離了兩千多年的主流傳統,不論形而上學遇到怎樣的危機,哲學都需要思考世界本質和人生意義這樣的根本問題,所以,“我願意聽從維特根斯坦的勸告,對于不可說的,保持沉默”。

特約采寫|徐學勤
哲學家不是怪物

《西方哲學史講義》,周國平著,深圳出版社·果麥文化,2023年11月。
新京報:中國的本土學者,寫西方哲學史的並不多見。你爲什麽會在七旬之年,來寫一部篇幅巨大的《西方哲學史講義》?洋洋八十余萬字,這是體力與毅力的雙重挑戰。
周國平:之所以寫這部書,一個偶然原因是有媒體和出版界的朋友約稿,而根本原因是經過幾十年的閱讀積累,我想對西方哲學史做一次系統梳理。
我是一個愛讀書的人,文史哲都讀,但讀得最多的還是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從柏拉圖開始,西方哲學史上的經典著作,只要是被翻譯成中文的,我基本上都讀過,有的則是讀的外文原著。我做了大量的筆記和摘錄,所以,在西方哲學的知識倉庫裏,我已經積累了很多東西。如果就這樣把它們擱置,未免可惜,所以就想著寫成某種作品。
讀這些經典的時候,我的內心充滿歡喜。我感受到哲學家們的人格和思想魅力,我想把這些魅力傳遞出來,讓讀者也領略到,這是我創作這套書的初衷。
新京報:你在序言裏說,這是一個哲學愛好者寫給衆多哲學愛好者的書,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是否達到預期?
周國平:基本上達到了。我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不是要寫一部晦澀的學術專著,也不是一般的通俗讀物。我想把學術性和可讀性結合起來,既能讓普通讀者感興趣,也能讓專業讀者産生共鳴,讓不同層次的讀者各取所需。
新京報:介于專業與通俗之間的定位,讓你在內容選擇和行文風格上有何不同?
周國平:在內容選擇上,我把西方哲學分爲三大塊——本體論、認識論和人生論。本體論是探究宇宙的本質、世界的真相;認識論是對人類認識能力和界限的研究;而人生論則是研究人生的意義問題,包括對幸福、道德、信仰、生死等問題的探討。過去,無論是西方人寫的哲學史,還是中國人寫的西方哲學史,都把重點放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認爲那才是哲學的核心領域,對人生論則談論得很少,而我把三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包括曆來哲學史不怎麽展開的部分,比如古羅馬的斯多葛派,以及近代的蒙田、帕斯卡、愛默生等,我都作爲重點來講述。
在行文風格上,我不想寫得太學術化,故弄玄虛,而是盡量讓人能讀懂,讀得有趣。在每一章的開頭,我都寫了哲學家的生平故事,這是其他哲學史著作所沒有的。我會去讀每一位哲學家的傳記,然後,從中挑選出最精彩的部分來講述。就是要讓大家感受到,哲學家並不是什麽怪物,而是活生生的、可以親近的人。

紀錄片《受審視的生活:哲學就在街頭巷尾》(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2008)畫面。
新京報:傳統的西方哲學史,以本體論和認識論爲核心,而對人生論不太重視。爲什麽會有這種偏見?
周國平:實際上,在那些原創性的哲學家那裏,人生論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比如,蘇格拉底就是把哲學從天上引到地上來的人。在他之前的哲學家,從泰勒斯到阿那克薩戈拉,關心的都是宇宙問題,是一些自然哲學家和天文學家。而蘇格拉底關注人的靈魂,他使哲學立足于城邦,進入家庭,研究人生和道德問題。亞裏士多德也把倫理學作爲研究的重頭之一。到古羅馬時代就更不用說了,完全就是由人生論占主導。
近代哲學是以認識論爲中心,尤其以英國哲學家貢獻最大。他們追問人的認識能力和界限問題,英國的幾位經驗論哲學家都是很深刻的,到休谟走到頂峰,後來又轉向懷疑論。但即使是這些以研究認識論爲主的哲學家,他們對人生論同樣很重視。像洛克的《人類理解論》、休谟的《人性論》,都對人的心理、情感和道德進行分析,而且占了很大的篇幅。羅素在人生論方面也很強大,他寫了大量文章,談論宗教、道德和幸福問題。
我不知道爲什麽後來人們在寫哲學史的時候,會對人生論不夠重視,似乎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則,好像哲學的核心就應該是本體論和認識論。我猜,這可能跟人生論沒那麽理論化有關,一般觀點認爲,哲學應該是很理論化的。但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一方面,原創性的哲學家都很重視人生論;另一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哲學家,他們對本體論和認識論不太關心,但是對人生論很有貢獻,哲學史應該給予他們公正的地位。
新京報:曾主持編纂過《儒藏》的著名學者湯一介先生曾說,自己是哲學史家,而不是哲學家,要創造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才能稱哲學家。在你看來,什麽樣的人可以稱爲哲學家?
周國平:實際上,在英文裏,“philosopher”這個詞,既可以用來指那些具有原創性的哲學家,也可以用來指以哲學爲職業的人,也就是哲學工作者、哲學學者。但我認爲,還是可以加以區分:研究哲學史,或者研究某個哲學體系、哲學派別的人,可以稱爲哲學學者;而能夠進入哲學史,成爲被研究對象的,就是大寫的哲學家。
其中的關鍵指標,不是看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很多“草根哲學家”都喜歡構建體系,但根本沒人理會,最後也就是一個假體系。所謂的建立體系,不是構建一套邏輯框架、自成一說就行了,而是真的要把人類的根本性思考往前推進,那才是真正的哲學家。
新京報:這讓我想起李澤厚和余英時對錢锺書先生的評價,他們都敬佩錢锺書的博學,但認爲錢锺書的研究成果過于瑣碎,沒有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就像是一堆沒有串起來的散錢,總體價值並不大。但也有人認爲,要炮制一套讓人眼花缭亂的體系,對錢锺書來說並不難,而他之所以不這麽做,是因爲他覺得看似嚴密周全的思想系統,其實經不起時間的銷蝕。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理論系統剩下來的有價值的東西,其實也就是一些思想片段。
周國平:是這樣的,我覺得建體系這種癖好是很可疑的。尼采就是反對體系的,盡管他有自己的哲學體系,但他不是把建立體系作爲學術目標去追求。對學者而言,最理想的情況,不是建立一套貌似宏大的理論體系,而是要在所有作品中形成順暢的邏輯關系。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沒有體系,建立體系是從亞裏士多德開始的。亞裏士多德研究形而上學、政治學、倫理學等,他是把哲學往學術化方向發展的第一人。一般來說,要把一門學問學術化,的確需要有相應的理論架構。我對此並不反對,但前提是你的理論架構和思想的深刻性、豐富性要足以匹配。如果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不夠,那還不如原汁原味地把你的研究心得呈現出來。像錢锺書的《管錐編》、帕斯卡的《思想錄》,都沒有所謂體系,但是書中充滿了令人贊歎的洞見,這就比光有體系而沒有思想不知要好多少倍。

《管錐編》,錢锺書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0月。
新京報:對讀者來說,可以到這樣的書裏去淘金。
周國平:對。其實作爲讀者,我們在讀一位有完整體系的哲學家的作品時,也不是去接受他的體系,而是接受體系裏面的一些洞見。尼采說過類似的話,他說體系是會過時和褪色的,但在構建體系的過程中,那些體現你個性和創造性的東西,會永遠閃光。
哲學不存在知識積累
新京報:《西方哲學史講義》主要寫了從公元前6世紀到19世紀的25位哲學家,盡管三卷本已經很厚,但仍然有很多重要的哲學家沒有被納入進來,比如孟德斯鸠、伏爾泰、黑格爾等。這注定是一場艱難的挑選,你的取舍標准是什麽?
周國平:這跟我的熟悉程度和研究旨趣有關。孟德斯鸠的貢獻主要在政治哲學領域,除此之外,沒有太多可說的內容,而政治哲學不是我的主業,所以就舍棄了。亞裏士多德、洛克、盧梭等人,雖然也都有政治哲學,但他們在其他領域也都很有建樹,所以我寫了他們。
伏爾泰我覺得沒法寫。他是一個批判者和破壞者,他的批判很深刻、很過瘾,但他不像盧梭那樣自成一體,所以很難整理出來。我覺得,伏爾泰更大程度上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哲學家。
至于黑格爾,我是有意舍棄了,我比較同意叔本華的評價。叔本華認爲,康德已經把形而上學總結完了,而黑格爾又去搞另一套形而上學,搞一個絕對精神體系,這是一種開倒車的行爲。當然,黑格爾的思想很豐富,我看過他的不少東西,包括《小邏輯》《大邏輯》《精神現象學》等,我都下過功夫。他後來的研究方向發生了轉變,去研究邏輯和曆史的一致性,試圖用邏輯來解釋社會,我對這個方向不是特別感興趣。所以,我還是知難而退吧,我覺得很難把它整理出一個適當的篇章來。

根據德昆西寫于1850年代散文《康德晚年及其他散文》改編的電影《伊曼努爾·康德最後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mmanuel Kant,1996)劇照。
新京報:這本書從古代寫到近代,沒有進入現代和後現代。你在序言裏說,“古代和近代是笨拙的、單純的、完整的,和我很親近,現代則太機靈、太複雜、太細碎,和我甚疏遠。在現代,哲學已失去家園,四處流浪,在別人的疆土上尋找寄身之處。”爲什麽會有這種感受?
周國平:很多人都在說“哲學死了”“哲學的危機”“形而上學的危機”等,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存在這種危機。在康德以後,形而上學作爲科學已經不再可能,這是衆所公認的。後來哲學發生巨大的轉向,變得四分五裂,其中一個主要潮流就是語言哲學。
語言哲學在歐洲大陸和英美的發展路徑又不一樣。英美學者注重分析哲學,認爲形而上學這條路走錯了,而錯誤的根源就在于語言。因爲人們使用的語言不符合邏輯,所以,他們注重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甚至試圖創造出一套邏輯完美的語言。而歐洲大陸的學者剛好相反,他們認爲語言太講究邏輯了,邏輯就是語法,人們的思想受邏輯控制,因而走向了形而上學。比如,英文單詞being,也就是德文裏的sein,是“存在”的意思,它本來是一個系詞,結果變成了實體。這種情況有很多,所以他們認爲,語言要從邏輯的支配下解放出來,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回到詩的語言”,這就是語言哲學的兩條路線。
此外還有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其實找不到一條出路。現代哲學背離了兩千多年的主流傳統,我不知道現在的哲學在幹什麽,所以,我願意聽從維特根斯坦的勸告,對于不可說的,保持沉默。我認爲,不論形而上學遇到怎樣的危機,哲學都要思考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世界本質和人生意義的問題。世界到底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它的源頭是什麽?這些問題不是科學所能解決的,人生意義的問題更是如此。如果不去思考這兩個最大的問題,那麽哲學就走偏了。就像維特根斯坦所說,當我們談論哲學的時候,談論的並不是真正的哲學問題。
新京報:你以後還會續寫現代哲學嗎?
周國平:不會續寫了,我花不起這個功夫。古代和近代哲學家所思考的問題,和我是比較一致的,而現代哲學的很多東西,對我來說是陌生的。像胡塞爾的現象學,我花了很大功夫,也寫過相關的學術論文。他的主要著作《邏輯研究》當時還沒翻譯過來,我看的是德文版,真的看得好累,而且,我覺得他最後失敗了。
新京報:在西方哲學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師承案例,比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但你在書中提出,“知識可以積累,所以自然科學會不斷進步,而哲學不存在知識積累的問題,也談不上不斷進步。”能否解釋一下?
周國平:這裏有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哲學不是知識。我們可以說哲學史是知識,一代代哲學家的著作構成了一個知識領域,對這些思想進行研究是一種學術活動,但是,哲學本身不是知識。一個人不可能僅僅通過學習前人的觀點,就成爲哲學家,前人的思想可以作爲你的引入和參考,但是不能代替你去思考。哲學要去思考那些根本問題,而每一個思考根本問題的人,都要從頭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不存在知識積累的問題。
道家是有本體論的
新京報:你在書中考察了許多哲學家的生平經曆和思想曆程,你覺得在哲學家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質?
周國平:不同的哲學家,其實很不一樣,但我覺得有兩個特質不可或缺。一是敏銳的洞察力,或者說天生的直覺。我不是說對具體事情的直覺,而是對世界的根本結構、人性的根本特征,這些根本問題的直覺。那些大哲學家,在這些問題上都是很敏銳的。比如笛卡爾、洛克,他們在講述自己的成長經曆和思想曆程的時候,都提到喜歡思考根本性問題。他們上的都是很好的學校,對功課、對各種陳詞濫調,都感到非常厭煩。他們能敏銳地抓住大問題,並以此爲標尺,來判斷一個人到底有沒有見識。哲學家的另一個特質,就是對思考的執著,有追根究底的精神。當然,思想的條理性和邏輯性,也不可或缺。
在某種意義上,哲學是詩和數學的結合。詩是指它的敏感性,數學是指它的邏輯性,兩者缺一不可。在古希臘,哲學和數學是分不開的。在柏拉圖學園裏,主要的課程就是數學,學園門口寫著:“不懂幾何學者不得入內。”
新京報:這部書從古希臘開始講起,我們經常說“言必稱希臘”,爲什麽西方哲學會在古希臘興起?

由柏拉圖《會飲》改編的同名電影(Le Banquet,1989)劇照。
周國平:要解釋這個問題,其實不太容易。尼采在《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這本早期著作裏,談到過這個問題,就是爲什麽希臘會成爲一個哲學民族?在西方的民族裏,這是獨一無二的。
實際上,希臘文明要比埃及文明更晚,早期的希臘人都要到埃及去遊學。埃及在兩個方面很發達,一是宗教,像畢達哥拉斯就在埃及做過祭司;另一個是測量學,要建金字塔,測量必須要好。希臘的一些智慧頭腦,從埃及把這兩樣東西都學去了,但是,他們沒有停留在朦胧的宗教和實用的測量學上面,而是把它們都抽象化了。當時的人都相信,自然界由某種神秘的統攝力量主宰,埃及的宗教認爲,那是一些具象化的神靈,而希臘人則認爲,它是一些抽象實體。比如,柏拉圖所說的“理念”,就是這樣的抽象實體。與此同時,希臘人又把埃及實用的測量學,變成了抽象的數學,比如,畢達哥拉斯定理就是其中的代表。這就是希臘人的特點,他們不停留在現象層面,而是要尋找背後更深層的東西。
至于他們爲什麽會這樣,我也不知道。按照尼采的說法,是因爲希臘人特別善于學習,他們學習了別人的東西,然後,在別人停下的地方繼續往前走,這種能力非常了不得。此外,我覺得古希臘人有某種徹底性。他們在神話時代是徹底的神話民族,奧林匹斯神話成爲民族的信仰,統一了全民族的生活。但到哲學時代,他們又變成了一個徹底的哲學民族,對神話進行批判,繼而誕生了很多哲學家。
新京報:從神話時代到哲學時代的轉變,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次飛躍。你在書裏拿古希臘和古代中國進行對比,你說“希臘人是完美的兒童,卓越的少年”,“兒童”說的是神話時代,“少年”說的是哲學時代。你認爲,東西方哲學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周國平:王國維是最早談論這個問題的人,他的結論是中國沒有純粹哲學。他的“純粹哲學”概念,是通過閱讀德國哲學得來的,他對德國哲學下過很大功夫。所謂的純粹哲學,就是metaphysics(形而上學),探究有形的現象背後無形的本質。王國維認爲,這樣一種最爲本體的哲學,中國基本上是沒有的。當然,道家和宋明理學也有一些,但儒家是沒有的。所以,他說儒家是道德學和政治學,而不是哲學。
新京報:你同意這個觀點嗎?
周國平:我認爲,他說的基本上是對的。從哲學的三個部分來看,儒家沒有本體論和認識論,儒家所講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都是道德修煉方面的內容,而不是認識論。張岱年先生也曾說,儒家基本上就是人生哲學。

動畫片《老子說》(2004)畫面。
道家是有本體論的,而且,現在看來還是很高級的本體論。因爲西方哲學試圖用概念和理性去把握世界的這條路沒有走通,康德已經證明理性沒有這個能力,而中國的道家從來就沒有想用理性去把握世界。道是靠理性把握不了的,是不可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但是,從《道德經》裏的描述,我們可以略微感受到,道就是一個自然過程和它內涵的動力。它很難用概念表達,所以老子說,如果一定要表達,我就把它說成是道。另外,莊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相對主義也可以算作認識論。但儒家確實沒有認識論,而儒家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新京報:爲什麽東西方哲學會出現這種差異?它是偶然的嗎?
周國平:雅斯貝爾斯曾提出“軸心時代”的概念,但他似乎也沒講清楚根源在哪裏。爲什麽在那個時間段東西方同時誕生重要的思想家?又爲什麽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認識方向?原因很難說清楚。思想産生的原因,不能用思想本身來解釋。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地理因素,確定了這樣的解釋角度以後,一定能夠找出很多證據來自圓其說,但它是不是完全有道理,也很難說。

《論曆史的起源與目標》,[德]卡爾·雅斯貝爾斯著,李雪濤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
哲學始于驚疑
新京報:蘇格拉底說,“哲學始于驚疑。”亞裏士多德說,“驚疑是由自知無知引起的”,並且得出哲學思考不是爲了實用的結論。
周國平:是的。我很贊同亞裏士多德的觀點,哲學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求實用。注意,這不是它的缺點,而是它的優點。這種不求實用的精神,在西方興起的時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諷。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學家泰勒斯擡頭仰望星辰,結果不小心掉到井裏,遭到周圍的人嘲笑,說他光顧著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見腳下的路。但是,歐洲的精英階層,把這種不求實用的哲學精神傳承了下來,形成一個偉大的思想傳統。用愛因斯坦的話說,“因爲知識本身的價值而尊重知識,這是歐洲的偉大傳統。”他們認爲,理性是人最高貴的能力,我們去發展和應用這種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價值,我們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並不一定要得出某種實用的結果。
這種不求實用的精神傳統,是後來西方科學、哲學、文學、藝術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實用價值爲最終目的,那麽,你的思考一定是狹窄的,往往會漏掉最重要的東西。當你不求實用的時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質,最後反而能在實用領域結出豐碩的果實。科學技術的發展,離不開這種純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報:這其實也可以用來解釋“李約瑟難題”,就是爲什麽科學沒有在近代中國産生。
周國平:是的。李約瑟對他的問題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著重用近代社會政治的變化來解釋,這是不對的,其實根源在古希臘和先秦時期就已經種下了。
從根本上來說,求實用是爲了滿足人的生理需要,讓自己過得更舒適安逸,這是一種動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動物的地方就在于,人還是一種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價值至高無上。讓人的精神屬性得到更好的發展,才是人最應該做的。我們不能以低階屬性的滿足作爲標准,來衡量高階屬性的價值。
馬克思也有類似的觀點,他在《資本論》裏有一段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真正的自由王國,是在必須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開始的,它存在于物質生産領域的彼岸,那就是作爲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發展。”爲了滿足生存的物質需要而活動,那是必然王國,必然王國是不可回避的階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這個階段。
他理想中的共産主義社會,不只是物質極大豐富,物質不過是手段,目的是爲了讓人從物質生産裏解放出來。把自己能力的發展作爲目的來活動,那才是真正的共産主義社會。所以他說,喜歡釣魚的釣魚,喜歡打獵的打獵,喜歡藝術的搞藝術,喜歡科學的搞科學研究,應該是那樣一種狀態。這種思想,跟亞裏士多德等人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西方哲學的不求實用性和純粹性,也是歐洲科學精神的重要源頭。

拉斐爾《雅典學院》局部。
新京報:在柏拉圖的著作中,經常提到人們對哲學無用的嘲笑。哲學家關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們與世俗保持距離,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顯得笨拙和無知。我們該如何看待哲學與日常生活,以及哲學家與時代的關系?
周國平:柏拉圖說,哲學就是追求永恒。哲學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問題,這是一個坐標軸。無論思考時代的問題,還是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如果以永恒價值作爲坐標,那就是從哲學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沒有這個坐標,那就和哲學沒有關系。
尼采有一個精彩論斷,他說:“哲學家不是時代的嫡子,而是時代的養子。時代不是他的親生母親,而是他的養母。”一個有著最爲永恒的靈魂的人,很偶然地寄養在某個時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這樣的感覺,那你一定是哲學家。

《當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2007)劇照。
當然,哲學家也需要有現實關切,但是,他們和時評家的關切方式很不一樣。後者會糾纏在一些具體問題裏面,而哲學家會以永恒的精神價值作爲坐標,對時代的弊病進行批判。譬如說,正義就是一個永恒的坐標,對非正義的現象進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學家應盡的使命。但是,哲學家不要想著去做帝王師,那就沒意思了。
新京報:說到帝王師,讓我想起柏拉圖的“哲學王”概念。曆史上想成爲“哲學王”的統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學王”的,你認爲只有《沉思錄》的作者、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哲學王”的核心要義是什麽?爲什麽“哲學王”的理想難以實現?
周國平:柏拉圖提出“哲學王”的理念,是因爲他的老師蘇格拉底之死。從那場教訓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學必須與權力聯盟,才能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有所作爲,否則哲學將寸步難行,他由此産生了“哲學王”的理想。他認爲,最好是讓哲學家成爲統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話,就把統治者培養成哲學家。
讓哲學家成爲統治者很難做到,得靠運氣。古羅馬出現馬可·奧勒留這樣一位“哲學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規劃出來的。柏拉圖曾在敘拉古城邦,試圖把那裏的僭主培養成哲學家,但是失敗了,那位僭主不耐煩地對他說,原來哲學就是無聊的老人對無知青年的談話。從此,柏拉圖就放棄了培養“哲學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辦學院、當教授。
我認爲,“哲學王”的概念是一個空想,不可能實現。哲學要對一切權力進行審視,而且,權力本身具有腐蝕作用,它會讓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認爲,哲學所處的最好的時代,就是權力不去管它的時代。權力既不要扶持哲學,也不要打壓哲學,而是保持中立態度,任由哲學家們自己去爭吵,對他們的是非對錯不作評判。
哲學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報:你的這部書專門寫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聞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學家的行列,你爲何會對蒙田偏愛有加?他在哲學領域的主要貢獻有哪些?
周國平:其實,喜歡蒙田的哲學家有很多,尼采也極力推崇他。蒙田對歐洲思想的發展影響很大,不亞于那些以哲學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貢獻就是人生哲學。
歐洲經曆了漫長的中世紀,基督教的倫理道德一直占統治地位,人們的思想被壓抑了很久。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蒙田這樣一個人,他的哲學回歸真實的、樸素的人性,拒絕任何人爲的拔高和美化。從人生格調來說,貌似很低調,但其實是驚世駭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這一點,他對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讓你不必因爲道德壓力,而對自己的平凡感到慚愧。神學的枷鎖已經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鎖也去掉。這種哲學對普通人來說是很有親和力的,而他的內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報:盧梭是西方哲學史繞不開的人物,他身上充滿爭議,他對公衆宣揚大愛,卻把自己的五個孩子送進育嬰堂。像盧梭這樣在私德上有虧欠的哲學家不在少數,比如羅素、薩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羅·約翰遜在《知識分子》一書中所說,知識分子愛人類,卻不愛身邊具體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學家的道德宣揚和私德相矛盾的問題?
周國平:這種情況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學家身上,就會被放大。盧梭的選擇有其特殊原因,因爲他很貧困,而他的貧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絕任何政府津貼或富人贊助,主張過一種回歸自然的樸素生活,一輩子主要靠抄樂譜爲生。他在愛情上也遭遇坎坷,這麽懂感情的一個人,跟他相守終生的,卻是一個既沒文化、又沒教養的女仆。女仆帶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們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很難養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進育嬰堂。盡管情有可原,但盧梭還是負疚終生。他在《忏悔錄》裏說,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內疚。人不能求全,盧梭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他的倫理學把良心作爲最重要的東西,這也給了康德很大的啓發。
關于哲學家的言行不一,古羅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辯護。他是尼祿的宰相,位高權重,還很會斂財,過著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書簡”裏,他卻主張人應該過簡單清貧的生活。

《塞涅卡道德書簡》,[古羅馬] 塞涅卡著,劉晴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2月。
當時就有人罵他是僞君子,說一套,做一套。他承認自己不是聖人,說:“我主張簡樸的生活,可是我自己過著富麗堂皇的生活,我主張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們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訴你們,我是講人應該怎麽生活,不是在講我現在是怎麽生活的;我的立論反對所有的惡,尤其反對我自己的惡;我給自己樹立一個目標,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辯護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應該追求的目標,盡管自己沒有做到,但這個標准仍然成立。
新京報:“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這就是應然和實然的區別。
周國平:是的。道德如果沒有一個高于日常行爲的標准的話,那就不成其爲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脫離人性,應該是只要努力就能夠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很少有哲學家因爲思想而發瘋
新京報:這部書的最後一章留給了尼采,尼采是你用功最多的哲學家,你翻譯了他的多部著作,還寫過兩本尼采研究專著。爲什麽對尼采情有獨鍾?他最吸引你的是什麽?
周國平:我最開始喜歡的是他的文風,喜歡他思想的深刻、尖銳、跳動、出格。用他的話說,哲學家應該成爲一個舞者,他就是一個跳著舞的哲學家。我特別喜歡他的表達和思想的不尋常,他大量的著作都是用格言體寫的,裏面有很多精彩的洞見。後來,當我真的去研究尼采,我發現他對哲學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本體論和認識論,同樣有精深的思考。

《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再版),周國平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19年6月。
關于尼采,我寫過兩本書,一本是《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那本書重點談尼采的人生哲學;另一本是我的博士論文《尼采與形而上學》,重點談尼采在本體論和認識論方面的貢獻。他關于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思考,除了《偶像的黃昏》外,主要體現在他未發表的遺作裏。這些遺作,後來由他的妹妹和一個學生整理成《權力意志》。有人認爲《權力意志》是一本僞書,因爲它不是尼采自己整理的。但我不這樣看,我覺得它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裏面沒有一段話是編造的,都是從尼采的遺稿裏摘錄出來的,而且整理得非常系統完善,全部按照主題分門別類。從這本書可以看到,尼采後期在非常系統地思考,爲什麽歐洲的形而上學會走到絕路,陷入虛無主義。
形而上學相信存在一個永恒的東西,這個東西到基督教到達頂峰,就是信仰上帝。但在啓蒙運動以後,“上帝死了”,大家沒有信仰了,于是陷入虛無主義。爲什麽會走上這條路呢?尼采進行了剖析,他認爲,形而上學最基本的兩個要素,一是理性,二是道德。在分析理性的時候,他提出了很多認識論上的洞見,包括我非常贊賞的透視主義。所謂透視主義,就是說世界沒有所謂的“本來面貌”,你從什麽角度去觀察,它就是一個什麽樣子,現象世界是我們唯一可以把握的世界。不同角度所把握的現象世界背後,沒有一個所謂的本質世界。這個觀點是非常領先的,它被後來的現象學派繼承了。可見,尼采在認識論方面也非常厲害,我佩服他完全是有道理的。(笑)
新京報:那麽,他的“超人”概念該如何理解?
周國平:其實,在尼采哲學的傳播過程中,存在很多認知偏差,“超人”概念就是其中之一。人們很重視“超人”概念,但我不認爲這個概念在尼采哲學中有多麽重要的地位。“超人”概念的提出,是因爲他對人類的現狀感到絕望,所以,盼望誕生一個“超人”,克服人類現有的弱點。但是,他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裏說,“超人”不過是詩人編造的玩偶,是一個騙局而已。

改編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ake Zarathustra,2001)劇照。
新京報:你在書裏說,尼采是一個非常看重生命力度和精神高度的哲學家,他提出“在自己身上戰勝時代”,但最後他爲何會走向瘋癫?
周國平: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系。我並不認爲尼采是因爲思想而發瘋,他的精神病是有體質原因的。現在一般認爲,是因爲他早年得了梅毒,後來發作了,導致神經系統出現問題。其實,很少有哲學家因爲思想而發瘋,詩人倒是有可能,荷爾德林就是一個例子。當然,尼采的思想裏面有瘋狂的因素,有很不常規的東西。在《看哪這人》這本書裏,就已經有一些發瘋的征兆。但是,因果關系不要顛倒,不是因爲他有這些思想而發瘋,而是因爲他發瘋了,所以才産生某些瘋狂的思想。

愛德華·蒙克作品《弗裏德裏希·尼采》局部。
新京報:你曾經說,尼采是屬于青年人的,勸青年人都去讀一讀尼采,爲什麽?
周國平:我領會的尼采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人要有強大的生命本能。一棵植物能開花結果,是因爲它有強大的根系,而一個人要有蓬勃的精神狀態,是因爲他熱愛生活,他有讓人生變得更精彩的沖動。青年本來應該是生命力最旺盛、最有精神理想的階段,但是很遺憾,現在很多青年人不是這樣,所謂“躺平”“擺爛”“佛系”,成爲很多人的口頭禅。
這當然跟時代環境有關,時代環境對青年人不是那麽友好,但這不是未老先衰的理由。青年人應該有活力,在不同的時代環境下,他們的生命活力和精神追求表現方式可以不一樣,但是不能沒有。沒有哪個時代是絕對好的時代,我的青年時代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時代,但是我沒有放棄精神追求,沒有放棄對生活的熱愛。
人性中的天使與魔鬼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周國平:哲學家改變世界的方式,不是親自走上政治或經濟舞台,用權力和金錢改變世界,而是通過觀念改變世界。哈耶克說得非常好,他說,實際上觀念對人類的影響是最大的。哲學家用觀念去影響各個領域的社會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又用觀念去影響各個領域的政策和實踐,繼而影響到社會上每個具體的人,所以,千萬不要小看觀念的力量。
新京報: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說,人類的戰爭和暴力在逐步減少,但是這兩年來,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不斷升級。面對戰爭與殺戮,哲學和哲學家能否起到某種作用?
周國平:我覺得哲學在這方面是比較無力的,因爲權力掌握在政治家手裏,在很大程度上,世界格局是由政治家決定的。當然,如果我們更深入地挖掘,會看到政治家的素養跟民族傳統和文明程度有關,但確實是政治家在直接支配著世界,哲學家只能夠提出建議。
康德很早前就專門寫過一本書,叫《論永久和平》,他提出了很多構想,其中包括廢除常備軍、制定國際法、建立聯合國等。羅素也是和平運動的領袖,他把國家權力過大看作現代世界不幸的根源。他曾爲反對一戰而撰寫過政治理論著作,還參與了二戰後的反對核擴散運動,創立了非暴力反抗運動委員會。不過,羅素的行動之所以能起作用,和歐洲整體的文明程度有關。
現在也有很多思想家在討論這個問題,但是我總覺得,情況是令人悲觀的。長久的和平,讓人産生“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很強大”的錯覺。其實,人性中既有天使,也有魔鬼,有時候魔鬼會戰勝天使,這就很可怕。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無知的戰爭擁護者,他們完全不思考,在那裏唱各種高調。那就是人性中的魔鬼在說話,他們身上的天使已經奄奄一息了。所以,我對此是不太樂觀的。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特約采寫:徐學勤;編輯:西西;校對:劉軍。封面題圖素材爲《當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2007)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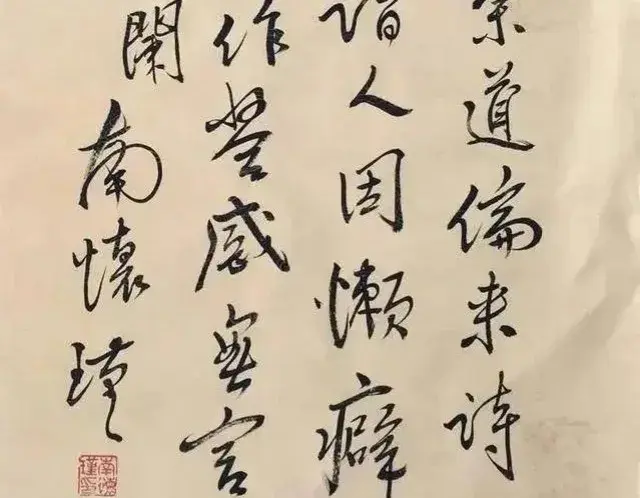

尼采死了,上帝還活著,耶稣複活了。
什麽學科都不能代替我們思考,只是可以借鑒的輔助
人不可自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爲有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爲有智慧的。--哥林多前書(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