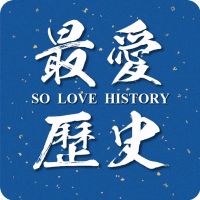建安年間,一棵橘樹枯死于銅雀台中。
橘樹並非河北之物産,是從南方不遠萬裏移植到邺城的“珍樹”。正所謂“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這株“異鄉來客”面對劇變的環境,無法適應,因而枯萎。但它的死牽動了一位詩人惆怅的心緒。
庭園之中,曹植凝視著枯木,專門寫了一篇《橘賦》,其中提到:“飏鳴條以流響,晞越鳥之來棲。”這棵橘樹經曆了“江洲之暖氣”到“玄朔之肅清”的變化,無法開花結果,卻依然希冀南方的越鳥前來棲息。
而越鳥,指的是孔雀。
事實上,孔雀已經來到了北方的園林。楊修便曾寫過《孔雀賦》:
“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池沼,與衆鳥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行者莫眡。臨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鹹如此,故興志而作賦,並見命及。遂作賦曰:有南夏之孔雀,同號稱于火精。寓鹑虛以挺體,含正陽之淑靈。首戴冠以飾貌,爰龜背而鸾頸。徐軒翥以俯仰,動止步而有程。”
根據這篇賦的序言,我們知道,孔雀同樣引起了臨淄侯曹植的感觸,他先寫了一篇賦,然後才讓楊修也寫一篇。可惜曹植的孔雀賦今已不存。
曹植和楊修感慨的是士人的命運如同庭園裏的孔雀,這些異鳥一開始因其“奇偉”而受到追捧,可時間一久,人們習以爲常,便不去瞧它。再美麗的事物,也敵不過人情冷暖。
溫暖和煦的南方,是一個奇妙未知的世界。那裏的珍異物種進入中原,雖然命運“淒慘”,卻在北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難以泯滅的痕迹。

曹植。圖源:影視劇照
01古時候,孔雀被視爲文禽。它有著華麗的外觀,羽毛晶瑩透亮,要麽深藍,要麽翡翠,還會呈現出絢麗的眼紋。
人們尤爲喜歡孔雀的尾屏,清代黃濬《紅山碎葉》說:“大開屏時燦爛且久,獨其冠有毛一叢,狀如小翎……聲亦清亮而宏達,真尤物也。”
孔雀永遠昂首挺胸,目視前方,舉止優雅。因此,古人認爲,孔雀有九德:“一顔貌端正;二聲音清徹;三行步翔序;四知時而行;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淫;九知反覆。”
作爲受人追捧的瑞鳥,孔雀在古代並不罕見。文煥然、何業恒發表的《中國曆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變遷》中指出:“目前中國孔雀的分布僅限于雲南省南部,但在曆史時期遠遠超出這個範圍。”
孔雀主要來自于南方之南。《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滇地)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三國志》也記載:“(交州)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
但遙遠的西域其實也産孔雀。《漢書·西域傳》有罽賓國出“孔爵”的記載,孔爵就是孔雀。《後漢書·西域傳》說:“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裏。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
直到清代,乾隆看見哈密進貢的孔雀,興致大發,寫了一首《孔雀開屏》,詩中雲:“西域職貢昭鹹賓,畜籠常見非奇珍。招之即來拍之舞,那慮翻翺蔥嶺尖。”乾隆賦詩距今也就兩百六十余年,那時新疆還有孔雀生存。

【清】郎世甯:《孔雀開屏圖》。圖源:網絡
《魏書·西域傳》說,龜茲國“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孳乳如雞鹜。其王家恒有千余只雲”。在龜茲國,既有在山谷間“群飛”的野生孔雀,還有如雞群一般養殖的家禽孔雀,最大的規模竟達到了一千多只。《藝文類聚》載,西晉司馬炎在位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馴指,應節起舞”。可見,西域各國精通飼養孔雀之道。
南方也一樣。《嶺南異物志》 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爲脯臘。”這說明南方人食用孔雀乃是常態。宋代學者周去非曾說過:“孔雀,世所常見者。中州人得一,則貯之金屋。南方乃臘而食之。物之賤于所産者如此。”
在西域和南方擺上餐桌的孔雀,一來到中原,便搖身一變成了金屋裏的瑞鳥。人們興致勃勃地觀察來自遠方的“異物”,主動將它們融入中國的精神世界。
孔雀在文人筆下,要麽傲然獨立、引吭高歌、輕舞開屏,如同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要麽因其美麗,象征著愛情與姻緣。
前者如唐朝詩人王建所作的《傷韋令孔雀詞》:“可憐孔雀初得時,美人爲爾別開池。池邊鳳凰作伴侶,羌聲鹦鹉無言語。雕籠玉架嫌不棲,夜夜思歸向南舞。如今憔悴人見惡,萬裏更求新孔雀。熱眠雨水饑拾蟲,翠尾盤泥金彩落。多時人養不解飛,海山風黑何處歸。”孔雀被人養在園林之中,雖錦衣玉食,卻仍想著回歸南方,如今身形憔悴,被人嫌棄,主人又買了一只新孔雀。而那只老孔雀,華麗已經褪去,不知能否回到家鄉。
後者如樂府詩《孔雀東南飛》,首句“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便足以讓人沉浸到一段愛情悲劇之中。
其實,孔雀性格凶猛,盜食農作物,並非人畜無害。但在異域光環的加持下,人們沒辦法不愛上這樣一只美麗的生靈。
02孔雀千裏迢迢來到中土,如果將其看作是旅客,它們走過的路很長,見過的世面卻很少。它們的命運早已注定:三兩成行,守衛森嚴,路途漫長單調,來到一處皇家園林,被最有權勢的人賞玩,直至死去。
漢文帝初,陸賈出使南越,南越王“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漢武帝時,帝國經略西南夷,南來北往的道路愈發通暢,孔雀與象牙、犀角、鹦鹉等紛紛來到中原。
三國時期,孔雀已經成爲南方進獻的常見物産。《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載:“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鬥鴨、長鳴雞。”三國吳孫晧時,孫谞任交趾太守,“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

【宋】崔白:《枇杷孔雀圖》。圖源:網絡
帝國的擴張,不僅在于版圖的擴大,更在于精神世界的膨脹。新征服地區的蠻夷土人,很難作爲編戶齊民直接提供賦稅,卻可以滿足皇室“充備寶玩”的獵奇需求。人與孔雀的相遇,就像“文明”的眼睛看見了“野蠻”之地。
與孔雀跋山涉水進入王都相反,還有一群人親身來到“野蠻”之地,剝離想象,觀察異域。他們最偉大的創造就是形形色色的“異物志”。
東漢有一個學者名叫楊孚,嶺南人,著有《異物志》。原書已佚,有部分內容爲後人引用得以保留。楊孚眼中的孔雀是寫實的:“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形體既大,細頸,隆背,自背及尾背有珠文,五采光耀,長短相次,羽毛皆作員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文長二三尺,頭帶三毛,長寸許,以爲冠。足有距,棲遊岡陵,迎晨則鳴相和。”這說明,人們很早就對孔雀有了充分的認知。
唐人房千裏的《南方異物志》的記錄最爲詳細:“孔雀,交趾、雷、羅諸州甚多。生高山喬木之上。大如雁;高三、四尺,不減于鶴。細頸隆背,頭裁三毛,長寸許。數十群飛,棲遊岡陵,晨則鳴聲相和,其聲曰‘都護’。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長二三尺。夏則脫毛,至春複生。自背至尾,有圓文,五色金翠,相繞如錢。自愛其尾,山棲必先擇置尾之地。雨則尾重不能高飛,南人因往捕之。或暗伺其過,生斷其尾,以爲方物。若回顧,則金翠頓減矣。山人養其雛爲媒。或探其卵,雞伏出之,飼以豬腸、生菜之屬。聞人拍手歌舞則舞。其性妒,見采服者必啄之。”這段文字詳細介紹了孔雀的分布、形貌、習性、聲音、性別、捕捉方法等,堪比百科全書式的介紹。
古人對于孔雀的認知也有荒誕之處。比如,唐人段公路引張華《博物志》雲:“孔雀不匹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也就是說,孔雀不交合,相互唱歌就能懷孕。
還有人認爲,孔雀與蛇交配。唐筆記小說《紀聞》就記載了這麽一個故事,詩人王軒養了一只孔雀,一日,奴仆告訴他:“蛇盤孔雀,且毒死矣。”王軒急忙派手下去救,手下不去,王軒發怒,那名手下則回答:“蛇與孔雀偶。”這種誤解大概來自于孔雀叼住蛇玩弄,未及時吃下的場景,人們以訛傳訛,便成了共識。
但總體而言,人們已不再僅憑刻板印象去想象南方,而以經驗的方式體會南方,這是中原王朝將邊疆逐漸納入自己統治的一個生動縮影。

【清】蔣廷錫:《孔雀圖》。圖源:網絡
03唐朝以後,邦國進獻的孔雀日漸減少,州郡土貢的孔雀越來越多,這足以說明,帝國的疆域已經擴張到何種程度。盡管人們對孔雀的認識越來越翔實,但在宮廷之中,它的角色定位始終沒變過——帝國動物園裏的一顆明珠。
帝國越強大,它的動物園就越大,裏面的動物就越豐富。在古代,無數憂國憂民之士抱怨過皇家園林的規模,抗議皇帝的鋪張浪費,然而大都無濟于事。
明朝弘治年間,光祿寺官員胡恭上奏道:“本寺供應瑣屑,費出無經。乾明門貓十一只,日支豬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猬五個,日支豬肉十兩……虎三只,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只,日支羊肉六斤;虎豹一只,日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只,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鴿子房,日支綠豆粟谷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計之,共用豬肉、羊肉並皮骨三萬五千九百余斤,肝三百六十副,綠豆粟谷等項四千四百八十余石。”
這是一筆相當沉重的負擔,但對很多皇帝來說,這筆錢必須得花。
皇家園林裏的生靈不僅僅是動物。它們是祥瑞,象征著天下太平;它們是貢品,代表著萬國臣服。《宋書·符瑞志》載,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交州刺史垣闳獻白孔雀”。孔雀如同一個使節,主動從遠方而來,要爲王朝增光添彩。
哪怕“異物志”已經剝去孔雀身上神秘的色彩,只要到了進貢的環節,孔雀還得重新再穿上祥瑞的衣服。愈是天上難找、地上難覓,進獻之物便愈是受到重視,愈可能出現在朝堂之上,進獻者的功勞就愈大,帝王懷柔遠人的名聲自然就愈響亮。
對于朝貢的邦國來說,進獻異獸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因爲中原王朝一般會進行回賜,饋贈之物相當可觀。而且,來華的使節往往都帶著一個商隊,進入王都的市場,進行交易。正如《文獻通考》所言,“島夷朝貢,不過利于互市賜予,豈直慕義而來”。
在這樣的天下體系中,還有許多“異獸”的中間商。
公元6至8世紀,中國南方的孔雀通過新羅,源源不斷渡海去往日本。在日本人眼中,這樣的行爲自然是“獻”與“貢”。當然,新羅有自己的小算盤。龍朔三年(663),唐軍在白江口之戰中大敗日本,作爲聯盟的新羅雖然取得了勝利,卻也感受到唐朝在東北亞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僅數年後,鹹亨元年(670),唐朝新羅戰爭爆發,戰爭持續七年,新羅最終請罪稱臣。由此不難看出,新羅向日本贈送孔雀,便是希望化敵爲友,強化力量以對抗唐朝。
至于日本,一直渴望提高自己在東北亞的影響力,打造一個小型的“天下秩序”。孔雀被帶入日本之後,重複著它們在中國宮廷的命運:作爲“珍稀異獸”進行展覽,供百姓與貴族觀看,宣示日本朝廷的神聖性。

【清】鄒一桂:《孔雀牡丹圖》。圖源:網絡
04兩宋以來,曾爲蠻荒之地的南方褪去了神秘的外衣,孔雀不再神異、稀奇。
“異物志”的傳統保留了下來。宋人範成大寫的《桂海虞衡志·志禽》中記載有以孔雀爲原料的菜肴,“孔雀……飼以豬腸及生菜,惟不食菘……又以孔雀爲臘,皆以其易得故也”。元代賈銘撰寫的養生著作《飲食須知》載:“孔雀肉,味鹹性涼,微毒。食其肉者,自後服藥必不效,爲其解毒也。”明代張岱的《夜航船》曰:“孔雀膽大,毒殺人。”
孔雀的羽毛十分絢麗,受到人們喜愛,用處也最多。嶺南、交趾一帶的百姓常常采集孔雀的金翠尾羽制成孔雀扇。《舊唐書·職官志》載:“凡大朝會,則傘二翰一,陳之于廷。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舊翟尾扇,開元年初改爲繡孔雀。”翟尾指的是野山雞的尾羽,爲了保證朝儀威嚴,開元盛世之下改成了孔雀羽。孔雀羽才是上上之選。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俏平兒情掩蝦須镯,勇晴雯病補雀金裘”中,賈母介紹了一件金翠輝煌、碧彩閃灼的氅衣:“這叫作‘雀金呢’,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後來,寶玉不慎讓氅衣被炭火燒了指頂大的一個洞。晴雯提出,氅衣是孔雀金線所織,也拿孔雀金線用“界線法”織補,或許可以過關。這時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裏除了你,還有誰會界線?”可見,社會上層對孔雀羽的喜愛。
清代官服以孔雀翎爲冠飾,又稱爲“花翎”。孔雀尾羽帶有“目暈”,其實就是孔雀尾毛上的彩色圓斑,以多者爲貴。一開始,清人不欲喪失民族個性,規定親王、貝勒不得戴花翎,因爲這是“臣僚之制”,宗室貴族豈能自降身份。後來,戴花翎變成了一種特殊的獎賞,宗室貴族也以戴花翎爲榮。清後期,花翎更是成了清帝籠絡臣子的工具,比如李鴻章戴三眼花翎,曾國藩、左宗棠戴二眼花翎。

【清】沈铨:《玉蘭孔雀牡丹圖》。圖源:網絡
曆史的河流不斷向前,翻天覆地的變遷已在不經意間發生。兩宋以後,“文明”不再只是觀察南方。越來越多的人湧進“瘴疠橫行”的南方地區,將隨處可見的草地、灌叢、竹薮改造爲耕地,將山林裏的喬木變成燃燒的柴火,將溪水流經之地變爲人類的聚落。文明到來,野蠻讓位。
孔雀本身就是一個嬌貴的物種,“生溪洞高山喬木之上……臥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適,蓋巢于山林而下浴沙土”,而它們宜居的地方又不斷被人類侵蝕。特別是到明清時期,人口膨脹,“野蠻”的領地越來越小,再加上華美的孔雀翎引來人類的大肆捕殺,孔雀的退卻早已不可避免。
南方逐漸不見孔雀的蹤影,而進貢的孔雀只能來自遙遠的東南亞了。
參考文獻:
李蘭芳:《孔雀考》,《形象史學》,2021年第4期
王子今:《龜茲孔雀考》,《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梁山:《孔雀與六到十二世紀的東亞外交世界》,《古代文明》,2017年第3期
林曉光:《六朝宮廷貢物與貴族文學——從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