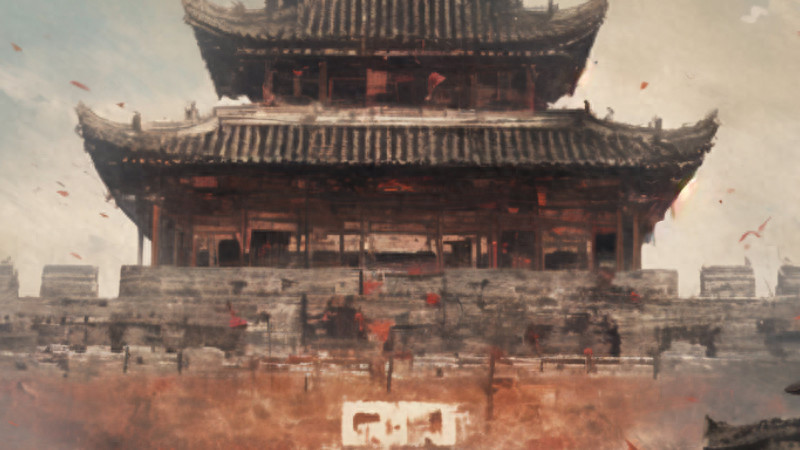文/黃禹康
1944年3月19日,是明王朝滅亡三百年紀念日,重慶《新華日報》連續刊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由于立場不同,國民黨認爲《甲申三百年祭》“影射當局”,對文章進行大肆圍攻;毛澤東則把《甲申三百年祭》視爲“勝利時驕傲”的鑒戒之史論,列入延安整風文獻,告誡共産黨人不要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針對獨裁,寫《甲申三百年祭》橫遭圍攻
20世紀40年代初,經過全民抗戰,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已經日趨明顯,抗戰已處于勝利的前夜。此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空前壯大,國民黨則竭力強化其專制統治。1943年初,蔣介石別有用心地抛出《中國之命運》一書,公開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論調。他還在書中搬出朱明王朝滅亡的事例,來爲其獨裁理論作論證,書中寫道:“明朝的末年,政治腐敗,思想分歧,黨派傾軋,民心渙散,流寇橫行。300年的明王朝,在李闖王、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與此同時,當年的七八月間中共中央針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輿論宣傳,“決定發動宣傳反擊”,指示重慶的《新華日報》和《群衆》周刊上“多刊登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鬥爭”,揭露蔣介石獨裁政權的腐敗和虛僞的真實面目。

◆《甲申三百年祭》封面。
1944年1月15日,重慶新華日報社委派喬冠華約請翦伯贊等人,前往郭沫若在重慶天官府4號的寓所集會,商量如何紀念明王朝三百年。對于這次集會,1944年3月,柳亞子在其《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一文的開頭寫道:“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收到于懷兄(即喬冠華)同月十六日從渝都發出的一封信,說道:‘今年適值明王朝滅亡300年,我們打算紀念一下,沫若先生們都打算寫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友閑談,大家一致認爲你是南明史泰鬥,紀念明王朝滅亡,非你開炮不可。’這時,我的神經衰弱病還是很厲害,腦子像頑石一般,不能發生作用,只好很抱歉地回信謝絕了他。”當時,幾乎各黨派、政界、學界,都把紀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動,看成是一次借用明朝腐敗抨擊蔣介石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使民主運動推進一步”的政治活動。
此時,正在從事《十批判書》寫作的郭沫若,基于對明末農民革命的興趣與革命文化界領袖的責任,也主動參與這一活動。據後來郭沫若在《十批判書·後記》中透露,在寫作《韓非子的批判》與《周代的農事詩》的前後:“我以偶然的機會得以讀到清初的禁書《剿闖小史》的古抄本。明末農民革命的史實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適逢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王朝滅亡的300年紀念。”郭沫若花費了一個月的時間,以詩人的激情和曆史學家的深邃思考,搜集資料,精心研究,認真分析,反複思考,于1944年3月10日完成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初稿。後來經過幾天修改充實,郭沫若將《甲申三百年祭》書稿鄭重送交當時中共中央駐重慶的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審閱。
1944年3月19日,《新華日報》開始連續刊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三百年前的3月19日正是李闖王進京、崇祯上吊、明朝滅亡的日子。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天報紙連載的《甲申三百年祭》前,特別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澤東的話:“今天的中國是曆史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曆史。”《甲申三百年祭》在《新華日報》連載4天,在社會上産生了強烈的反響。

194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重慶的機關刊物《群衆》第9卷第7期上也刊載了一組紀念明王朝滅亡的文章。其中,有柳亞子的《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贊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魯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風氣》、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學的時代意義》,這四篇文章主旨都是圍繞明末史事,抒發自己對現實的感受,恰好與《新華日報》發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相呼應。柳亞子除撰文外還賦七律詩一首:“陳迹煤山三百年,高文我佩鼎堂賢。吠堯桀犬渾多事,喘月吳牛苦問天。由檢師心終覆國,自成失計遂捐燕。昌言張李如能拜,破虜恢遼指顧間。”
面對圍攻,郭沫若蔑視論客們“無理取鬧……”
郭沫若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近兩萬字的史論。文章生動剖析了明王朝土崩瓦解和李自成功敗垂成的曆史原因和經驗教訓。文章不僅引發了人們對曆史興亡的感歎,還通過對明王朝、李自成和清兵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長的分析,使人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像崇祯那樣封建專制和腐敗沒落的統治政權必然是要滅亡的。
國民黨認爲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在“影射當局”,馬上組織專人對文章進行圍攻。1944年3月24日,爲蔣介石執筆撰寫《中國之命運》的陶希聖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題爲《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指責郭沫若“爲匪張目”,“將明之亡國的曆史影射當時的時局”,抨擊《甲申三百年祭》是“出于一種反常心理,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陶希聖在社論中還說:“三百年前,蔓延于黃河流域及黃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爲首領,于外患方亟之時,顛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結果是什麽?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國局面。”“郭沫若今天把流寇誇揚爲革命,把策應敵寇,斷送國家,滅亡民族的流寇誇揚爲革命,這不但是民族主義的羞辱,並且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玷汙。”
4月13日,《中央日報》又發表了《論責任心》的社論,責難《甲申三百年祭》“渲染著亡國的怨望和牢騷”。4月20日,葉青又在《政治月刊》上發表長篇專論《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評議》,同時還主編《關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一書,揚言“供防毒消毒之用”。他在書中攻擊《甲申三百年祭》“與共産黨的宣傳十分和合,共産黨要反對政府,這篇文章就盡力指責明王朝的腐朽統治,企圖喚起人民的聯想作用”。
4月21日、26日、28日,《中央日報》又相繼發表社論,攻擊《甲申三百年祭》,表示不能“聽其謬論流傳”,要“共同糾正這種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隨後,一些報刊也學著《中央日報》的腔調,異口同聲地攻擊《甲申三百年祭》是敗戰主義和“幫助了外寇”,甚至罵郭沫若爲“敵人的第五縱隊”。對于國民黨的攻擊,郭沫若在致美國費正清博士的信中稱,《甲申三百年祭》“本是研究性質的史學上的文字”,《中央日報》的社論是“無理取鬧的攻擊”,“我只感覺著論客們太可憐了,竟已經到了歇斯叠(底)裏的地步”。
延安整風,將《甲申三百年祭》視爲曆史的鏡子
駐紮在延安土窯洞裏的中共中央,對《甲申三百年祭》采取了與國民黨截然不同的態度。1944年4月18日至19日,延安的《解放日報》全文轉載此文,並加了編者按,指出:“郭沫若先生根據確鑿的史實,分析了明王朝滅亡的社會原因,把明王朝的腐朽統治與當時農民起義的主將李自成作了對照的敘述和客觀的評價,還給他們一個本來面目……無論如何,引起滿清入侵的卻決不是李自成,而是明王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任臣、不抵抗的將軍,以及無恥地投降了民族敵人引狼入室的吳三桂之流。吳三桂在後來又‘變卦’了,而且真的變卦了,不像現在有些吳三桂們,表面上‘反正’了,實際上還在替日本主子服務。”這篇編者按有力地反擊了3月24日《中央日報》發表的《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同時,《解放日報》還稱贊《甲申三百年祭》“充滿了愛國愛民族的熱情”,“在科學地解說曆史”,“蚍蜉撼大樹只是增加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的曆史價值而已”。

◆延安《解放日報》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全文轉載《甲申三百年祭》。
在延安《解放日報》轉載《甲申三百年祭》不久,1944年4月22日,毛澤東在《學習與時局》的報告中又提到了《甲申三百年祭》,他強調說:“我黨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發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爲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一反衆說,獨出新解,第一個提出《甲申三百年祭》所總結的曆史經驗是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政治部向全黨、全軍發出通知,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爲全黨的整風文件,要在解放區普遍印發,供黨內學習。通知稱:“郭沫若的文章指出李自成之敗在于進北京後,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脫離群衆,妄殺幹部,實爲明末農民起義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作品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幹部,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和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悲劇覆轍。”通知發出之後,各解放區紛紛開始翻印《甲申三百年祭》。
不久,林伯渠從延安飛抵重慶。他親自告訴郭沫若,黨中央、毛澤東決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爲延安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已經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廣泛印發。8月下旬,郭沫若又收到周恩來從延安托專人帶來的用陝甘甯邊區産的淡藍色馬蘭紙印的《屈原》劇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單行本。郭沫若看後備受鼓舞,當晚就提筆給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在延安的朋友寫信,感謝他們對自己的鼓勵和鞭策。
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親筆複信郭沫若。他在信中寫道:
“沫若兄:
大示讀悉。獎飾過份,十分不敢當;但當努力學習,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後,成天在工作堆裏,沒有讀書鑽研機會,故對于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曆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産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麽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麽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恩來同志到後,此間近情當已獲悉,茲不一一。我們大家都想和你見面,不知有此機會否?謹祝
健康、愉快與精神煥發!
毛澤東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郭沫若從毛澤東真摯親切和期許頗深的回信中看到,他精心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符合黨和人民的需要,得到了共産黨領袖的充分肯定,更增添了與蔣介石國民黨反動統治鬥爭到底的信心。
以史爲鏡,把勝利進京視爲“趕考”
其實,當初郭沫若撰寫《甲申三百年祭》,是想借明末政治腐敗導致民怨沸騰國家傾覆的曆史事實,揭示國民黨貪汙腐敗,喪失民心,必然會重蹈明亡覆轍的老路的道理,因此,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記述李自成的部分,只占全文極小的篇幅。但是,毛澤東卻偏偏看重其中李自成的曆史教訓。盡管郭沫若在文章中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中共中央卻主動將其作爲一面曆史的鏡子,號召全黨學習《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黨同志吸取李自成農民軍由勝利到失敗的曆史教訓,在勝利面前要經得起考驗,永遠不能驕傲,要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本色,以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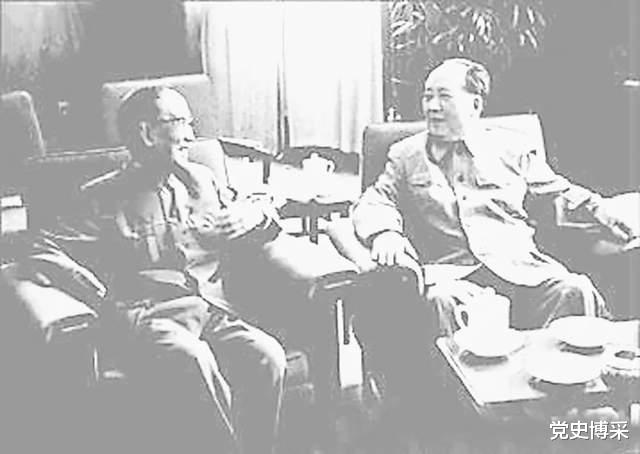
◆毛澤東與郭沫若。
從當時保存下來的各解放區整風學習筆記可以看出,一些黨員幹部拿這面曆史鏡子對照自己進行檢查,確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位宣傳處的副處長在筆記中寫道:劉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嚴重的反映。自以爲進過抗大,在115師打過大勝仗,立過大功,就目空一切,誰也看不起;講私人感情,同地方新來的同志不團結;高高在上,高談闊論,脫離群衆;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還成個什麽革命隊伍,也不會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場。一位政治部青年幹部也在筆記中寫道:我們現在還沒有進城,但是已經被城裏的花花世界迷了眼,總想吃得好一點,穿得好一點,還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說自己土氣,要是進了城,還能不被金錢、美女俘虜了去嗎?李自成起義軍的悲慘下場,真該我們警惕啊!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同年3月23日上午,毛澤東在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前,又提起《甲申三百年祭》中李自成的教訓。他形象地比喻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退回去就算失敗,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李自成進京後就變了。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
“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經超出史學論著的範疇,成爲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的曆史鑒戒。尤其是文中“慎終如初”的觀點,很值得黨員領導幹部借鑒。今天,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征程中,我們仍要始終牢記李自成的教訓,始終牢記毛澤東的“要考個好成績”的教誨 ,自覺踐行“兩個務必”的諾言,不斷加強黨性鍛煉,努力向人民交出一份優異的考卷。
本文爲《黨史博采》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