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凝視”或者“男凝”(male gaze)是互聯網高頻詞,尤其常見于有關性別關系的討論之中。但是,它究竟是什麽?它是在說,男性僅僅是注視女性,就構成了侵犯嗎?那麽“女性凝視”對男性就不構成傷害嗎?
當下,觀衆對影視作品中女性角色的邊緣化和性客體化問題表現得越來越敏感。例如,去年熱播的《漫長的季節》就因“爹味”而引發爭議。近期爆火的《周處除三害》所呈現女性形象也令不少女性不適。在經曆了女性主義啓蒙後,女性在觀看影視作品時,總能感受到一種“顛簸”。也就是當她們享受劇情時,突然被男性凝視所打擾而陷入眩暈。

《周處除三害》劇照,圖爲程小美。
雖然《周處除三害》是部不錯的影片,但是它在處理女性角色方面仍存在諸多男性凝視的鏡頭,以及將女性角色工具化的問題。女性當然應該尊重自己的感受,既不否認整部作品,享受它帶來的愉悅,也要勇于承認自己的不適,表達自己的敏感。這一原則同樣適用于男性觀衆,當他們被女性主義作品冒犯時,也應當直面自己的怒火,同時保持對怒火的思考。
即便我們僅僅是爲了娛樂而觀看影視作品,也不意味著對作品的深入分析是在上綱上線。如果電影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遐想,點燃了情緒,那麽它就是在“刷新”觀衆。它在挑戰觀衆看待世界的方式,並給予了觀衆新鮮的思想刺激。更重要的是,一部好作品是不同群體展開對話的良好契機,如果說性別化的社會分工導致兩性面對著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麽評論影視作品或許是打破隔閡的最便捷方式。
兩性不必然懷揣防備漸行漸遠,而可能放下傲慢與偏見,以善意討論走近彼此。這種善意源自人類對與自己不同的“陌生人”的好奇和尊重。從創作端來看,女性創作者的參與對于電影和電視劇中女性視角的展現至關重要,與此同時,男性創作者也不必然被性別視野所局限,同樣可以制作出兼顧女性視角甚至女性解放立場的電影。

撰文 | 豬迅兒
工具化的女性角色
在正常的社會交往中,人們自然而然會相互凝視,它是一種充滿豐富心理活動的觀看。若單純從凝視者的意圖或被凝視者的不適感出發,我們無法全面定義“男性凝視”。然而,當考慮到權力關系的存在後,凝視變成了一種力量的遊戲:凝視者處于主導地位,被凝視者則陷入被動、受控制的境地。這種不平等的動態,讓被凝視者的脆弱和不安感變得可理解。部分女性在公共場合中“過于敏感”地指責男性偷拍,正是對被凝視者處于不平等關系中所經曆的不安全感的直接反應。
英國理論家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最早針對電影提出了“男性凝視”概念。總的來說,在男性爲主導的影視創作産業中,女性形象常常是按照男性觀衆的欲望和想象來塑造的。這主要體現爲對女性身體的性客體化呈現,以及對女性角色的刻板化和工具化塑造。穆爾維提出,電影中實際上存在著三種“觀看”,分別是角色之間的、觀衆的和攝影機的凝視。
最明顯的是通過電影中男性角色的目光來體現的男性凝視,此時女性角色被塑造爲被動的觀看對象。這種現象在鏡頭運用上體現爲對女性角色的特寫,將她們變成了男性角色和觀衆的視覺盛宴。比如《滿江紅》中的瑤琴,她過分香豔的卻對情節和人設都缺乏推動的被強暴鏡頭,旨在滿足觀衆的窺陰癖。“符合曆史”的理由則是最好的掩體,使得目睹這一切的男主、導演和觀衆都得到了道德赦免。這類情況極具代表性,它圍繞著女性角色的性吸引力來使用特寫,觀衆通過男性角色的眼睛觀看故事,體驗其欲望和沖突,而女性則成爲生機勃勃的虛幻景觀。

《滿江紅》劇照,圖爲瑤琴。
另一種情況是對女性角色的刻板化和工具化塑造,故事往往圍繞男性角色展開,女性角色只是欲望對象或支持者,她們的行動和情感都只圍繞著男主的目標展開,而自己的經曆和感受常常被邊緣化。《周處除三害》中的程小美就是一個完全的工具角色,她過分單純的人格狀態與她被黑幫性侵多年的人生經曆脫節,她的存在似乎只是爲了展現男主陳桂林超凡脫俗的少年氣概和純真的情感。

《周處除三害》劇照,圖爲程小美。
在穆爾維看來,大量電影制作提供了一種以男性視角爲中心的觀看經驗,這意味著,電影在敘事結構、角色設計和視覺呈現上,都主要是爲了滿足男性觀衆的欲望。在這種情境下,女性觀衆在觀看的過程中,往往不自覺地以一種“男性化”方式來理解和感受電影,從而進行自我客體化。
但是,如果電影明確定位爲男性受衆,是否就意味著我們應該無視女性的客體化呢?否認性物化女性會給男性帶來最原始的感官刺激,這是否是一種不承認現實?可是,什麽是現實?現實注定不可改變嗎?特裏·莫裏(Terri Murray)在《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研究》中提出的一個類比能夠回應此類問題。如果我們不斷向兒童提供糖果,宣傳糖果,四處開設糖果店,然後又聲稱孩子們“天生”就喜歡糖果而非健康營養的食品,這顯然十分荒謬。就像我們明知道糖果含糖量高、營養價值低,就不應該大力推廣它一樣,承認原始沖動存在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迎合、鼓勵這些沖動。至少,應該允許揭露“糖果缺乏營養價值”這一事實的聲音存在。
最後,所謂“攝影機的觀看”實際上是在說創作者意圖和理解。電影腳本和拍攝的創作者通常是男性,他們的視角和意圖影響了電影的敘事和視覺風格。當這類電影還意圖利用女性覺醒的情緒時,後果就更爲惡劣。

《消失的她》劇照。
《消失的她》就是這樣一種電影。它以性別對立的方式,刻畫出絕對醜惡的渣男何非,可笑的是,他卻是全片唯一一個行爲邏輯連貫的角色。與此同時,受害者李木子的死亡中所蘊含的絕望、恐懼和猙獰,都被這種淒美釋然所掩蓋,正如女性的真實困境在犧牲頌歌中被掩蓋。李木子的閨蜜陳麥以“你殺了最愛你的人!”“她懷了你的孩子!”來譴責凶手,這種譴責是極端男性中心的。它將女性放在邊緣位置,作爲自然的欲望客體,來提醒男性應當對其犧牲表示憐惜。這種極度不真誠的對女性的憐惜,其本質是在以一種美化和弱化理想女性的方式,再次增強男性中心的邏輯。
女性的“男凝”與“凝男”
從觀衆的角度看,僅憑生理性別爲女,並不能自動擺脫“男性凝視”對她的審美影響,有時甚至更可能陷入迷戀。以《周處除三害》爲例,很多女性觀衆並不會對程小美這樣的角色設定感到排斥,反而代入了這個被迫害的,同時也純潔無瑕、拯救他人的女性角色,並沉湎于一種自我感動。這類女性觀衆在面對電影中的“男性凝視”時,會呈現出多重的微妙態度。

《名偵探柯南》劇照。
《名偵探柯南》是一代人童年回憶的代表,其中,純潔善良爲愛守候的毛利蘭,作爲“服務型”女主的典範引發了衆多女性劇迷的共鳴。很多女性共情于女性角色的“利他屬性”,並認爲這就是女性特質。她們樂于被贊譽爲“家宅天使”,對“解語花”“大飒蜜”之類的角色頗有好感,這可能源于她們對關注和認可的渴求。這類觀衆讓人聯想到《性愛自修室》中的愛米(Amiee),那個性格柔順遲鈍又可愛奔放的“兔牙妹”。愛米最初完全不明白自己喜歡什麽,在戀愛和性關系中,她也只會遵循從色情片中學到的、以男性偏好爲中心的方式呈現自己的身體,並從“自己被他人愉悅地使用”中誤讀自己的滿足。
另有一部分女性受衆沉迷于女性角色的“被迫害性”和“犧牲性”。她們對“苦情美學”産生了強烈共鳴,沉浸于這種淒美的犧牲。這種美感來源于對苦難的美化。在這些劇情中,男性往往既是女性苦難的根源,又是女性的拯救者。比如《周處除三害》中的程小美,她不僅不可避免地遭受著“香港仔”的淩虐,又被陳桂林所解救。正是由于“香港仔”的暴虐被描繪爲如常的、自然的男性欲望,從而使陳桂林的拯救行爲顯得格外純粹和出衆。

《周處除三害》劇照,圖爲程小美與香港仔。
喜愛這類角色的女性觀衆往往沉浸于一種深刻的“無價值感”中,她們甚至“覺得自己很不堪,不希望連累他人”。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她們感動于電影中女性的痛苦和磨難,從而加深對自我犧牲情感的認同,獲得一種奇異的滿足感。這種審美機制的根源可能在于深層的文化認知和社會化過程——女性從小被教育要時刻顧及他人、犧牲自我,同時又是脆弱的、珍貴的。這類影視作品因此成爲強化這一男權文化中將女性痛苦自然化的媒介。
還有一類女性觀衆更加複雜,她們對程小美的偏好與對“瑪麗蘇”的偏好機制相似。在這類女性觀衆喜愛的作品中,男性角色通常被描繪爲權威型或奉獻型的形象,這裏的陳桂林既是霸道的黑道大佬又是不圖財色的救星,而女主角的設計雖然融入了一些現代女性特質,在根本上還是更符合傳統的性別期待。雖然這種敘事似乎依托于男性的主體位置,女主是相對的客體,但這只是爲了合理化女主能夠獲得絕對關注的現實。在這裏,女性作爲“被凝視的群體”和“喜愛並享受凝視的個體”是截然不同的情況。這類女性觀衆展現出了覺醒意識和她們對傳統女性魅力的認知之間的沖突。
需要明確的是,以上分析旨在提供對現象的理解,而非評價或比較女性觀衆的優劣,爲的是深入探討一部分女性觀衆的心理動態和審美偏好是如何受到“男性凝視”主導的影視作品所影響的。同時,女性觀衆的日益增多,的確促進了影視行業對女性視角的重視,也加大了對女性角色塑造的投入。雖然女性的“凝視男性”並不必然呈現爲一種抵抗,但它無疑對長期由男性主導的影視産業産生了挑戰,也加強了女性在媒體和文化消費中的影響力。但是,那些工業糖精式的瑪麗蘇戀愛劇和販賣男色的影視營銷等,可能還是在沿襲父權社會塑造男女關系的老路。這些作品有時可能是遮掩現實問題的致幻劑,或者簡單地顛倒了支配性的權力關系,反而加劇了這種權力模式的影響。
有趣的是,當女性成爲創作者時,有時候“男性凝視”會以一種更巧妙的方式被轉變爲“凝視男性”。女性創作者往往傾向于生長出一種直覺性的“反男凝意識”,它的一種體現方式爲,對男性中心而非個體男性的洞察與嘲弄。當這種反諷要通過個體角色表現出來時,創作者往往會同時展現出這個角色可被理解、可憐或者可愛的部分。電影《熱辣滾燙》的導演賈玲就是如此。

《熱辣滾燙》中的樂瑩。
賈玲通過女主角樂瑩的視角,展現了女性導演對這個充滿“男性凝視”的世界的深度把握——在這種凝視之下,女性的價值往往取決于外貌等級。肥胖女性被邊緣化,遭受嘲笑和惡意。因此,肥胖期的樂瑩展現出一種抑郁和無奈,但她卻以自我合理化的方式,對嘲笑者展現出一種理解與悲憫。

《熱辣滾燙》中的樂瑩。
如果無法理解這種來自邊緣的對中心的悲憫,就無法理解樂瑩學習拳擊的動力,也就是一個基層肥胖女孩“轉變”的動力,這是很多男性影評人和觀衆無法理解這部電影的原因。樂瑩不需要仇恨,不需要在這個現實卻愚蠢的權力等級制度中獲得“承認”。她練習拳擊,只是爲了獲得自在地做自己而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自己的空間,這就是《熱辣滾燙》所要刻畫的“贏”——在經曆了惡意後,能夠以直報怨,保持內在世界的穩定和溫柔。“贏”不是去暴力地顛倒“男凝”,而是要輕巧地超越“男凝”。
女性導演之所以選擇某一女性主題進行創作,是因爲她們“想要表達”。這種表達不一定有清晰的女性主義意識,不一定會進行尖銳的、犀利的或者系統性的批判或反思。創作可能僅僅起于一種“察覺到不對勁”的感知,它被一種無意識的直覺所驅動,最後呈現出溫和真誠的女性敘事。
創作者如何超越男性凝視?
雖然女性創作者相比于男性創作者更可能傾向對“男性凝視”産生直覺性的對抗,但是部分女性觀衆可能會不自覺地欣賞並接受那些服務于父權制文化的女性形象。這表明生物性別與“反男性凝視”意識並不直接相關。與此同時,男性創作者也完全有能力創作出體現良好性別意識的作品,無論是作爲創作者還是評論人,在塑造女性角色時,他們都可能擁有多樣化的策略和視角。
從創作角度來看,在塑造女性角色時,打破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同時維持合理的人物邏輯是至關重要的。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on)在《殺死比爾》中,通過女主角崔克斯·基多(Beatrix Kiddo)的複仇故事,以漫畫式的誇張手法,塑造了多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這些角色展現了女性在大銀幕上運用暴力的正當性和能力,她們不僅不再重複著被暴力脅迫的受害者角色,而且在獲得新力量的同時也不必犧牲傳統女性的美麗、母性等特質。雖然《殺死比爾》並沒有完全摒棄關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但它卻爲那些陳舊的印象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殺死比爾》劇照。
我們很難說昆汀是一個性別意識很強或尊重女性的導演。但是在《殺死比爾》的創作過程中,他認真地聽取了飾演女主的演員烏瑪·瑟曼(Uma Thurman)在角色塑造方面的建議。這對其他男性導演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啓發——即便他們不願意主動接受女性主義思想,也可以通過真誠地傾聽女性的觀點和體驗來創造女性形象。放下傲慢,聆聽女性對于自身的真實感知和思考,或許是創作出優秀作品的關鍵。
影視作品對抗“男性凝視”的另一種策略更爲激進,它試圖探索一種去意義化的表達,嘗試跳出父權制世界的意義框架。在最近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中獲得多個獎項的電影《可憐的東西》就是這類嘗試的代表。《可憐的東西》講述的是女主角貝拉(Bella)的故事。貝拉是一個融合了成熟女性身體和嬰兒大腦的“科學怪人”。電影呈現了一場不受束縛的冒險,它十分嚴肅地討論了“性”。

《可憐的東西》劇照。
值得探討的是,這部電影或許並不是在展現女性的現實經驗,而是在質問“性”的可塑性。這種探索徹底無視了對“女性是第二性”這一可悲現實的反抗,而這是普遍意義上女性主義政治的前提;它另起爐竈,聚焦于“性”本身,“性”依然是女性主義所關心的最本體的事物之一。雖然男性導演可能對女性的苦難和困境理解不深,但依然可以針對“性”這件事,提出極先鋒的拷問——性的去父權制是否能成爲出路。
本片遭受了諸多質疑,這些質疑都是情感真摯或深入現實的表達。但是,從影視評論和觀衆的角度來看,對于一部真誠而冒進的作品,或許不應該采用全盤否定式的批評。如果我們認爲圍繞著女人的“性”展開就是“男性凝視”,這種過于單純的標准實際上在將女性固化在一個絕對的弱勢位置上,並很可能通過這個道德高位扼殺創造力。創作永遠是風險之旅。這種探索充滿了未知,它不僅可能冒犯男性,也可能冒犯女性,《可憐的東西》就是如此。
最後,當我們用最真誠的感知去面對一部作品,去體會自己的被吸引與被冒犯時,我們便在豐富自身靈魂的領悟力。同時,我們也應該帶著善意去同情和理解具備真誠性和先鋒性的電影。畢竟,影評也參與構建了作品的深層意義。對于抵制創作中的男性凝視問題上,觀衆的角色尤爲關鍵。我們期待一個什麽樣的世界,首先需要以我們所希望看到的方式去積極影響這個世界,它也體現在我們對作品的態度和解釋之中,這些行爲和思維方式終將成爲夢想世界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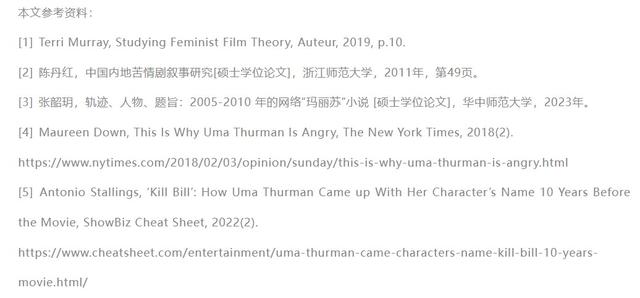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豬迅兒;編輯:走走;校對:薛京甯。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