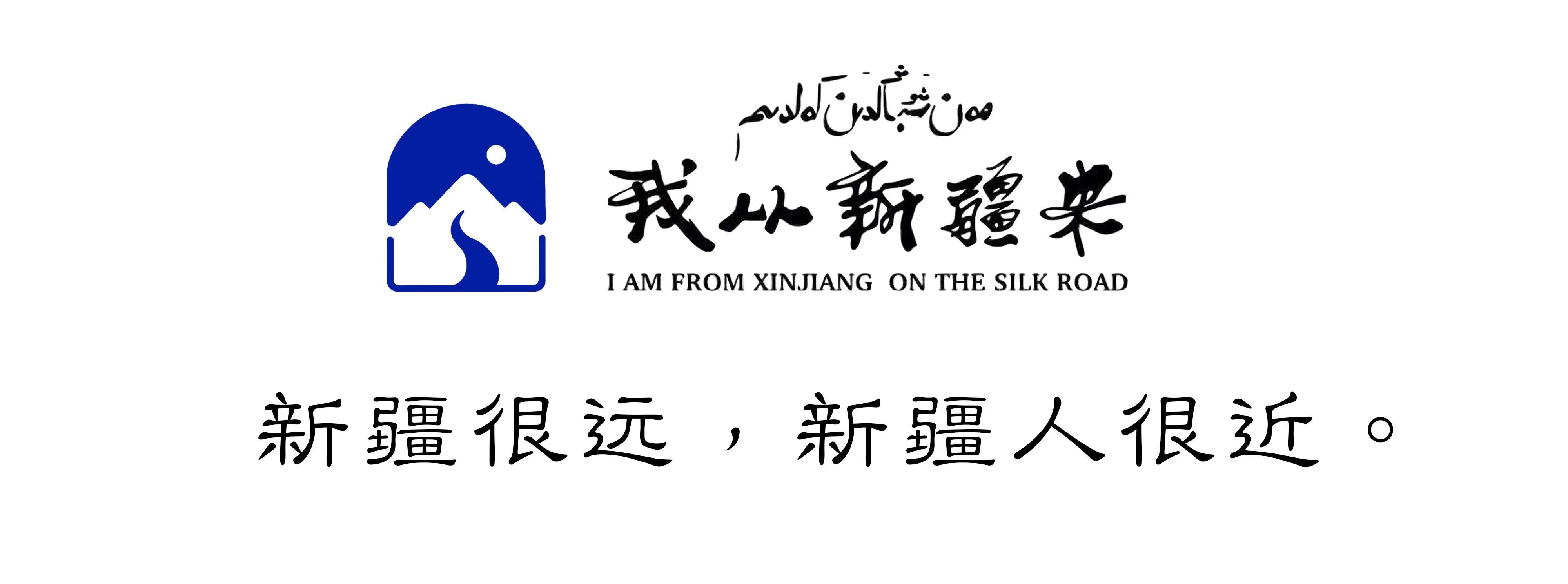 “每個人最終都會活成自己的家鄉。”
“每個人最終都會活成自己的家鄉。”蜿蜒靜谧的克蘭河水,童話世界般的白桦林,聖潔壯闊的阿爾泰山脈……阿勒泰賦予了巴燕·塔斯肯寫作的力量,他的作品浸透著對家鄉的熱愛及對生命的敬仰。
年僅一歲時,巴燕就被父母送去了阿勒泰市的拉斯特鄉諾改特村由爺爺奶奶撫養,那時的他總覺得命運對自己太不公平,讓一個鮮活的生命陪伴著兩個即將走到時間盡頭的老人,這是多麽殘忍的一件事情。
然而時至今日,他稱那段時光才是“想的生活”。
他對那片深深烙印在心中的故土——諾改特村,懷有一種無法割舍的眷戀。
這種情感促使他在字裏行間不斷地回溯與感慨家鄉的美好。
克蘭河畔的童年
回想起童年,巴燕總會想起阿爾泰山腳下四季的輪回、日夜的交替;諾改特村率真又善良的鄰居;陪在自己身邊的爺爺奶奶、小姑,以及陪他一起生長的地裏的莊稼、圈裏的牲畜、屋後的白桦林。
1999年,他出生在阿勒泰的一間租賃房內,母親在鄉政府工作,父親做牛羊生皮生意,經常奔波在農民家和工廠之間。
于是,巴燕在一歲時被父母送去了諾改特村,那片他曾無數次想逃離的土地,如今卻成了他的根。

▲一歲時的巴燕
住在爺爺奶奶身邊,巴燕覺得自己就是家裏的小王子,仿佛可以上天入地。
那會兒家裏唯一結婚生子的只有他父親,巴燕作爲家裏第一個孫子,得到了長輩的寵愛,家裏有什麽好事大家都想著他。
“阿勒泰系列”是巴燕以在故鄉阿勒泰度過的童年時光爲背景創作的散文系列,他在其中寫到了許多發生在諾改特村的趣事:想搶走奶奶的朱馬希爺爺,總是讓“我”好奇的大力士穆拉提,陪伴“我”建造秘密基地的哈薩克牧羊犬“白兔”……
除了爺爺奶奶之外,巴燕和小姑相處的時間最久。
哈薩克民間習俗中,有一種名爲“圖倫”的發型,是給未做割禮的小男孩留的兩撮長發。
巴燕想起小姑經常想給他理“圖倫”,卻被自己拼命反抗,奶奶聽到孫子的告狀後便會“收拾”小姑,但小姑還是會趁巴燕睡著時把他的頭發剃幹淨,讓他再也沒有吵鬧的機會。
巴燕算是被送給爺爺奶奶撫養的半個“還子”。
在哈薩克族的傳統習俗中,“還子”作爲家裏第一個孫輩,一般還于老人撫養。
盡管因工作原因,父母不得不讓巴燕與爺爺奶奶一起生活,但他們仍傾盡所能,關心巴燕的成長。

▲巴燕與爺爺奶奶和父母的合影
小學四五年級時,巴燕只有放假才有機會回到諾改特村。
最初回到父母身邊時,他很不習慣,就像來到陌生人家一般。
半年後,待他逐漸適應城裏的生活,在假期又被送到鄉下生活,不斷地在爺爺家和父母家兩地徘徊,讓他偶爾産生在城市和村莊之間迷失的錯覺,同時來自父親和爺爺這兩種角色的愛,時常讓他感到忽近忽遠,患得患失。
但隨著年齡的增大,他慢慢適應了這種變化,他意識到家人永遠是那個一直願意爲自己毫無保留地付出一切的人。
“在我看來,我從父母那裏得到的愛和我從爺爺奶奶、小姑,以及其他叔叔們那裏得到的其實沒什麽差別。”不同形式的愛更是讓他擁有了難忘的童年。
巴燕成長于諾改特村克蘭河下遊的山腳下,從小跟著爺爺奶奶度過了半農半牧的定居生活,擁有了城市小孩難以觸及的生活體驗,這份獨特的成長背景,成爲了連結他與大自然的紐帶。
他們一家居住的位置離其他住戶都很遠,身邊幾乎沒有同齡玩伴的巴燕經常會自言自語或者和牛羊說話,這會讓他覺得與“人”打交道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
“當時的我會有一種莫名的熱情和期待,希望能遇到陌生人,能和他們聊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起初,諾改特村的路要麽是草地,要麽就是黃土路。
每逢雨季,黃土路便飽受洪水侵襲,泥濘不堪,形成處處難以行進的泥潭;而冬季雪落之時,路面則被皚皚白雪覆蓋,通行更爲艱難。後來草原修建新的路,方便了諾改特村通往牧場的交通。
從土路、水泥路再到柏油路,隨著路修得越來越好,巴燕一家就會見到很多人、聽到新鮮的事情,山裏山外的世界漸漸融爲一體。
從此,村裏人的生活也不再那麽乏味。

▲諾改特村部分晚秋風光
每年春天發洪水時,巴燕和爺爺經常會在河邊撈起被水沖走堆積在一起的大小樹枝、枯木幹,一個個帶回家,把它們曬幹後儲存,留著過冬。
被他們撿走的除了木柴,還有遊客扔下的垃圾。
爺爺在屋後用鐵鍬鏟除土坑,推著手推車將那些食品包裝袋和塑料瓶運到土坑裏,燒毀它們,這讓巴燕很是不解。
遊客的到來能爲這片寂靜的土地增添人間煙火氣,但他們又會帶來許多垃圾,讓爺爺和自己來撿,這種時候爺爺總是對巴燕說:“我們身體裏的血液,一半是母親給的,一半是克蘭河給的。我們從河裏得到了這麽多東西,也要爲它做些事情。”

▲小時候的巴燕與爺爺
在巴燕這二十多年的成長過程中,爺爺在他性格的養成、對文化的認知及價值觀的形成方面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巴燕的爺爺是在新疆農業大學最早就讀的一批學生之一,但因受饑荒等自然災害的沖擊,不得不回歸遊牧生活。
盡管生活環境轉變,爺爺始終保持著對知識的熱愛,博覽群書,並時常以生動的故事滋養巴燕的心靈。
哈薩克族是遊牧民族,因其受自然環境和生活習慣等因素的影響,同多數其他遊牧民族一樣,使用文字記錄的文獻是少之又少。
相反,口頭文學在近代哈薩克文學出現之前是最繁榮的,例如,三大史詩《瑪納斯》《江格爾》《格薩爾》也是三個不同的遊牧民族口頭文學的經典代表作。因口頭文學的繁榮,幾乎每位哈薩克老人都是“聽書”聽了一輩子。
受口頭文學的影響,從古至今哈薩克人會通過給孩子講故事的方式教育他們。
哈薩克族是一個不缺英雄的民族,所以每個小孩從小都是聽著祖輩的英雄事迹長大的,也因此培養了他們不屈的精神。
對于小時候的巴燕而言,他對外面世界的認知幾乎是一片空白,而爺爺的存在就如同一部行走的百科全書,任何問題都能得到他的解答。


“我從爺爺那裏學到了很多,可以說我的三觀就是在傳統的哈薩克式教育下建立的。”巴燕通過爺爺講述的一個個故事,得以窺見他們那一代老人經曆的風雨滄桑。
這些故事在他心中播下了智慧的種子,以至于當許多年後巴燕親身經曆相似的人生挑戰時,內心已然有了足夠的准備與勇氣,能夠坦然面對並戰勝那些困難。
“克蘭河畔的春天是慢慢來的,是突然發現的,是悄悄走的,是永遠懷念的。”克蘭河畔的童年時光成爲了巴燕永恒的記憶。
這些被歲月精心雕琢的片段,日後不僅成爲他創作靈感的重要源泉,更在他的妙筆生花之下,栩栩如生地重現在了字裏行間。
從懵懂頑皮到文學探索
初高中階段,巴燕在學校是一個“小壞蛋”,或許正是源于成長在溫馨寵溺的家庭氛圍中,他在學校非常調皮,難以專注學業。
在高二下學期,當班主任開會告訴同學們要准備高考時,巴燕才知曉高考和中考的不同性質。
“我以爲高考也像中考一樣,把我們分配到不同的學校,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場競爭激烈的考試在等著我。”
從小到大,巴燕覺得自己從來沒幹過一件讓家人驕傲的事情,當別的大人顯擺自己的孩子時,他只會給家裏人帶來麻煩。
爲了讓父母和爺爺奶奶省點心,讓他們開心點,巴燕下定決心在高三鉚足勁兒學習,提高成績。
“高三那一年是我成長最快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真的該長大了,也要去擔一些責任了。”
那段時間老師和同學在學習上爲他指引了方向,只要有一點進步,老師們都會表揚他,給予他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通過一年的努力,巴燕順利考上了廣州大學。

▲2018年,巴燕前往廣州求學之前與爺爺奶奶的合影
在正式進入大學之前,巴燕並沒有系統接觸過寫作,等上了預科,他有幸在寫作基礎課中結識了一位帶他走進文學大門的雷淑葉老師。
最初,巴燕只是爲了應付作業而去寫文章,寫出來的文章就跟小孩子寫的一樣,停留在高中語文作文的形式,直到有一節課,老師布置了一篇關于故鄉的寫作任務,這讓巴燕十分感興趣。
那時候正是2018年12月,不久前巴燕從家裏接到了爺爺得癌症晚期的消息。
他本想休學回到阿勒泰陪爺爺度過最後的時光,卻遭到了父母的勸阻,爺爺更是不希望讓孫子看著自己難受。
在學校,巴燕想念家鄉和家人的情緒達到了頂峰,每天向父母打電話詢問爺爺的情況,父母告訴巴燕爺爺並無大礙,但巴燕心裏明白爺爺的食道早已無法進食,只能靠營養液去維持生命。
巴燕的思念和痛苦沒法和身邊的人訴說,那篇讓雷老師贊歎不已的文章成了他的發泄口。
由于時間久遠,現在已經找不到那篇文章,但巴燕至今記得文章得到了老師的肯定,老師誇他有寫作天賦,其中的情感很真誠、純樸。
“我發現自己很喜歡得到別人的認可,我能感覺得到老師讀懂了我寫的內容、表達的情感,那一瞬間我就充滿了動力。”

後來,巴燕選擇了漢語言文學專業,他堅持寫文章,拿給雷老師看。
盡管他起初的作品略顯稚嫩,但老師每一次都是逐字逐句修改批注,告訴他怎樣才能寫得更好。
老師還會在自己的公衆號上幫他發表文章,它們在學校內引起了不錯的反響,這讓巴燕覺得寫作是一件值得他一直堅持的事情。
巴燕的父親平時也會用哈薩克語進行文學創作,當父親第一次聽到兒子想要寫作時,便極力推薦了藏族作家阿來的《塵埃落定》。巴燕僅用了短短兩天時間讀完了這本書,而且深深爲其所吸引,愛不釋手。
隨後,父親陸陸續續推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書籍,例如莫言的《紅高粱》、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他慢慢開始領略文學作品的魅力,沉浸在文字的世界。與此同時,他也爲自己未能更早地接觸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而感到一絲遺憾。

▲2021年,巴燕從廣州大學畢業
除了閱讀文學名著外,巴燕也喜歡讀詩,久而久之,他開始嘗試寫詩。
上大學時,一位遠方的筆友給他寄了一本河南詩人王海桑的詩集。
在這之前,他也讀過其他詩人的詩,但王海桑的詩帶給他的觸動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些詩娓娓道來詩人所做之事、所見之景及內心波瀾,那些看似平淡無奇卻又熠熠生輝的文字猶如磁石般吸引著巴燕一頁頁地讀下去。
受到王海桑風格的啓發,巴燕開始了仿效之旅,每寫一首詩便拿給雷老師閱讀,雷老師對他的作品表現出了由衷的贊賞。
隨著創作實踐的積累,巴燕察覺到自己的詩風正悄然發生轉變,盡管受到了王海桑的影響,但他寫的內容不再局限于詩歌的形式,而是更貼近散文的韻味。
這些變化同樣被敏銳的雷老師捕捉到,並認爲他或許更適宜于散文創作。
散文較之于詩歌,其最顯著的優勢在于其“形散神不散”的結構特征,這讓巴燕愈發渴望擺脫音韻節奏與修辭工整的限制,能夠隨心所欲地寫出所思所想,真實且細膩地記錄下內心的點滴感觸與思考。
重塑記憶中的阿勒泰
“故鄉,是我們年少時想要逃離的地方,是我們年老想回,可能已經回不去的地方。”
巴燕在《行走在土地上的人》中寫道:“我被困在白桦林中的那些年,常抱怨命運對我太不公平。在這顆充滿了生機的星球上,一個鮮活的生命陪伴著兩個即將走到時間盡頭的老人,生活在山腳下的小村莊中。他們不能陪我奔跑,不能爬樹,不能讓一顆大石頭去照顧另一顆小石頭……”
剛來到白桦林的巴燕一直覺得自己很孤獨,那顆狹隘而渴望自由的心讓他整天幻想著有人帶自己走出天井。
後來走進大學、踏入社會,巴燕無比思念童年。
他身邊的大學同學都因爲遠離家鄉、遠離父母而開心時,巴燕一心想著放假回家,關于那片白桦林的一切,都成爲了他日思夜想的根。

巴燕以前夢想過念完大學後,回到諾改特村,住在自己原來的房子裏,但所有的東西都在發生變化,現在的諾改特村早已物是人非。
曾經荒無人煙的大草原上,現在最不缺的就是鱗次栉比的木屋和接連不斷的遊客。
盡管新的發展讓人欣慰,但巴燕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他所熟悉的那片原始而蒼茫的大草原,那個古樸靜谧的村莊。
正如他在其作品中所述:“一個遊牧人的一生,是生在一片土地,卻死在另一片土地的一生。我們幾代人的生命好像全用來丈量一條河,從上遊到下遊。”
巴燕想起自己剛來到大學時,他身邊幾乎沒有任何同學了解哈薩克族。
“我當時很難過,如果內地的朋友通過我的文字,能夠對這個來自邊疆的遊牧民族多一些了解,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甚至世界觀、價值觀,那我的文字就是有價值的。”
2019年,巴燕讀了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這本書給他對原生作品的理解打開了一扇窗。
後來又接觸到作家劉亮程的作品,巴燕心想:“這些前輩們已經把那片土地寫得這麽好了,我還有什麽可寫的。”
但隨著閱讀的深入、和不同民族的朋友交流,他意識到,其實同一個主題可以有無數個維度和視角來诠釋。
他是土生土長的哈薩克族,他可以以哈薩克族的身份,用最真實的文字把這一民族對山川萬物的感受,對文化和世界的認知寫進自己的作品,展現給讀者。
人與人、人與動物、植物、大自然的關系在巴燕的筆觸下顯得淋漓盡致,那些飽含深情的文字流淌著對自然界的崇敬之情,對生命奇迹的贊美,以及對孕育萬物的大地的無盡感恩,無不展現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深遠哲思。
“我的性格,對待別人的方式,對周圍事情的態度,包括我寫作的風格都是受了那個村莊的影響。”
大草原、淳樸的家人、簡單平凡的遊牧生活讓他擁有了單純、坦率和直接的性格。
每寫完新的一篇文章後,在重新讀的過程中,他經常會覺得這些溫柔、細膩的文字像是出自女孩的筆下。

▲2023年夏天,巴燕在魯迅文學院進修
《雲邊有個小賣部》裏有這樣一句話:“在大多數人心中,自己的故鄉最終會成爲一個點,如同亘古不變的孤島。”童年、阿勒泰,還有那片白桦林成爲了巴燕寫作靈感的源泉。
“我知道什麽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巴燕很慶幸自己在年少時就體驗到了理想的生活。
這是在他鄉求學、打工、流浪的人無法體驗到的,他們渴望但又因爲現實原因沒法經曆的生活。
無論是好看的風景,好玩的事物,還是他從爺爺奶奶那裏得到的不可複制的愛,這些都是他這一輩子最珍貴的記憶。
諾改特村對于巴燕而言,一直都是心靈的寄托、精神的原鄉,但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不只是故鄉的面貌,它所承載的豐富的曆史、文化和民俗在漸漸地消失。
在這樣的環境下,接受一次又一次不同文化的沖擊後,巴燕覺得自己相比以前變得求同存異了。
即便曾經的諾改特村早已一去不複返,但他也看到了故鄉在發展變化中所展現出的頑強的生命力和無限的潛力,這讓巴燕在渴望保護民族文化精華的同時,也希望可以去其糟粕,使其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

▲巴燕位于現桦林公園的沙裏夫汗陵
在寫作這條路上,巴燕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除了文學啓蒙教師雷老師,每一位讓他在寫作領域成長、堅持下去的前輩讓他成爲了現在的自己,他們的認可和鼓勵也是巴燕繼續創作下去的動力。
文學作品不同于其他藝術類型,有人看到它、談論它,無論是說它的優點還是不足,總歸是屬于好事情。
在巴燕看來,沒有讀者、沒有人討論的作品,寫得再好也沒有任何意義。
不同于散文,小說給寫作者的發揮空間是更大的。
未來,巴燕想嘗試出版自己的書,想繼續把阿勒泰系列寫下去,也會嘗試更多不同的題材。
小時候的他有無數個夢想,當兵、拳擊手、運動員、導演,卻從未想過會走寫作這一條路,但現在的他,成爲了作家巴燕。
如今,巴燕在一家外貿公司上班,一旦有空閑時間,他便投入到文學創作。
也許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他已下定決心繼續走下去。
在他的筆端之下,記憶中的故鄉和童年的景象仿佛穿越時空,一一再現,複歸最初的純真與美好。
-END-
本文由“我從新疆來”原創,歡迎關注,帶你了解熟悉而又陌生的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