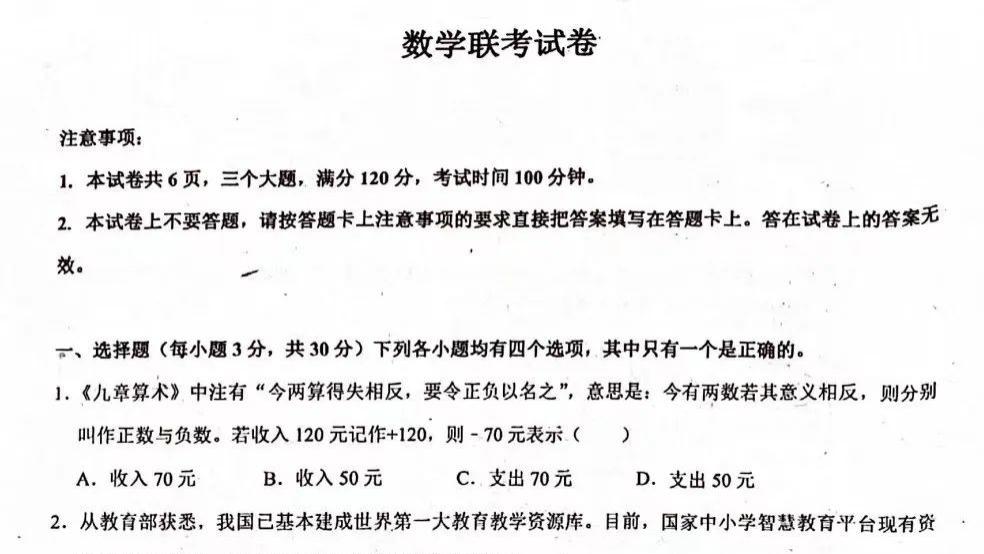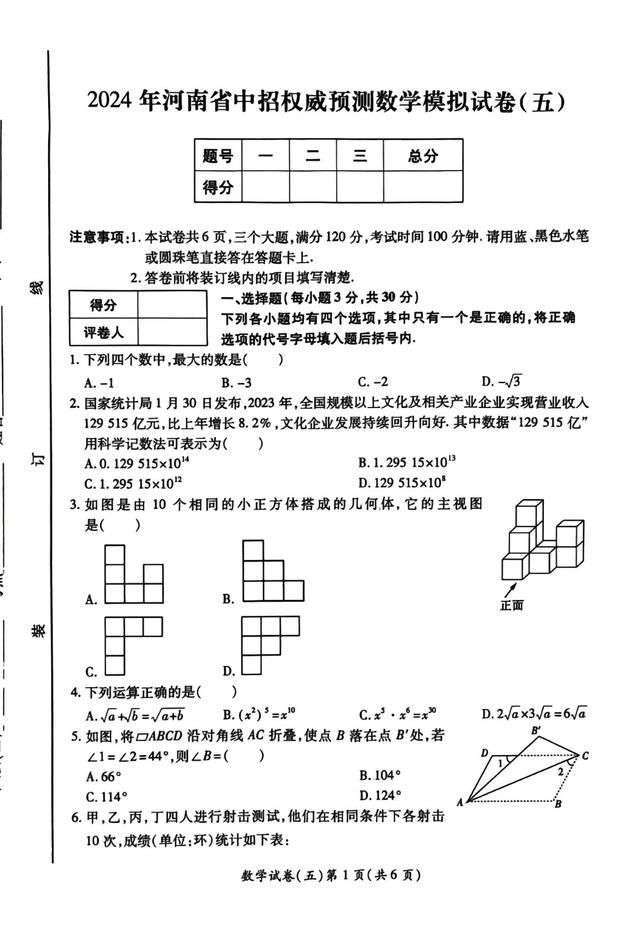馮軍鶴在課堂上(受訪者供圖)。
回顧兒時的記憶,總有一個瞬間激起了我們對書與閱讀的渴望。你是否還記得在學校拿到語文卷子的時候,先翻到閱讀材料讀故事的期待感呢?閱讀的快樂那麽純粹,在不能使用手機、電腦的校園時光顯得尤其珍貴。新京報書評周刊專訪了《X書店12節虛構的語文課》的作者馮軍鶴,聊了聊他眼中的語文教育和他在語文課中的文學實驗。
對于馮軍鶴來說,語文課既是文學課,也是社會課,是關于人的。而一個好的老師,是一個聆聽的人,是一個好奇的人,更是一個願意跟學生不斷交換對于知識的不理解和不確定的人。

采訪 | 王銘博

馮軍鶴,畢業于清華大學中文系。曾于雲南支教數年。以文學爲家,教書爲業。三聯《少年新知》自由撰稿人及課程講師。一席特邀演講嘉賓。
當語文老師後退,
讓學生成爲主角
新京報:你是怎麽想到要做《X書店12節虛構的語文課》這套書的?
馮軍鶴:這套書的雛形是我給《三聯少年刊》寫的稿子,主要講我在課堂上的教學內容、怎麽設計課程、爲什麽選某本書作爲閱讀素材等。經過《三聯少年刊》主編的推薦,出版社的編輯來聯系我,促成這套書的出版。

《X書店12節虛構的語文課》(全6冊),作者: 馮軍鶴,出品方: 100層童書館,出版社: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時間: 2024年4月。
新京報:在書中,你將主角設置爲一個在課堂上比較內向的女孩的形象,與你熟悉的老師視角完全拉開了距離。爲什麽這樣設計呢?
馮軍鶴:構思這套書的時候,我不想按老師的視角來撰寫、講述課程的設計理念。因爲我覺得這不符合我對于教學裏身份關系的認知——我覺得學生還是比老師更重要的。在課堂上,我很多時候在後退。
我其實做了很多准備,但在課堂上還是主要抛出一些問題,讓學生討論,進而提問。我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調動學生上,而不是作爲老師去做所有事情。所以我想以學生的視角來寫,但又不想寫成那種老師假裝成學生,把自己的觀點投射到某個學生身上的作品。
在這套書中,我把內容更虛構化,與真實稍微隔開一點距離,所以就有了現在的設定。有點類似于夏丏尊和葉聖陶寫的《文心》,也是從學生的角度寫,不過在我的書裏,主要不是知識,而是閱讀、審美和寫作這方面的內容。

《文心》,作者: 夏丏尊 葉聖陶,出品方: 酷威文化,出版社: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時間: 2022年5月。
新京報:主人公女孩沈青是純虛構的角色,還是在現實課堂中有原型的呢?
馮軍鶴:沈青的整個故事線,包括單親家庭、父女關系,還有人物性格都是完全虛構的。通過她的視角觀察到的班級裏的同學,有許多直接來源自我現實中的學生。
把沈青設計成內斂、敏感的性格,也是想探討一下文學和一個學生可能産生什麽樣的關系。雖然把課堂內容抽出去,剩下的關于沈青和父親、沈青和去世的媽媽之間的故事有點少,但我還是想要努力往這個方向做一些探討。
新京報:你在課堂上作爲老師“退一步”的選擇,是你在與學生的互動中慢慢摸索出來的嗎?
馮軍鶴:我覺得一方面和我自己的性格有關系,另一方面是慢慢形成的。最早去支教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麽當老師,也不知道怎麽管理課堂,基本上都是跟著當地老師去學習。一開始肯定還是想要把課堂的狀況控制得更好,更有秩序,流程也更通暢。
但是因爲我自己比較喜歡玩,所以經常會和學生在課間、體育課一起玩。玩久了就建立了一種新型的關系,他們不會再覺得你高高在上、很有距離感,在課堂上也慢慢能夠放松地跟你互動。我很享受這種狀態,松弛一點,甚至可以說更靈活一點,在上課的時候沒有那麽多一定要遵守的規則。所以我傾向于跟學生建立比較平等的關系。
警惕一種啓蒙的姿態
新京報:在設計自己的語文課的過程中,你受到過什麽教育理念的影響嗎?
馮軍鶴:在我支教完、來深圳之前的兩三年,我在理念上受到了郭初陽老師的影響。尤其是在如何打開文本、關聯更多文本等方面。在支教的時候,我教小學,很難把我閱讀的書跟這麽小的孩子的課堂關聯起來。但等我到了深圳教初中的時候,我可以找到更多我熟悉的文本,去設計成像郭初陽的課堂一樣豐富、開放的語文課堂。
但是另一方面,郭初陽將課堂做了嚴格的預設。就是說,通過提問題、給材料,還有回應學生的回答,最終希望學生能夠思考到某些內容。對這點,我並不是特別認同。
新京報:是因爲預設也意味著限制嗎?
馮軍鶴:這與傳統的教師權威有關。我大學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比較受後現代哲學的影響,所以我會比較警惕一種啓蒙的姿態。就是說我作爲一個有知識,甚至掌握真理的導師來啓蒙你。
因爲警惕這樣的姿態,所以當看到郭初陽老師的課的時候,一方面覺得很厲害,從中學習使用開放又豐富的文本去調動課堂的方法,另一方面自己也想探索怎麽往後退的問題。

《無知的教師》,作者: [法]雅克·朗西埃,譯者: 趙子龍,出版社: 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 2020年1月。
在深圳教書第一年結束的時候,我讀到了《無知的教師》,影響了我的教學實踐。這本書是法國哲學家朗西埃寫的。朗西埃認爲,當一個老師沒有任何知識權威可以給到學生的時候,學生反而會有更長久的發展。
比如當下的一些補習班,長遠來看,上名師補習班對學生本身會有損失,因爲補習班會比公立學校還要強調老師多麽厲害,多麽有魅力,多麽有知識,對于補習班老師的學曆崇拜也比公立學校更強。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更多是通過崇拜老師、吸收老師給的知識解析,來獲得自身的成長。
學生處在一種“我需要更厲害的角色來幫助我進行知識分解”的狀態,可能會漸漸失去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會失去對自己智慧的自信。這是《無知的教師》裏很關鍵的觀點——傳統的教師權威,會讓學生對自己的智慧失去信心,所以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智力解放五講”。
這本書既告訴我們老師應該警惕什麽,也告訴我們老師應該是什麽樣子——你得是個聆聽的人,是個好奇的人,是個願意跟學生不斷交換對于知識的不理解和不確定的人。
所以這本書最後很浪漫,朗西埃相信,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和老師是知性的共同體。
新京報:從你的實踐中,也能看到《無知的教師》對你的影響。
馮軍鶴:對。有時候我拿一個沒有備課的文本,去課堂裏跟學生們一起讀,讀完我們一起思考,互相提問。這個課堂我可能不知道最後會達成什麽目標,所謂的中心思想、傳統的教學目的,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但學生非常積極,我也坦誠地說自己剛讀這個文本,學生們就會更願意說自己想到了什麽。這個過程很調動學生,也很調動我自己。
新京報:當面對孩子的時候,給他們空間並盡可能保持平等,他們就會更願意投入到課堂和閱讀中並産生興趣。其實教育家們在這方面是有很多共識的。
馮軍鶴:對,我前一陣子還讀到萊辛的一個觀點——其實我們對于很多學科或者某方面的信息已經了解非常多了,但是很奇怪,我們好像從來不會利用這些信息去做一些改變。
文學閱讀與我們的現實
息息相關
新京報:在你的語文課上參與閱讀、討論和寫作的學生,有什麽變化嗎?
馮軍鶴:變化有許多方面。比如有的小孩可能一開始不喜歡語文、不喜歡讀書,但是我們周末的作業就是讀書,因爲下周會有專門的課堂討論這本書。有一個學生在我們班被認爲可能心理年齡只有二三年級,實際上已經初一了,整天像小孩一樣叽叽喳喳,甚至上課的時候會在地上爬。有一個周一,他沖過來跟我說:“老師我一口氣讀完了《活著》。”然後開始跟我說書中的情節、他和爸爸的討論。按照課堂作業量來說,我們要兩三周才讀完《活著》。

《活著》,作者: 余華,出品方: 新經典文化,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時間: 2017年6月。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這個孩子得到了閱讀的快樂,雖然這個快樂可能很短暫。我從來不想強化語文課,或者說文學本身,能夠給孩子帶來多少東西。這肯定是個體性的,不會是整體性的。
他之後可能不再讀書了,我走了之後他也不再被強迫讀書,但他曾有過讀一本書很快樂的體驗,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因爲你不能保證能一直陪著他們,但他們只要有記憶,未來拿起書的時候就會有期待,會想到曾經感受過的愉悅。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的成長和變化。
然後第二點就是,在我看來,語文課某種程度上既是文學課,也是社會課,是關于人的。有些主題你不給到學生,他就不知道、看不見,你給到他,他首先能看見這個東西,就是非常大的改變了。
比如在我的語文課中,有關于女性、性多元的課程。一方面,我會在課堂上結合閱讀的書,給學生看各個領域的數據,比如說在某個行業,女性的占比是多少,學生會很驚訝。
等到我們再一起去讀一些書的時候,我也從中獲得了成長,開始更有意識地去關注書裏面的女性角色,然後在課堂上一起分析女性角色,經常能從學生那裏聽到一些我自己沒有想到的視角和觀點。
坦白地說,我自己是個男性,我覺得一個男性無法成爲一個真正的女性主義者,因爲沒有作爲女性的體驗。在我看來,這種體驗本身是最關鍵的。所以有些女生在課上的觀點,我覺得我受教了,被重新打開了一扇窗子,看到了不同的風景。好幾個女生,甚至好幾個男生在課堂上都有這樣的變化,這是很重要的成長。
當他們在其他平台上和其他閱讀中,不斷自覺地去找到相關的內容,去思考,這就是長期的了。
新京報:你是怎樣想到要設計關于女性的課堂的呢?
馮軍鶴:可能因爲我自己從小性格就比較女性化一點(當然這與性取向無關,哈哈),我有點像我媽媽,很敏感,雖然不至于內向,長相也比較柔弱。小時候,農村的環境就是大家庭,鄰裏間關系非常緊密,他們看見我會說“誰家的女孩出來了”“像個女孩一樣”。雖然進入初中也叛逆過一段時間,但到了高中,班裏的男生會說你的動作怎麽這麽像女生之類的話,而我根本沒意識到。然後我的頭發也相對偏長,再加上長相有點像個女孩,所以這個聲音一直伴隨著我。
我會産生困惑,因爲在非常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你根本就沒有思考的空間,所以當他們叫你女孩的時候,你不知道這種不適就是社會本身給你的不適。所以等到我上大學之後,讀到女性主義文學作品,我才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原來我感受到的不適感是社會的偏見本身帶來的。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會有這樣一個意識。
在快節奏的當下,文學審美仍有價值
新京報:在你的語文課中,更深層的共鳴經常是在續寫文本的過程中産生的,這是爲什麽呢?
馮軍鶴:在我的課堂上,放在第一位的是文學審美。學生們能夠在文學的閱讀中感受到不同文學作品風格上的差異,還有在文字選擇上的區別,比如汪曾祺的句子是非常淡的風格,張愛玲的描寫是濃烈、細致、有象征隱喻的。
在講這些作家的時候,我一定會講到他們的風格和文字,然後講他們的審美和文學形式與內容的結合,從而讓學生們把文學作品當成藝術來評判,而不僅僅是故事內容。
當然文學的審美是通過非理性的感知來構建的。風格無法被說得非常清晰,所以我們必須借助感性的方式讓學生建立一種差異性的感受,包括通過寫作的方式。我們的寫作都直接建立在文本之上,而不是說今天布置一個寫周記的作業。比如我們讀了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就希望學生化身葛薇龍,來寫文章。這個方式讓你把故事當中沒有展開的枝桠,或者說人物可能會發生的事情繼續寫下去,然後在這個情況下,自然會代入到既有的文本風格當中去。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裏,學生們就不需要我去對文本風格做過多解釋,而是一種感性認同和創造性的寫作。

《第一爐香》,作者: 張愛玲,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出版時間: 1997年3月。
新京報:這樣的寫作方式在應試教育的考試題目中也會出現,你在課上的寫作安排與之有什麽不同呢?
馮軍鶴:我覺得最大的區別是強調整本書閱讀。因爲如果是一個單篇的文本,其實讀者很難沉浸進去。短篇小說遠遠沒有一個長篇小說給到的內容和風格基礎豐富。
孩子的想象力需要一個托住的東西,他們很難判斷和甄別什麽是值得寫的,什麽是有趣的且易于轉化成文學內容的。但是當你給他讀《活著》,然後在小說世界觀中的苦難的基礎上,沿著某個人物的線索寫,他能看到一個非常明確的文學世界,還有非常明確的人物關系。
新京報:在當下這個大家更看重故事梗概和解析的快節奏時代,文學的審美價值爲什麽對于我們十分重要呢?
馮軍鶴:我覺得我們對于理性的認知過分停留在非審美的層面,會覺得理性是用來討論、思辨,尤其是用來辨別對和錯的。但在我看來,沒有絕對的對和錯。我們設定的認知方式都是有前提的,很多理性的東西其實不那麽堅固。所以有時候可以用審美的方式判斷、認識世界。
回歸本質,比如我們對一個人好,是因爲我們會在這裏面感受到一種人性的美感。所以你看一個文學作品的時候,會非常關心它是以什麽樣的方式在表達,這種表達方式會與內容相對應,甚至是強化了內容。
當我們在現實中聽了一個錄音,分析錄音裏的人是什麽性格,有什麽看法,文學和這是不一樣的,對吧?所以你不回到文學審美的層面,文學之于文學的東西就丟了。
新京報:在文學閱讀中,嘗試去理解一個跟自己不太一樣的人,對學生的人格成長是不是很重要?
馮軍鶴:我在演講和書中都會強調,重要的不是判斷,是理解。在我們當下的教育中,確實缺少判斷的能力,但是我覺得,同樣缺少理解的能力。文學通過模糊邊界,讓孩子看到複雜性,還有現實豐富和多元的一面。
比如我跟小孩討論張愛玲,很多家長、老師會說:孩子怎麽能讀張愛玲的情情愛愛呢?張愛玲那麽悲涼,讀了她的作品好像會覺得生活特別令人抑郁。我覺得這中觀點也是沒有看到文學複雜的一面。張愛玲其實是非常多元地在討論愛情,既有熱情的一面,也有孤注一擲的一面,還有愛得死去活來的一面,但同時也讓你看到這種熱情的短暫性,看到裏面非常不可預期的人性的一面。
如果說小孩只看到了霸道總裁文裏的愛情,然後不論發生什麽,都一定要成功在一起,那麽他們對于愛情的想象就是這樣,這很可悲,對吧?
我們長大之後都會意識到一切是多麽不可預期,多麽複雜,所以我覺得借由整本書閱讀幫孩子建立一個看待事物的延遲判斷是很有必要的。他們不會急于給事物和人一個標簽,一個對和錯,一個愛與恨,而是願意等待,留出進一步了解的空間。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采訪:王銘博;編輯:王銘博;校對:劉軍。封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