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未來當我們回看2023年,會覺得這是相當特別的一年,因爲不同電影中的女性議題呈現,巧合地傳達著相似的訊息。
先是暑假時,全世界迎來票房破紀錄的《芭比》。在粉紅陳設與糖果色調的濾鏡底下,是一則女性自我追尋的英雄旅程。到了秋天,又有了另一部堪稱黑暗版《芭比》的作品,而它不只暗黑,也更加詭谲荒誕。那些《芭比》礙于尺度沒有提到的、或有意無意回避的,都在這部電影中成爲主角——那便是艾瑪·斯通封神的《可憐的東西》。

《可憐的東西》在威尼斯影展獲得最高榮譽金獅獎,不僅女主角艾瑪·斯通演技備受好評,更普遍被評爲導演歐格斯·蘭斯莫斯生涯最佳作,盡管他的前作已是相當高標准的《寵兒》和《龍蝦》。
可惜的是,沒能獲選奧斯卡最佳影片。

《可憐的東西》是改編自蘇格蘭作家阿拉斯代爾·格雷的同名小說,本片在衆多影展片中宛如一則形態奇詭的暗黑童話,將觀衆吸納入古怪科幻的想象空間。
隨著我們踏上“女科學怪人”的覺醒之旅,來一場對性別關系與道德規範的反思。
影片開始,我們望見一位穿著藍色禮服的女子從橋上一躍而下,這是一場死亡,更是另一場誕生。接著,畫面帶觀衆來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倫敦,女主貝拉盡管外表看似成人,她的行爲舉止卻如嬰兒般不受控制,成日仰賴科學家與女仆的悉心照料。話雖如此,與其稱之爲照料,其實更像是監控,科學家將貝拉囚于豪華宅第,避免她接觸房外的世界,如此滴水不漏的“保護”,直到爲科學家所聘的一位學生發現其中蹊跷,才有了打破的可能。

當年爲逃離丈夫而帶孕自殺的貝拉,死後詭異地成爲科學家的實驗品,她被植入自己腹中嬰兒的頭腦而複活,但她早已非原本那人。
被賦予第二生命的貝拉深深崇拜著科學家,科學家看著自身傑作日複一日的成長,也同樣欣喜。
兩人的連結最初奠基于不道德的科學實驗,卻發展出某種相互需求的奇異關系。

電影初期的貝拉,是個尚未被馴化的靈魂,她缺乏禮儀,不經思考,更沒有所謂羞恥。
那個沒有性器官的芭比,在這兒成爲性欲過剩的科學怪人,看似是不見容于社會的怪物。
不過我們將發現,貝拉的力量其實源自她的自由與無知。
經曆性覺醒的貝拉渴望性愛,無需歡愉,同時不以此爲恥,反倒不解于這個被道德規範的社會爲何作繭自縛。然而,她真正的覺醒,在于自己身世之謎的揭曉。當她知道自己的際遇,反叛與憤怒在心中萌芽,因而一心想踏往豪宅之外的世界,想做那些過往不被允許的事。于是她不顧一切,跟著初相識即墜入愛河的無良律師鄧肯踏上一段追求自由與性愛的旅程。
他們倆乘著船到訪裏斯本、亞曆山大港與巴黎等地,離開倫敦,離開宅邸,宛如踏上一段走出伊甸園的壯旅。

《可憐的東西》表面看來怪異又極端,底子裏其實是部奧德賽式的成長啓蒙電影。
貝拉踏出豪宅後的日子,才真正見到世上的真實樣貌,她感受自由與解放,也同時因看見受困苦難的奴隸而傷悲,助人之心油然而生,這是使她從:科學怪人漸漸成爲“女人”的過程。
而當貝拉意識到性工作一職能帶來財富,她毫無猶豫地爭取成爲紅牌,只爲自力更生,不再仰賴男人——這才終究讓她成爲一個自由人。

她的天真曾被人利用,如今反倒成爲解放自己的力量,甚至驅使她想成爲一位醫師。
貝拉的存在如冒險家、夢想家與科學家,卻沒有片中男性角色由上而下病態的控制欲,最終從“被創造”的客體,成爲了“再創造”的主體。
奇幻同時真實,現代卻又古典,加上一點點邪典元素,融合在一起卻毫無違和,電影用魚眼鏡頭搭配古怪有趣的對白,交織成一段雜糅哲學、宗教與性別的討論。與《芭比》相同,《可憐的東西》主旨不在于性別對立,而是它拆解父權主義,講述當女性離開父權體制規範後,能夠成爲何種樣貌?片中多場大尺度的場面預期可能冒犯某些觀衆,但也像是激起對性解放的有機诘問,使作品不欲鄉願討好,又不致憤世嫉俗。

貝拉本是“可憐的東西”,如離開宮殿走入黑森林的公主,這段自我覺醒漫漫長路,使貝拉從科學怪人變回女人,再從女人的束縛中松綁,成爲掌控自己命運的人。
至于誰才是最後真正“可憐的東西”?
我想這部怪誕電影的結尾,是不會令觀衆失望的。

再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芭比》。
兩部電影均有提及父權社會如何壓抑女性,《可憐的東西》講貝拉的成長源自情欲覺醒,芭比卻連愛情器官都未有。由是,同樣說女性成長,不少人將兩部電影相提並論,甚至有人說《可憐的東西》比《芭比》更加“女權”,畢竟前者涵蓋了身體與思想上的自主,更有外國網友笑說《可憐的東西》大概就是芭比去看婦科醫生的後續。

在我看來,《可憐的東西》其實志不在此。
不過就是經曆了《芭比》一整個夏天的粉紅風暴後,被煞有介事的扣上“女權”帽子。導演的動機其實更加開放,更加純粹。摒棄所有記憶,重新想像一個最古老的故事:抛開道德枷鎖、社會規範,我們會如禽獸一樣活著,還是可以毫無束縛地建構一個更合時宜的伊甸園?

當科學怪人成了“上帝”,這次他不造亞當,轉爲女屍植入腹中嬰兒腦袋,先創造“夏娃”,她有一個代表美麗的名字——貝拉。電影從來沒有道破嬰兒的性別,貝拉究竟是男是女?我們無從得知,答案或許都不重要。我們與生俱來的身體,將我們置入性別角色的無形框架之中,其實腦袋又有否性別之分?
貝拉是一個自由的靈魂,她借由一個女性的身體去接觸世界。然而,她的世界僅限于上帝爲她建構的伊甸園,這時候的她還未完全感受到自己身爲女性的角色,直至上帝帶來“亞當”要跟她成婚,引來了滿身誘惑的“蛇”——額頭寫著渣男二字的律師鄧肯。

初嘗禁果以後,她突然意識到自己與身體的關系,提出要跟鄧肯逃走,開頭固然是縱欲橫流,世界由黑白變成彩色。
其後因爲鄧肯的占有欲被綁上賊船,巧遇上古靈精怪的老奶奶與年輕人哈利,一起看書、思辨,我思故我在。明明是被困在船上,貝拉卻覺得思想如大海一樣,無邊無垠。此時,貝拉已走出雙腿之間原始的歡愉,轉而追求雙耳之間知識與精神上的滿足。
這段旅程也讓貝拉首次目睹人世間的千瘡百孔,千金散盡,墮落凡間。流落煙花之地,在形形色色岩岩巉巉的逢場作戲之中,見盡花都蒼穹下,原來衆生皆可憐。

繞了一圈,風塵仆仆,恍如隔世。
貝拉由失樂園走回伊甸園,上帝早已奄奄一息。上帝離開之前,向貝拉告解了她的身世。爲何母親要選擇了結自己(和自己)的生命?要得到答案,她決定正面面對上輩子的情人——父親。這位父親一言不合就開槍的性格,是父權的代表。爲了讓失而複得的維多莉亞能安分守己的留在身邊,他悄悄地安排了一場去勢手術。只是,他不知道,眼前的維多莉亞,已經重生成爲貝拉。蛻變成新時代獨立女性的她直搗問題症結所在,有樣學樣的爲這個十惡不赦的父親換上一顆羊腦。

比起以女性主義談論《可憐的東西》,我想它更是一部人類追求內在覺醒的電影。乃因觀衆至始至終都無從得知維多利亞腹中的嬰兒真實性別,我們只知道她以女性的身體開啓全新的人生,以“性”打開對世界的探索。
貝拉就像童話故事裏的長發公主,只能透過微小的視窗窺探高塔外的世界,這當然無法滿足她對世事的好奇。貝拉摔碎碗盤、尖叫怒吼著控訴“上帝”古德溫的束縛。然而總是強調科學理性的古德溫,一方面象征父權社會底下男性對女性的掌控,另一方面卻又對貝拉充滿愛與呵護。
電影中的矛盾與沖突將世俗的理論煽在觀衆的腦袋上。

撇除欺騙與謊言,我很想念你!
但與其用“父權社會”概論古德溫,我更認爲他的控制來自多個面向。最終,高塔裏的長發公主掙脫感性科學家的束縛,跟著風流律師闖蕩世界,落入凡間,踏上真實世界的旅途。
說到貝拉爲何會對世界産生更多的興趣,我想其中伴隨“性”的啓蒙。
不論當時貝拉的實際年齡,因爲無意間體驗性的愉悅,開始對性愛有了想像。
她隨手拿起餐桌上的桃子(蘋果)、小黃瓜童言童語的跟邁斯分享她新奇的發現,如同貝拉的角色設定,年幼的心靈致使她毫不避諱的談論任何事情,總是一針見血的點出社會上不合理的僞裝,難吃的食物就吐出來、遇到難相處的人也不諱言。

電影中的“性”有如亞當與夏娃的禁果,但在貝拉與生俱來無拘無束、向往自由的個體上,性變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由性激發促使他與律師鄧肯旅行,體驗無數次歡愉。卻在知道鄧肯也有極限後,則轉身向外尋找更多性伴侶。同時也和鄧肯分享她和別人的愛愛過程,連花花公子也感到瘋狂。
電影中,最令我印象橋段莫過于郵輪之行。這使得貝拉航向更無邊際的遠方,抵達人生體驗的彼端。當鄧肯沉迷于酗酒、賭博之際,貝拉卻開始認識新朋友,一位老婦人和她的隨從,成爲貝拉接觸哲學的契機,更帶她看見世界殘酷的面貌。


這個世界有光彩華麗的富人生活,也存在貧窮、饑餓、打劫的煉獄。富人們就像活在城堡的中心,他們只能在高處俯視如蝼蟻般,著以破布的貧民,但通往貧民世間的階梯卻僅剩斷垣殘壁,將世界的兩端完全阻隔。隨從告訴貝拉倘若今日他們成爲窮人,也同樣爲生存而搶劫與掠奪。這使我想起《寄生蟲》裏的經典台詞——有錢所以善良。
貝拉爲眼前的景象嚎啕大哭,爲她無法改變世道而悲傷,過去只活在古德溫的保護傘之下,不知世界的階級與生活樣貌就像一個正方體,有著他不曾看過的另一面。貝拉試圖以她純真的處事態度,將鄧肯賭博贏來的金錢請船上的水手的贈予貧民,卻不知早已被私吞。

“悲傷和同情”是推進貝拉更“具人化”的重要情感元件,同時是電影的高潮。
下船後貝拉不屑于鄧肯毫無處事能力,起初爲了財力來源踏入妓女院,卻遇見足以改變她生命的老鸨。
與其說爲了金錢,貝拉不在乎世俗如何看待妓女這份職業,當鄧肯瞧不起她時,她認爲自己僅將身體作爲生産工具。這份工作同樣以勞力付出獲取報酬,與其他任何職業無不同之處。她甚至在這段日子中透過和不同男人愛愛,就連被陌生男子粗暴的對待,也是她認識世界的養分。而未婚夫邁斯也有著前衛的開明,告訴貝拉“這是你的身體,你有權自由使用它”。

鄧肯表面爲貝拉當妓女負氣而走,實際上已成爲黏人的恐怖情人,隱喻他後續淪爲近乎癫狂、悲慘、可笑又窩囊的男性。
當貝拉准備結束遊曆世界的生活時,故事又帶著觀衆急轉彎。貝拉的母親維多利亞·布萊辛的丈夫將軍橫空出世,攔截貝拉和邁斯的婚禮。呼應貝拉曾說她周遭遇見的男性都想控制她。
當貝拉正式走進母親的過去,房內彌漫窒息與壓抑的微粒、莊園裏的廊道就像通往刑場般死寂。父親以槍枝要求貝拉服從,但貝拉即便感到恐懼卻毫無退縮。而後她利用古德溫的筆記將羊腦移植給他,傳承古德溫的外科技術。

畫面切換到祥和且平靜的午後,一群人悠閑的品味下午茶伴隨著綿羊的鳴吠聲。
本段幽默的敘事手法,帶著強烈的“馴服”意味,呈現過去將軍總以自己的威嚴和權利使他人順從,冷血且毫無人性,對比成爲羊人之後由貝拉翻轉強權的控制 ,極具趣味和沖突。
整部電影充斥著怪異、荒誕、奇幻,角色們穿著複古,卻像是活在不曾存在的時空中,令人仿佛置身異世界。就是這般怪誕與沖突形塑電影的調性。

最終貝拉如同周遊列國後的壯士,在追尋人類本質的道路上破關斬將,品嘗過可口的美食、欣賞過旖旎風光、遇見過人性的愚昧與貪婪,那些世間五味雜陳的情感與她所閱讀的書本收攏爲這趟旅程的見識,使她從嬰兒蛻變爲成熟兼具理性與感性的個體。
這段第二次的人生,即便過程不如她想像中的美好,卻在看見世間苦惡後,她了解世界,痛,但,活著真好。

若你看過《芭比》且對于它沒有入圍奧斯卡應有的獎項含恨,那你更應該觀賞《可憐的東西》。不論兩部電影是否真的爲女性主義作品,就人類覺醒的命題上,《芭比》因靠攏大衆市場,以台詞口白傳達理念,演變爲“教育觀衆”或宣傳式口號,《可憐的東西》則用故事推動劇情,引領觀衆看出主角的成長曲線。
尤其艾瑪·斯通的表演,更將其從嬰兒到成人視角的性格、肢體、神情、思想诠釋得區隔分明。140分鍾的電影,我們就像跟著貝拉遊玩世界一樣,在看似獵奇的畫面裏,每一個角落都堆滿了故事,每一句台詞都值得詳盡分析與理解。這樣一部豐盛的電影,值得每個人去細細品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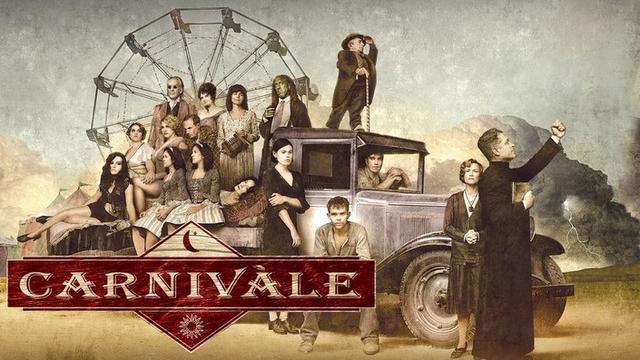


這片子和女權其實一毛錢關系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