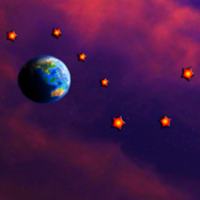文丨丁麗萍

我家後院裏有兩棵梨樹,每年,當人間最美四月天過後,梨花去,百果留,我就開始爲梨樹疏果。疏完果,還要爲留下的幼果掐去頂上的花萼。給幼梨去花萼,我是聽我二舅說的,他說那叫掐花。我二舅生前是栽培管理梨樹的行家,他與果樹打了一輩子交道。
我有兩個舅舅,一個姨,我媽是他們四兄妹中最小的。我二舅是個二等殘廢榮譽軍人,解放戰爭時期,他在孟良崮戰役中受了傷。從部隊回來後,他再沒有離開過他的村子。二舅的村莊叫張家寨子,坐落在流經膠東半島的大沽河邊上,那裏盛産萊陽梨。萊陽梨,以它肉甜汁多而馳名中外。據二舅說,萊陽梨個大,好吃,除了産地的地理環境和土質特殊外,在管理上,掐花這環節很關鍵。掐花也叫摘萼,顧名思義就是在梨還小時,把它頭頂上的那個花萼弄掉。我們在市場上買的萊陽梨,頭頂上都有個褐色的疤,那就是梨被掐花自愈後留下的。
我家的兩棵梨樹不是萊陽梨,但我每年還要給幼梨掐花,聽二舅說,掐花的另一個好處是能除掉藏在花萼裏的害蟲蟲卵。自從我二舅于2017年春去世後,每年給梨掐花,對我來說又多了一層意義,我把它當成了懷念二舅的一種儀式。

張家寨子是個大村,村子與大沽河之間隔著一片方圓近千畝的沙地。那沙地自河心一直延續到村邊,在靠近村後處形成了一道沙嶺。那道沙嶺東西跨著整個村子。在沒有房屋的村東和村西兩頭,沙嶺表面平坦,大約有兩米高,上面疏密不均地長著一種生命很頑強的野草。在有房屋的村後,沙嶺則變成了高低不等的沙山。那些沙山,大的約有兩個農房疊起來那麽高,矮的也有一個高。沙山的沙子又細又軟,淡黃的顔色從遠處看著像一個個的谷子堆,當地人稱它們“沙谷堆”。
沙谷堆是小孩子們玩耍的天堂。二舅家在村後邊,與沙谷堆只隔著幾排房子,我小時候特別盼望著去二舅家。每次去了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的表哥表姐,加上周圍別人家的一些小朋友,去爬沙谷堆。到了沙谷堆下,不管天冷還是天熱,我們把鞋子一脫,打著赤腳,就開始手腳並用往上爬。先到頂的占高處,等大家都爬上去後,就一字排開來,橫躺下身子,齊數一二三,閉上眼睛就往下開滾。那個年代生活垃圾極少,沙谷堆很幹淨,上面除了偶爾有幾根幹草或幾片樹葉,沒有什麽其它雜東西。我們一幫孩子就那樣反複地爬上去滾下來,滾得身上,頭發裏甚至鼻子眼睛裏都是沙,但我們不在乎。每次都要直滾得疲憊不堪,爬不上去了才肯罷休。
在土地歸集體所有的年代裏,我二舅是村裏的果樹技術員。那時我曾去過一次他們的果樹園。那園林占地面積很大,裏面的果樹很多。那是在我大約十一或是十二歲的一個夏末,我媽讓我去給二舅家送點兒什麽東西,碰到他家裏沒人,我就去了果園找二舅。在果園門口有人認識我,當聽我說要進去找我二舅,他說果園那麽大,生人進去找人很難,說不定會迷路。他讓我在園門口等著,他進去找二舅來領我。

二舅看到我很高興,老遠就喊我的乳名。我告訴二舅,我去他家,可家裏沒人,我就過來找他了。二舅聽著我說話,拿過我手裏的東西,就領著我往果園裏走。我跟著二舅穿過一行行挂滿了果子的果樹,來到了一個小草屋前,那是二舅他們平時用來放置勞動工具,下雨天進去避雨的地方。二舅讓我別亂走,他說要拿梨給我吃。那個年代我們所受到的教育是要以集體爲家,愛護集體財産,沾公家的便宜可恥。我違心地跟二舅說我不想吃梨。
二舅沒有聽我的違心謊話,他走到小草屋的東屋山頭,用手撥開一堆沙子,從裏面掏出一些黃澄澄的梨拿到我眼前。二舅邊用粗糙的大手摩挲掉沾在果子表面的沙粒,邊對我說,那些梨都不是“正宗果子”,它們是些在成長途中,因故落下來的。因覺得可惜,每當看到有看上去還會有“前途”的落梨,他們在果園裏幹活的人會習慣地把它撿回來埋到那個沙堆裏。一段時間後,“有前途的果子”就能被捂熟糖化,成了脆脆甜甜可口的果子。
二舅說著話,從衣兜裏掏出把小刀開始爲我削梨吃。那時我還小,不懂矜持,拿到二舅給我削好了的梨,就狼吞虎咽地幾口就能吃完一個。二舅蹲坐在地上削梨,正好也能休息一下。他每削完一個,就擡眼慈祥地看看我是否吃完了上一個。寫到這,我好像聽見我二舅慈愛的聲音在喚我的乳名,提醒我慢慢吃,別噎著。我哭了。我的二舅生前很愛我,我也很親他。

記得二舅給我吃的梨有好幾種。有種形狀圓圓的,他說是夏梨,頂部有個大疤痕的是萊陽梨,顔色橙黃鮮豔的是香水梨,還有一種個子很大,我記不清他說那是什麽梨了。那些梨每一個聞起來都是香香的,吃起來脆甜脆甜的,不過真比較起來,當然是萊陽梨最好吃了。
我國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後,原屬村集體的果樹被分樹到家了。自那時起,二舅沒有果樹技術員頭銜了,但他對村裏每家每戶的果樹仍然很上心,只要是有關果樹的事情,有人需要幫助,不管是誰他都是有求必應。
聽我媽說,二舅癡迷果樹是隨了他們的父親了。她說,當年農村實行高級社,他們家入社的土地上有上千棵水果樹,其中很多都正處在盛果期。我母親說,那些果樹都是他們的父親-我的姥爺栽培的。她記的,那些年,每當下雨天,我姥爺就會推著個獨輪小推車,從村後的沙灘上裝了沙子,一車一車地送到村裏每家每戶的街門口。她聽人說,每到一戶人家門前,不管人家是否聽得見,他都要喊一聲,“給恁送沙墊路來了。”
那個年代,姥爺移沙是爲了栽樹。樹苗是他自己培育的,下雨天栽樹不需要澆水,他可以把移沙,挖坑,栽樹三個步驟一次性完成。如今,我姥爺栽下的果樹都已經沒有了,只有村西邊一棵白果樹還在。那樹主幹又高又壯,樹身挺拔,枝繁葉茂,它那巨大的樹冠在周圍幾裏外都能看得見。聽我表姐說,此樹在前些年,已被政府歸爲受保護不可隨便砍伐之列。

我二舅的一生其實是挺艱辛的,但他是個很堅強的人。他五歲時,我姥姥去世了,十年後我姥爺也走了。在二舅的後半生裏,他五十幾歲時妻子病故,七十歲那年唯一的兒子也因病而去。二舅一次次經曆失去最親的人的不幸,可他從沒怨天尤人對生活失去信心。二舅性情平和,善良,樸實。待人友善,真誠,沒有偏見,他骨子裏擁有一種甯衆人負我,我不負衆人的天性。
自我長大,去外地上學,工作後,就再沒有時間常去看我二舅,特別是出國後,更是少有機會。後來,我只是從我的弟弟和妹妹那裏聽說,最近這些年,甚至直到二舅去世前的那個秋天,他們在春、夏、秋季節去看他,直接到他與他孫子家的果樹林裏就能見到他。每次二舅看到他們,也是會喊他們的乳名,也要弄果子給他們吃。不同的是,這後來二舅給他們吃的都是又大又甜,現從樹上揀摘的好果子。
昨夜我做夢了,夢中,我看見在天上的二舅正與各路衆仙一起在忙著准備王母娘娘的百果宴。我還聽到二舅和我說話了,他說他現在還是很忙,因王母娘娘把蟠桃會改成了百果宴,萊陽梨被選爲其中的仙果之一,他因有豐富的栽培管理梨樹的經驗,被選去負責管理天庭裏新設的萊陽梨園了。奇怪的是,我在夢中,沒有聽見二舅喊我的乳名。
二舅一生癡迷園林樹木,他生前就像只工蜂,一年到頭在林中不停地忙活。他在世時,我曾聽他說過,能以果園爲家,有果樹陪伴是他最喜歡過的生活。我相信,在天上,二舅如真的是位果仙,他一定會非常的幸福快樂。

完成于2024年5月3日,星期五

☆ 作者簡介:丁麗萍,女,筆名萍水相逢。祖籍山東煙台,現住美國紐約。本人喜歡文學,熱愛讀書,愛好寫作,寫有多篇散文、故事及短篇小說。作品散見于《人民日報(海外版)副刊》,及多家報刊、雜志和網絡平台。
原創文章,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