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出生于晚清一個耕讀世家。他六歲入塾,八歲能讀《四書》,誦五經。二十一歲考取秀才,二十三歲中鄉試舉人。二十七歲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入選翰林院庶吉士。
作爲一個科舉過來人,曾國藩不僅在心理、精神層面給予子侄以鼓勵和支持,還親自就學習備考等方面與子侄進行切磋。生在科舉時代,參加科考則成了讀書士子的安身立命途徑。兒子曾紀澤鄉試屢遭挫折後無意科舉,曾國藩坦然接受這一事實,尊重紀澤的選擇,並對他抗心希古的志向頗爲激賞。但曾氏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對次子紀鴻的要求。
當聽說紀鴻在縣試中考了第一名,曾國藩非常高興,並稱許紀鴻的文章“清潤大方”。當紀鴻問父親是否應去科考時,曾國藩說:“爾既作秀才,凡歲考、科考,均應前往入場。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職業也。”曾氏將應試科舉作爲讀書士子的份內之務,這表明了他對科舉的態度。在家書、家訓中,曾國藩對紀澤、紀鴻等後輩說到了讀哪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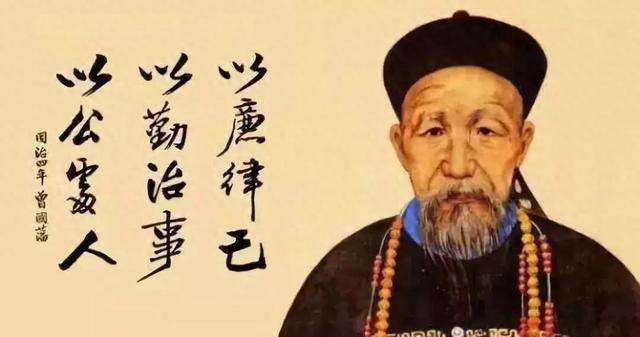
經籍類是科舉士子首要必讀之書。鹹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寫信給曾紀澤,敘及士子應讀之書。紀澤向父親彙報自己已經看完了“五經”。曾氏認爲,除“五經”應熟記外,“十三經”中其他六經,即《周禮》《儀禮》《爾雅》《孝經》《公羊》《谷梁》諸書,均應請塾師口授一遍,以覽知其大概。
史籍類中,曾國藩認爲《史記》《漢書》均應熟讀。他還不止一次地說到自己對這兩部曆史典籍的嗜愛。對讀史的次序,他也加以指點。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他信谕紀澤、紀鴻:“爾擬于《明史》看畢,重看《通鑒》,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鑒論》。爾或間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
諸子籍中,曾氏比較推重《莊子》《孫武子》。曾氏曾說他嗜《莊》、韓文、《史》《漢》成癖,恨不能一一诂釋箋疏,窮力討治。
集部籍中,曾氏薦讀《文選》和韓文。之所以喜愛韓文,乃出于愛其雄渾剛健的氣勢。
除此外,曾氏還建議二子應閱讀《通典》、《說文解字》《方輿紀要》,姚鼐所輯《古文辭類纂》和他本人所編輯的《十八家詩鈔》。
在曾氏推薦閱讀的這些書中,經、史、子、集以及《說文》等訓诂之學,均有涉獵。曾氏與紀澤交流讀書經驗,認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並進一步對漢學、宋學之差異進行了解析:“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提醒紀澤讀書時不妨以理性待之,“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取其合理處,棄其虛妄不實處。
清代自乾嘉以來漢學日臻鼎盛,但曾國藩卻無意于右袒任何一方,而是主張調和漢、宋。他同時告訴紀澤,治經時,無論看注疏,還是看宋傳,總宜虛心求之。認爲惬于心意者,則以朱筆標出;有疑問時,則將其收錄于另一冊本,將自己的疑義附記于此,哪怕僅有片言只語,倘隨著讀書能力的提高,知識積累愈加豐富,所疑之惑便可漸漸解之。清代著名考據家高郵王念孫父子即通過此種劄記的方法卓然成爲大家,曾氏勉勵紀澤也應學習王念孫父子的樸學精神。接著,他又推薦紀澤閱讀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王念孫的《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亦須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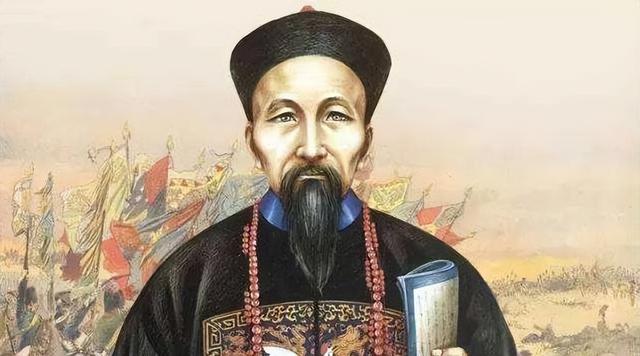
曾氏曾就“看”與“讀”之區別加以述之:“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他還將之比方爲富家之慎守與獲利:看書就像在外貿易,能獲得三倍;讀書則如在家慎守,不會輕易花費。若以兵家戰爭作比,看書則像攻城略地,開疆拓土;讀書如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他還認爲讀書須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並進行了一系列的比方,說“涵”如春雨滋潤萬物,渠水灌溉稻田;“泳”則如魚之遊水,人之濯足。紀澤之所以不能深入體察經義學問之內涵,原因即在于缺乏“涵泳”、“體察”的工夫。切實成爲讀書君子,乃曾國藩對後輩子孫的期待。其殷殷之情,溢于字裏行間。
如果對清代科舉准備用書加以對照,可知曾國藩給子侄所薦讀之書,乃是科舉考試獲隽的必備之書。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曾撰《科舉考試的回憶》一文,對自己的科途加以回顧。商氏自言六歲開蒙,讀《三字經》《千字文》。這是幼童識字之基礎。能背誦及認識大部分字後,開始讀《四書》。《四書》須依朱熹之注,讀正文時,亦應讀朱注。塾師將新的內容口授一遍,學生即自己記誦,同時溫習舊書。因“四書”是考試基礎,三篇八股文題目的出處所在,故全部內容須從頭至尾背誦至滾瓜爛熟方止。
然後是讀“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仍需全背正文,但無須背注。這是爲科舉考試四篇經文而備。此外還須讀《孝經》《公羊傳》《谷梁傳》《周禮》《爾雅》,以及五、七言唐宋小詩、《聲律啓蒙》等,學作對句,學調平仄。還須讀十七史蒙本,每每四字一句,句句有史實典故,這既有助于少年兒童了解曆史,又可增加對典故的認識,可謂一舉兩得。十二歲後,始學作八股文、詩、賦、策論等。此時不但要讀八股文、古文、律賦、文選之類,並且要讀史書如《通鑒》、“四史”,子書如《莊》《老》《韓非》等各種書籍,俾腹中充實,以備作文之驅遣。

雖曾國藩不希望子孫後輩讀死書,成爲古板的學究或狹隘的文人,但紀澤、紀鴻獲隽秀才後,曾氏對二子讀書方面的指導,亦大有意于科舉,則毋庸置疑。爲培養二子的“時務經濟”之才,曾氏要求二子須熟讀《文獻通考》,並會查閱會典,熟習文物制度,典章法則。曾國藩曾批點過《文獻通考》中的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籴、土貢、國用、刑制、輿地等門。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寫信給紀澤、紀鴻,說自己在核改水師章程,讓紀澤翻閱《會典》,查出千總、把總可各領多少養廉銀。曾氏提示紀澤現行經制可查閱《會典》,因革之制則可查《事例》;對于提督之官何時改爲武職,曾氏建議紀澤或可查《會典》,或可詢之淩曉岚、張肅山等。這些問題可使紀澤對清代養廉制度的因革和文武官的沿革等職官文化體制,較一般人有更加透徹深入的了解。
曾氏曾將自己不懂天文、算學作爲平生之一恥,希望紀澤、紀鴻能夠有所補救。家書中談及推步算學縱難通曉,但認識恒星五緯並非難事。十七史中各個時期的《天文志》和《五禮通考》中所輯錄的《觀象授時》,皆可做爲學習資料。“每夜認明恒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爲使策論寫得充實有光輝,曾氏曾要求紀鴻、瑞侄“可將《文獻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限五十日讀畢。”
曾國藩要求紀澤兄弟不僅要通訓诂,還要善辭章,天文地理,典例文物,無不涉獵,這是典型的“通才”式君子教育。曾氏本人一生信奉儒學,他希望家中子弟亦能博學多識,無囿一方,成爲于國于家大有用的通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