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蘇轼,是名副其實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其在詩、詞、書、畫、文,甚至在美食上,都頗有一番造詣。
蘇轼這一生,雖仕途坎坷,際遇無常,領略了世間種種聚合別離,但同時,這些人生閱曆也成就了一個縱橫恣肆、別具一格的大文豪。

他人緣極佳,交友甚廣,朋友圈遍布大江南北,據統計,蘇轼一生所交的朋友,有千人之多。比如在杭州做官的第二年,他給好友劉景文寫下“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以勉勵這位因年老窮困而長此頹唐的友人。
還有一次,蘇轼和北歸的王鞏會宴,途中蘇轼見到了王鞏的妾室宇文柔奴。
柔奴天生麗質,能歌善舞,嬌豔可人,更難得的是,當年王鞏被貶,柔奴毅然隨行到偏遠的嶺南。在佳人的陪伴下,王鞏得以走出那段灰暗的歲月,而且始終保持著坦蕩的心胸,稱“安患難不戚于懷”。
席上,柔奴爲蘇轼勸酒,蘇轼便問她:嶺南的風土應該不太好吧?柔奴則答道: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此話一出,令蘇轼不禁大爲感動,感動這佳人伴君子的天賜之緣。隨後,蘇轼就用柔奴的這一句話寫成一首詞,感動了世人千百年。

蘇轼身爲一代大文豪,敬仰和賞識他的名人雅士不在少數,所以他的身邊從不缺朋友。不過,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交友之道。
蘇轼交友,一不重門第,二不論貴賤,只看品性,只求真心,就像蘇轼本人所說的那樣:“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也正因此,蘇轼的朋友圈中各路人都有。

蘇轼和他的朋友們
有以文會友的米芾(大書法家)、文同(畫家);有以真心會友的劉貢父(史學家);有以品性會友的李廌(窮書生),還有那個半夜亦未寢的張懷民(北宋官員)等等。
而我們今天所說的王鞏,就是蘇轼的一個名氣不上不下、官職不高不低的好友。
王鞏生于1048年,和宋神宗同一年出生,是宋初名相王旦之孫。王鞏年輕的時候,苦學力文,窺涉百家,志氣甚堅,有畫才,擅長作詩,又因受到祖上恩蔭,王鞏得以步入仕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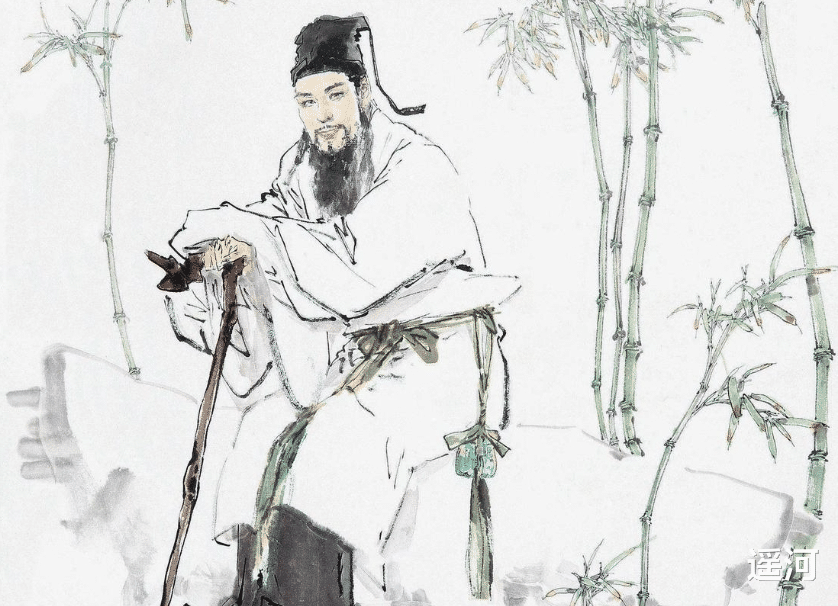
在宋神宗初年,王鞏曾受到王安石的賞識,並屢次想用他,但都被威武不的王鞏給拒絕了,後又受到大臣馮京、吳充等人的器重,擔任過揚州通判、右朝奉郎、和工部尚書等文官。
想當年,蘇轼在徐州任職時,王鞏前去拜訪,幾人一同登魋山、遊泗水,吹笛飲酒,乘月吟詩,好不快哉。在黃樓之上,兩人相視而笑,王鞏還對他說:“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說自從李太白死後,世間再沒有這種樂趣三百多年了。
就這樣,兩位身在仕途的同僚漸漸成了無話不說的密友。

只可惜,在這之後不久,蘇轼和王鞏就迎來了他們人生中最大的轉折,也就是“烏台詩案”。
北宋中期,以王安石爲首“變法派”和司馬光爲首的“保守派”拉開了黨爭的序幕。在變法之爭中,由于蘇轼和變法派的見解不合,屢受排擠,所以他只好離京外任,到杭州任通判,後來又做了密州、徐州和湖州的知州。

在這段時期,蘇轼看到了變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弊端,于是他就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原本只是例行公事,也公開地、准確地表達了自己不和新派合作的態度,說明新法中的一些弊端。
但蘇轼是一個詩人,筆下往往帶有個人感情,即使是在官樣文章中,也會有意無意地加上一些個人色彩。結果,這些話就被新派給利用了,認爲蘇轼是在攻擊朝廷,反對新法。
1079年7月,才在湖州上任三個月的蘇轼被吏卒逮捕,押往京師,最後被貶爲黃州團練副使,而受此案牽連者多達二十余人。

在這些案犯中,當屬“與蘇轼往還”的王鞏被貶得最遠、責罰最重,貶到了嶺南最荒僻的賓州。
那個時候,王鞏的妻妾、下人,基本都走光了,唯獨一個歌女願意和王鞏一同到賓州赴任,這個歌女就是宇文柔奴(娘)。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宇文柔奴原本是一個天生麗質的大家閨秀,只可惜在柔奴幼年時,她的禦醫父親就被人冤枉入獄,最後在獄中身亡。她的母親因忍受不了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急火攻心病倒在床,不久也撒手人寰了。

然而,還沒等宇文柔奴走出雙親離世的悲痛,她就被叔叔賣到了京城的行院,成了一個賣藝不賣身的藝伎。
這柔娘天資聰穎,晶瑩俊秀,在行院中頗受歡迎,也因此受到了精心培養。在十幾歲的年紀,其聲名就傳遍了京城,亭亭玉立如花一般。

後來的一天,行院一個姐妹生了病,柔娘陪著她到一個太醫那治病。巧合的是,眼前這個太醫,正是柔娘父親的摯友陳太醫。
實際上,在柔娘被賣到行院後,陳太醫就曾多方尋找柔娘的下落,但一直未果,何曾想柔娘就在京城當中,更沒想到兩人會以這樣的方式遇見。事後,陳太醫便托人找關系,打點了一些銀兩將柔娘贖了出來。
在跟隨陳太醫的這段日子,柔娘讀了很多醫書,看過了父親生前留下的一些藥方,再加上陳太醫的親身指導,柔娘的醫術漸長,得到了街坊四鄰的一衆好評。

再後來,柔娘就遇到了王鞏。那個時候的王鞏,家資頗豐,善詩作畫,有很多傳世之作,而且在仕途上又正值春風得意、爵重官高時,俨然一個人見人愛的風流才子,只可惜王鞏已有妻室。
奈何這柔娘也是真的動了情,甯願當王鞏家中的歌女,都要陪伴王鞏左右。然而,也就是這樣一位歌女,卻心甘情願陪王鞏走荒蕪之地,一同度過悲涼幾年。
試問嶺南應不,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在貶谪的那幾年,柔娘用無微不至的關懷掃去了王鞏心中的陰霾,她不但每天悉心照顧王鞏,還會親自上山采藥,爲當地百姓治療疾病。後來,柔娘和王鞏回到京師,這件事還被傳爲佳話。

烏台詩案後,身在黃州得蘇轼也對王鞏受牽連一事很是內疚,感覺自己愧對王鞏,說:“茲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爲此,蘇轼時常去信噓寒問暖,或是探討詩畫方面的內容,或是自責,或是聊些養生之法和所見所聞,有《次韻和王鞏六首》、《王定國詩集敘》等。
而柔娘也很熟悉蘇東坡,經常與他交流醫療健康的話題,蘇東坡在養生方面有些門道,嶺南一帶頑疾頗多,于是他就建議柔娘讓王鞏用按摩腳心法對付瘴氣,又說“每天飲少許酒,調節飲食,讓胃氣健壯。”

遠在嶺南的王鞏則時常安慰蘇轼,讓蘇轼顧好自身,別爲他擔心,還在回信中大談養生之術,說他正在賓州修煉身心。
就這樣過了4年,1083年王鞏奉诏回京,蘇轼聽聞後,立即備好了豐盛的酒宴,爲這位昔日摯友接風洗塵。
蘇轼本以爲受了多年的荒地摧殘,此時的王鞏已是意志消沉、落魄不堪,可等到兩人見面時,卻發現站在對面的人還是那樣的意氣風發,還是那個如玉般的豐俊男子。

席間,蘇轼趁著酒意,便問王鞏和柔娘:嶺南那邊的生活應該不太好吧?然而柔娘卻笑著看向王鞏,坦然地回答道:“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這一番真切而深情的言語,令孤身多年的蘇轼既震撼又羨慕,感慨世間的真情原來就是這般單純,也羨慕王鞏這小子命好,就連上天都愛惜他,贈予他一個柔美聰慧的佳人相伴終生,更贊歎柔娘外表和內心統一的真善美,試問這種身處逆境卻安之若素的可貴品性,天底下有多少女子能做到?

柔娘說罷,蘇轼當即爲她填下《定風波》一詞: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
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裏歸來顔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好一個此心安處是吾鄉,原來古代的愛情,也可以這麽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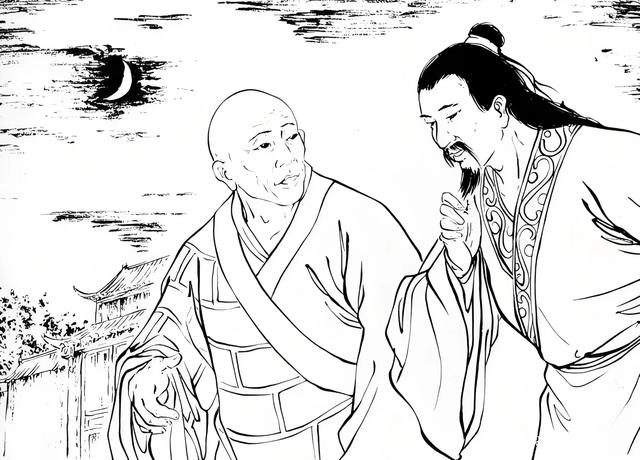


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