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鄢陵之戰中擊敗楚軍、獲取最後的勝利後,晉軍方面上至國君晉厲公,下至普通的士卒,都是興高采烈、一片歡騰;晉厲公還以‘駐軍楚營、享用楚粟’的行爲來熱烈慶祝擊敗老對手楚軍、維護晉國霸業依舊穩固及來之不易的勝利。

于是,士燮在大勝之後立即觐見並規勸晉厲公,請國君要常常保持警惕謙遜之心、時時刻刻自省;用‘天命不能常在不變’來警醒自己,和卿士大夫們團結一心、一致對外,以防備隨時到來的威脅!
士燮出仕後忠勤誠懇、盡心盡力輔佐了晉國的兩代國君,所以股肱老臣的話晉厲公當然不能不聽,總要在表面上做出接受的樣子;因此,在率軍隊飽飽地吃了三天楚軍留下的軍糧後,晉厲公便順勢宣布從鄭國撤軍,返回國內進行休整,以恢複因此次大戰而消耗過大的國力、軍力。
至于鄭伯(鄭成公)那個背信棄義、騎牆跳橫的反複小人,以後寡人有空了再來收拾他(晉厲公語)。
親自率軍在鄢陵擊敗了楚共王指揮的楚軍、鞏固了晉國的霸業後,晉厲公繼先君文公、襄公之後,成爲晉國新一代的、當之無愧的中原諸侯霸主(先君景公其實也不錯,但有邲之戰失敗的硬傷,就不好和文公、襄公並列了)。
加上之前于麻隧之戰中擊敗秦國、交剛之戰又擊敗狄人,在這幾次軍事勝利之下,晉國的外在威脅基本上已被消除,志得意滿的晉厲公認爲國外已經沒有了勢均力敵的對手,于是便把目光轉向了國內,預備動手削弱已經開始威脅公室權力的諸卿士大夫勢力,將晉國的軍政大權統統集中于公室之手,即施行‘去群大夫、立己左右’的計劃。

從晉靈公開始,晉國的軍政大權基本上由卿士家族所掌握,曆任晉侯反而失去了絕對的朝堂控制權;而爲了權力的掌控爭奪,幾代晉侯和卿士之間都發生過君臣之爭,其中靈公被趙氏所弑殺,而景公則在其他卿士的協助下反擊趙氏成功,一度消滅了趙氏大宗。
晉厲公還是‘晉國太子’的時候,就對國家大政由卿士分別出掌、公室卻不掌握絕對朝堂控制權的狀況痛恨不已,一直耿耿于懷,決心等將來自己繼位後,一定要設法改變這個‘君臣不分’的局面,施行“盡去群大夫、立己左右”,將晉國的權力盡收于公室;而這個收權的思想,伴隨了晉厲公此後的一生。
周簡王五年(前581年),晉厲公繼位之後,先後發動了和狄人、秦國、楚國的戰爭,並在這幾次作戰中以軍令統一的名義,逐漸收回了部分被卿士們所掌握、把持的軍權。而晉國的諸卿士們雖然感覺到國君在有計劃地收回自己手中的權力、不肯輕易就這樣交權,但當時晉國外部威脅重重,楚、秦、狄都在對晉國虎視眈眈,只有消除了外部威脅,晉國才有擴大利益、繼續號令天下諸侯的權力。
因此,在一致的利益前提之下,晉國君臣通力合作,一心對外,總算沒有在外敵未平之時,就先鬧出‘內讧’的笑話來。
當然,就在晉國對外用兵的時候,諸卿士們也采取了各種或明或暗的方式,來對抗晉厲公的收權行動(比如麻隧之戰,晉厲公就沒能得到卿士們的全力支持,攻占秦都雍城,徹底打垮秦國);晉國君臣彼此都在等待一個好機會,徹底了斷這一切(這也是士燮堅決要求留下楚國作爲晉國外部警惕來源的原因;楚國的威脅若在,晉國內部的卿士大夫們就會心存忌憚,無法和國君全面對抗、導致晉國生成內讧的局面)。

眼看自己曾預言過的“若外甯、則必有內患”的不幸情況即將發生,痛苦中的士燮無計可施,只能天天前往士氏(範氏)宗廟中向先祖們祈禱,請求他們保佑自己早點死去:
“君上日漸驕橫奢侈,又意外地戰勝了所有的敵人,這是昊天在故意增加他身上的致命缺陷,我們晉國的禍難就要發作起來了。燮不願意親眼看見災禍的降臨,只有在這裏向憐我、愛我的祖宗們祈禱,請你們讓我快一點死去,不要讓我和範氏被牽扯進這即將到來的禍難之中;要是你們能讓我達成心願的話,那就是我範氏一門的福氣了!”
《左傳.成公十七年》——......‘君驕侈而克敵,天益其疾也,難將作。唯祖宗愛我,祝我速死,無及于難,範氏之福也。’
周簡王十二年(前574年)六月,也就是鄢陵之戰結束後第二年,在長期堅持不懈的誠心祈禱之下,士燮終于得償所願,平安無事地老死在家中,總算得到了善終,也沒看見今後要發生在晉國內部的血腥內讧。
就在臨死之前,士燮還強打起精神,仔細囑咐著將要繼承士氏(範氏)家主之位的兒子士匄,命他發誓嚴守門戶,不得參與今後朝堂上的任何爭鬥,以免給範氏招來禍患;面對父親的臨終囑托,士匄一一應允。
士燮去世之後,他遺下的中軍佐位置出現空缺,晉厲公便命郤氏家主、上軍將郤錡繼任中軍佐;而士匄此後也順利地進入晉國朝堂,擔任新軍佐;原新軍佐郤至則升任爲新軍將。
此時,晉國朝堂八卿的新一屆排名爲——中軍將兼執政大夫栾書、中軍佐郤錡、上軍將荀偃(中行偃)、上軍佐韓厥、下軍將荀罃、下軍佐郤犨、新軍將郤至、新軍佐士匄。

在新一屆晉國四軍八卿中,郤氏家族依舊占有著三席(中軍佐郤錡、下軍佐郤犨、新軍將郤至)。而之前的郤氏,曾經四代出任晉國執政(郤芮、郤縠、郤缺、郤克),四代人中進入卿士行列的也有八人(郤芮、郤縠、郤溱、郤缺、郤克、郤錡、郤至、郤犨)。
郤氏在晉國百年經營,樹大根深、黨羽衆多,擁有的財富和權力都無與倫比,幾乎達到了“富半公室,家半三軍”的程度;就連當年以趙盾爲代表的自趙氏大宗,都無法和郤氏相提並論。而趙氏大宗被消滅後,晉國目前的卿士家族中,地盤最大、實力最強的卿族,就屬郤氏爲尊了。
士燮的中軍佐之位被上軍將郤錡按朝堂順序接任後,郤氏的權勢更高,郤錡的中軍佐距離晉國執政(栾書的中軍將)也只有一步之遙;如果情況一切正常的話,郤錡將在數年後,接替或退休、或去世(甚至是被晉厲公打擊奪權)的現任晉國執政栾書,成爲郤氏家族曆史上的第五位晉國執政。
而郤氏家族的興盛和強大,不但遭到了晉厲公本人的忌憚和警惕,就是想要穩固家族勢力、同時挑起國君和其他卿士家族內讧的中軍將栾書,同樣保持著嚴重的關注和萬分的警惕;鄢陵之戰中,時任新軍佐郤至沒有聽從中軍元帥(就是栾書自己)‘穩固待援、徐徐進攻’的命令,而是獨自出擊並大勝當面的楚軍,雖然增加了郤氏在晉國國內的影響力,但同時也使得身爲中軍元帥的栾書大丟臉面,乃至忌恨勢力大漲的郤氏。
所以,在率軍從鄢陵回國之後,警惕心極重的栾書就想采取措施報複郤氏,乃至設計除掉在栾氏身後緊緊追趕、馬上就要超越甚至取代自己家族地位地位的郤氏。
栾、郤兩家,其實都是晉國公室旁支別立氏家而來的卿族,晉國目前與國君源出一脈的卿族,主要就是栾、郤、韓三家(另外還有祁氏、羊舌氏等地位低一點的大夫家,也是晉公室別支);按道理,同屬公室別支的栾氏和郤氏不應該內部發起內讧,但栾書私心作祟,想要禍水東引,讓晉厲公與郤氏之間因爲爭奪權力而自相殘殺,以便自己得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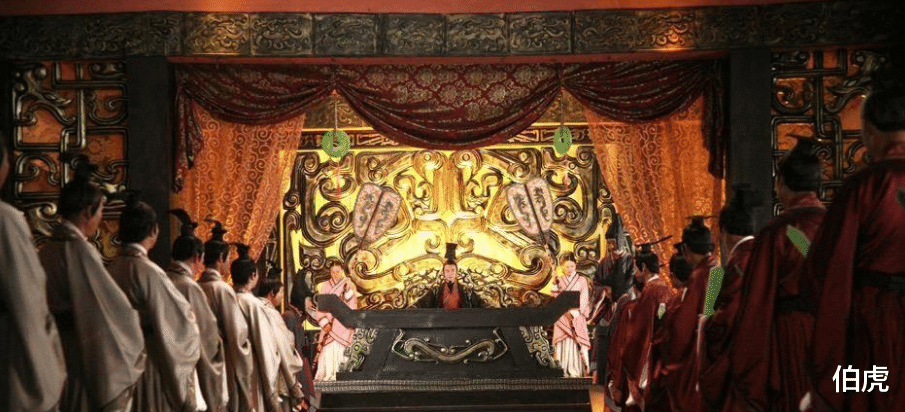
原本晉厲公從鄢陵回國之後,所制定的“收權、定政”的第一目標,就是執掌晉國軍政大權大權的中軍將兼執政大夫——栾書,栾氏的權力將被晉厲公一步一步收回;栾書如果知趣的話,晉厲公倒是不會對他怎麽樣,只是將其手中的權力全部收回,然後讓他退出朝堂、回家養老便罷了。
但栾書出仕數十年,從下軍佐一直做到了中軍將,其心思缜密、老奸巨猾,當然明白晉厲公的收權計劃針對的是誰;因此,栾書一面與晉厲公全力周旋,分散其對栾氏家族的注意力,一面則爭取將禍水引到其他卿士家族頭上去。而栾書的目標,自然就是諸卿中風頭正勁、勢力最強的郤氏家族。
這就是栾書想盡了辦法,要借晉厲公之手,鏟除原本就和栾氏有過節和矛盾的郤氏,同時又達到讓晉厲公因枉殺大臣而失去國內人心、最終自取滅亡,從而保全栾氏家族的終極目的。
此後,爲了轉移晉厲公的“奪權”第一目標,打擊潛在的政敵(其實都已經很明顯了),老謀深算的栾書經過了一系列的仔細策劃,又精心布置了一環接一環的高深圈套,讓自我膨脹的晉厲公在不知不覺中,將收權打擊的第一對象,成功地轉移到了郤氏的頭上;而具體的經過,則如下所示——
爲了嫁禍郤氏、維護栾氏的安全,栾書先在私下裏找到在鄢陵之戰中被晉軍俘獲的楚國王子公子茷,以“釋放其回國”爲條件,唆使他在接受晉厲公的召見時,構陷、中傷郤氏家族;而爲了早日回國,于是公子茷在拜見晉厲公時,按照栾書的吩咐,煞有介事地說:
“當初鄢陵之戰,我們寡君(指楚共王)是被貴國的新軍將(即郤至,當時還是新軍佐)的主動出擊所引誘,兩國這才打起來的。我當時還聽說,新軍將之所以這麽著急的進攻我軍,就是想趁機引起戰場上的大亂,以使貴國陣中出現不測之事(暗指晉厲公或許會因此而陣亡、或被俘);事後,他們(指郤氏)再到雒邑去迎公孫周(晉文公玄孫、晉厲公遠房族侄)回國,繼承君位,以此立下擁立之功。”

晉厲公再怎麽剛愎自用、驕傲自大,也還是有一定的作爲、四方征戰大獲全勝的強勢國君,不是那些庸碌昏聩的無能之輩,基本的治國用人素質一點都不差,自然不會僅憑著公子茷這個俘虜的一番話,就對國家的卿士直接下手。
但當時在鄢陵戰場上,晉厲公確確實實是看見過郤至和楚共王的使者有過深切的接觸,接受了戰場禮物,並向楚共王的車駕行禮,後來郤至又放棄了追擊潰逃中的鄭成公座車;這些事情,不得不讓晉厲公對郤至(郤氏家族)這麽做的真實用意起了懷疑,想要搞清楚其中的原因。
而爲了釋疑,晉厲公便召見執政栾書前來,詢問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和建議;這正是栾書心中所期待的結果。
來到公宮中的栾書自然裝作什麽都不知道,等晉厲公轉述完公子茷的話後,栾書才“大驚失色”地回答說:
“君上所說的這些,很有可能是真的啊!當時的戰況那麽危急,新軍將(郤至)還是一副不怕死的樣子,主動向楚軍發起進攻;而作戰中,他幾次下車、脫了頭盔向對面的楚君致敬,又接受了楚君所贈送的禮物,並在戰場上和楚國的使者東拉西扯地說了半天閑話,這事實在很蹊跷。後來,新軍將又故意放跑了鄭伯,沒有將其直接俘獲,也不知什麽原因。
當初,我們准備伐鄭時,曾事先向齊、魯、衛三國發出邀請,還遣使請他們一同出兵;可三國軍隊直到大戰結束後才姗姗來遲,沒有起到一點作用;我事後聽說,是新軍將故意授意出使三國的使者(指出使三國的時任新軍將、郤至之叔郤犨;此時郤犨已經升爲下軍佐;當時栾書之子栾魇也是出使的使者,栾書故意這麽說,是撇開自己家族的責任,將矛頭引向郤氏),要延緩三國的出兵,使國君您單獨率軍和楚、鄭聯軍作戰,因此處于危險的境地中。
不過,這些事情都是沒有確鑿的證據,還不能證明新軍將(郤氏)確實是要謀害國君、迎立公孫周回國的;下臣實在不敢妄言其他,既然公子茷對您說新軍將要讓您陷于危難境地、以便擁立公孫周繼位,那麽您不妨趁著這次向天子獻捷的機會(春秋禮儀,諸侯進行戰爭獲勝之後,都要派出獻捷使者去雒邑王都向天子奏捷,並獻上所獲的戰利品和俘虜,以示尊崇王室),以新軍將爲獻捷的使者,派他前往雒邑拜見天子;您可以暗中派人觀察他在雒邑時是否私下接觸了公孫周,以及有否密談擁立之事,再圖後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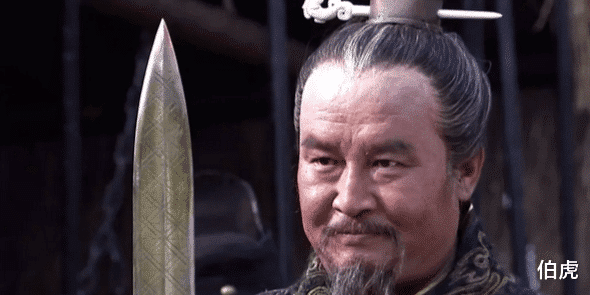
晉厲公不覺有異,對栾書的建議很滿意,因此便下令讓郤至擔任‘獻捷使者’,帶著鄢陵之戰中獲得的戰利品和俘虜,前往雒邑,向周天子奏捷。
至于齊魯衛三國出兵延緩之事,並不是栾書打擊郤氏計劃的重點,而只是一個幌子;栾書真正的意圖,是轉移晉厲公的視線,讓他關注郤至到雒邑後,是否與在王都的公孫周私下會面交談,乃至做進一步的勾連。
栾書唯恐郤至到了雒邑卻不去拜見公孫周,那麽自己的計劃就要落空,因此他偷偷讓自己的心腹以晉國使臣的身份提前趕到雒邑,先拜會了公孫周,建議他說:
“新軍將郤至,自入仕以來屢立戰功、忠勤國事,將來一定前途無量,更上層樓;此次他作爲‘獻捷使者’來王都向天子奏捷,就是國君要重用他的先兆;公孫您是公室的英才,又在王都侍奉天子,也對晉國大有貢獻;您這次一定要見一見新軍將,相互熟悉一下,將來您如果要返回晉國的話,與新軍佐交好對您是大有裨益的!”
公孫周此時尚不滿十四歲,年幼天真,不知道這都是栾書那個老狐狸的算計和陷阱,根本沒多想,于是滿口答應下來,並在郤至來到雒邑之後,主動發出邀請,請郤至恰來會面、交談。

但讓郤至和公孫周沒想到的是,這一切全都被晉厲公暗中派出監視他們的人全看在了眼裏;事後,監視者又向晉厲公做了詳細的彙報(還有添油加醋)。而晉厲公聽到郤至到雒邑後果真去拜見了公孫周,彼此還詳談了許久的回奏後,當即勃然大怒,認定郤至與公孫周勾結頗深,的確有廢立之心;從此,晉厲公開始對郤至動了殺機,乃至要對郤氏家族下手。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郤氏家族大難的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