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卿心君悅
在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中,可謂是能人與小白齊聚,陰謀與詭計並出,呈現出了一幅官場職場的衆生相。
細品這其中一個個人,一件件事,在特有的規則之下,在限定的生存環境之中,是與非,善與惡,對與錯,並沒有界限分明,反倒攪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種現象,恰好應和了哲學中的那一句話——存在即合理。
合理,是合乎某一種規律或是規則,如官場規則,職場規則。
于此,一些人看似不堪、蠢笨、不地道,甚至沒有原則、沒有底線的選擇或是行爲,在特殊的規則之下,其定義與評判未必真如上述的這些貶義詞,興許其中還內斂著一種智慧。
這未必是人生的大智慧,卻可能是某一領域、場合、環境的大智慧。
正如司禮監不顯山不露水的石公公,當他站在海瑞面前,意氣風發地自我介紹道:
“我姓石,是新任司禮監首席秉筆太監。”

而在其晉升之路中,就帶有這種大智慧。
騎在牆頭混資曆在官場中,有一句俗語:
“年齡是個寶,能力很重要,學曆不可少,背景最可靠。”
乍一聽這句話,多數人都會心照不宣地把目光盯在最後一點,會意一笑,再依次往前看。
可殊不知,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年齡”,卻是大多數人(普通人)最大的倚仗。
在這裏,請不要把“年齡”,用“幹部年輕化”的眼光局限地定義爲“年齡的大小”,而是要以變通的眼光,將其看成是資曆。
對,就是資曆——這是唯一一個不憑借背景,甚至不太看能力,單靠時間就能達成的東西。
如果說“公正會在時間的路口等待”,那麽最公正的很可能就是這一點。
回到劇情中,司禮監的石公公相對于陳洪、黃錦來說,所能倚仗的就是“資曆”。
論背景,黃錦是頂頭上司呂芳最親的幹兒子之一,是大領導嘉靖相對親近的人之一,石公公較之黃錦,毫無可比性。

論能力,陳洪是司禮監的“一支筆”,各類文件的擬稿人,自身又是一個善于心計、手段狠辣之人,石公公較之陳洪,也毫無可比性。
這裏所說的“資曆”,並不是說石公公的資曆比陳洪和黃錦要久,有優勢。畢竟論在宮裏的年頭,刷尿盆出身的陳洪,和搬酒醋壇子出身的黃錦,在宮裏呆的年頭未必就比石公公差。
而是說,對于處于劣勢,毫無競爭力的石公公來說,他就只能憑靠“資曆”這一點,等著“論資排輩”緩步向上爬。
終究,每向上爬一步,就會距離目標近一步。而每近一步,觸及目標的可能性就會越大。
看到這,有些人會覺得這些是廢話。
不!
這就是智慧,甚至還是普通人混官場的唯一之路。畢竟有很多人連這一點都沒有做到,熬著熬著,還沒等來機會,就先一步放棄了。
而且,混資曆也沒有想象的那麽簡單,並不是單純“混日子”就能混出資曆來的。
你首先得能自保,保證自己不被暗流、暗箭所傷;
其次你還得確保自己不被淘汰出序列,永遠持有競爭的資格;
達成了這兩點,你所度過的時間,才叫作“混資曆”。
否則,你所混的資曆,實際上是在混日子,是在混工齡,等退休。
說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提一下司禮監最後一個人孟公公了。

孟公公與石公公的處境相似,但在“先天”上,石公公卻比不上孟公公,其原因只有一點——石公公“有所求”,而孟公公“無所求”。
在官場“無所求”的人,無欲則剛,往往無敵,而“有所求”的人,欲望所致,則處處受限。
正因如此,才有了劇情中的這一幕——
海瑞在浙江借著查“官場貪墨案”的機會,緊咬著“毀堤淹田”和“通倭”一事不放,鄭、何二人爲逃避罪責,事事攀扯宮裏,爲了讓這二人開口,海瑞“反其道而行”事事主動攀扯宮裏,逼得旁聽的楊金水當晚就瘋了。
趙貞吉將此情況上報給宮裏,恰逢呂芳在精舍當值,就這樣奏疏到了陳洪的手中。一見事情牽扯到了呂芳倚重的幹兒子楊金水,陳洪立馬就要將事情捅大,直通嘉靖。

關鍵時刻黃錦站了出來,將奏疏暫且壓下,並去精舍報喜召回了呂芳。
呂芳見了奏疏,立馬就去給楊金水“擦屁股”,臨走前安排黃錦頂替他去伺候嘉靖。
當晚,嘉靖識破了這其中的玄虛,但並沒有絲毫怪罪呂芳的意思,反倒讓黃錦捎帶“啞迷”(外重內輕的鐵球)給呂芳,叫呂芳依令行事。
至此,司禮監的衆人對這一事件的始終,都有了心照不宣的認識——
陳洪想借此機會,坑害楊金水,並拉下呂芳的算盤,不僅落空了,還直接得罪了呂芳。
二把手得罪了一把手,這在官場上可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是下屬,必須得拿出一個旗幟鮮明的態度出來,來表明自己站A,還是站B。
晚飯時,呂芳尚未返回,陳洪與司禮監其他三人同坐一桌吃面條。
這頓飯,孟公公吃的很快,吃完面,一揚手接過站在一旁小太監遞上來的毛巾,抹了抹嘴,沒跟任何人打招呼,獨自離開了飯桌。

孟公公就是站隊呂芳了嗎?
不,孟公公雖說對陳洪的所作所爲不恥,但此舉並非想要站誰的隊,也沒人會覺得他是要站誰的隊,在衆人的心中,他的離開只是想離開紛爭的漩渦,躲到一旁去。
衆人會有這種認識,皆因清楚孟公公“無所求”,因爲“無所求”所以不涉及利益之爭。也正因孟公公“無所求”,所以他也不怕得罪人,我行我素就好。
可孟公公這麽一“表態”,當場就把石公公給難住了,畢竟石公公可是“有所求”的。
此時,石公公如果繼續坐在桌子上,不與陳洪保持距離,在一定程度上就相當于站隊了陳洪。可他若是像孟公公那般灑脫地離開,又相當于直接表態站隊呂芳,這樣又會得罪了陳洪。
關鍵時刻,石公公起身說了一句:
“能不天天都吃面嗎?”

說罷,接過小太監遞過來的毛巾,也離開了。
這樣一來,石公公離開了飯桌,算是與陳洪保持了距離,不會惹呂芳不滿;同時,他在離開時,特意強調是“對吃面條不滿”,這樣也算給陳洪留了面子,不會得罪死陳洪。
石公公的這種行爲就是典型的“騎牆頭”,雖說他這種“左搖右擺”的態度,注定了他不會被那一陣營真正地接納,但同樣,哪一派也不會輕易得罪這樣的人。
這樣一來,石公公就爭取到了“混資曆”的時間與空間。

在官場,僅靠“混資曆”就可以步步高升嗎?
不。
“混資曆”,能得到的只能是蠅頭小利,想獲取巨大的利益,還是難逃“站隊”二字。
隊,還是要站的,怎麽“站”就是一種智慧了。
沒有背景,沒有能力的石公公,最後能當上司禮監首席秉筆,靠的就是“站隊”。
楊金水瘋後不久,海瑞在浙江又搞出了事情,一番審訊,從何茂才的口中撬出了一份重量級的供狀——
“毀堤淹田”的背後主使是嚴世蕃,其中,楊金水知情。
這份供狀一進司禮監,呂芳當場就按在了手裏。
是供狀裏的內容駭人驚聞嗎?
不是。供狀裏所記錄的事情,早在事發之後,嘉靖、呂芳就已知之甚詳。
那爲何呂芳要按在手裏?
是因爲這份供狀的內容若是見了光、上了秤,立馬就會引起朝野的動蕩。
嘉靖爲保清名,就必須得興起大獄,而大獄一起,嚴黨倒不倒到在其次,他呂芳勢必會受到牽連。
爲了自保,也爲了給自己謀求一條平穩落地的路,就有了名場面——“呂芳請嚴嵩和徐階喝酒”。
原本(表面)呂芳想瞞著嘉靖,卻未想到(預料之中)黃錦再次失誤,惹來嘉靖逼問陳洪實情,在陳洪一番“挑潑”的表演下,呂芳被貶去監修吉壤,而陳洪短暫坐上“司禮監掌印太監”的椅子。

權力的變更,總會引起一系列的動蕩,畢竟新領導要“點火”,要控場,要收權。
涉及到收權,就不可避免兩件事——
一是打壓異己,一是提拔親信。
在司禮監,小五子只因叫了一聲“祖宗”,當場連升三級是如此;另一個小太監因叫了一聲“二祖宗”,被貶去浣衣局更是如此。
一直熬資曆的石公公,就在這個時候瞧准了時機,向陳洪押了寶。
在那種風雲變幻的時刻,黃錦致力于營救呂芳,孟公公一旁冷靜看戲,只有石公公站了出來,站在陳洪的身邊,聽從陳洪的吩咐,爲陳洪做事。
石公公一共做了兩件事——
其一,奉陳洪的命令,守在西苑大門,阻止六部九卿的堂官進入內閣;
其二,奉陳洪的命令,出城門親自將楊金水押到司禮監。

在這其中,石公公在陳洪面前,俨然一副“下屬”的姿態。
尤其是在第二件事中——
奉旨押送楊金水回京的錦衣衛,手中拿著一封海瑞二審的供詞,要親手交給呂芳。
面對陳洪,錦衣衛敘述完楊金水發瘋前後的事,陳洪說道:
“聽說浙江重審鄭泌昌、何茂才的供詞,你們也帶來了。”
攥著供詞的那個錦衣衛緩緩起身,答道:
“帶來了……趙中丞說了,要屬下們親手交給呂公公,然後再由呂公公面呈皇上萬歲爺。”

聽完,陳洪若有其事地說道:
“呂公公?這裏有呂公公嗎?”

此時,司禮監四個人皆在,黃錦與孟公公皆未發言,唯獨石公公一人說道:
“呂公公被派到北郊監修萬年吉壤去了,現在這裏由陳公公主事。”

石公公這段話看上去是在向錦衣衛解釋內情,可實際上其說話時所帶的別樣語氣,很明顯是在配合、討好陳洪。
陳洪聽完,哈哈一笑:
“跟這些奴婢說這個幹什麽,把東西拿過來就是。”

注意,此時陳洪就站在這個錦衣衛的對面,而石公公則坐在遠處的一側喝茶,論距離陳洪距錦衣衛更近,論方便陳洪伸手討要更加方便。
然而,陳洪話音剛落,石公公就放下了茶盞,起身走到錦衣衛身前,用手指夾出錦衣衛緊緊護住的奏疏,再到陳洪面前,交給了陳洪。

石公公這“一取一遞”意味著什麽,在場衆人皆心知肚明。
石公公就這麽徹底站了陳洪的隊,一點也不顧及呂芳重新複職的可能?要知道,此時呂芳並未撤掉“掌印太監”的職務,而陳洪名義上只是代理。
不,石公公顧慮了。
石公公接下來的一幕,不僅證明了這一點,還讓旁觀看戲的孟公公大跌眼鏡,不得不對石公公的“虛僞”暗道一聲佩服。

在黃錦的幹預下,陳洪沒能打開那封奏疏,等黃錦離去,陳洪開始審問楊金水。在陳洪看來,他能不能坐穩“掌印太監”的位置,全看他能不能從楊金水的口中撬出東西來。
見楊金水一副“裝瘋賣傻”的態度,眼睛盯著半空,陳洪惱怒道:
“看著我!”
楊金水不爲所動。
一旁的石公公又趁機發話了:
“你們進來,把他的頭按住,讓他看著陳公公。”

隨後,陳洪見楊金水仍舊裝傻,便要動刑,誰知這個時候石公公竟出言制止了:
“陳公公,萬歲爺還沒問話呢,現在動刑只怕不妥吧。”

石公公這一的行爲,當場就驚住了孟公公,讓孟公公意味深長地看了石公公好久。
陳洪見竟是石公公出言阻止,立馬面露不悅看了過去,而石公公卻毫不慌張,一臉真誠地緩慢點頭,意在告訴陳洪——我出言提醒,可是爲了你好。

石公公這一行爲雖然不地道,甚至可以說是不堪,但實用性卻是極佳的——
一來,石公公算是用行動向陳洪上交了站隊的“投名狀”,這一次阻止,陳洪即便有所不滿,有所猜疑,但也得領情。
二來,石公公這一阻止,也算是給自己留了退路,萬一呂芳複職,他也可以用今天這一行爲來化解呂芳的敵意。
也正是因此,在呂芳複職之後,呂芳和黃錦都給過陳洪臉色看,唯獨石公公,二人從未有過計較。
也正是因此,當陳洪真正上位之後,尋到機會貶去了黃錦“首席秉筆”的職位,石公公立馬得到了提拔。

縱觀石公公的官場之道,我們很難給予一個高度的正面評價。
觀其晉升之路,多是“騎牆頭”“左右搖擺”“兩頭下注”等這類卑劣不堪的手段與路數。
可對于像石公公這般的人物來說,又有什麽其他的選擇呢?
司禮監的環境擺在那裏,前進的路一目了然。
如果沒發生後續的那些意外,司禮監的一把手呂芳,是大領導的絕對親信,呂芳不倒,後續提拔的人自然會是呂芳的人。而呂芳會提拔的人,自然是楊金水、黃錦與馮保。

在石公公面前擺著的就只有兩條路——
一,呂芳的人輪流當掌印太監,陳洪釘死在首席秉筆,他原地踏步;
二,陳洪有機會上位,他可以依靠陳洪爭取一個“首席秉筆”。
所以,他選擇站隊陳洪,是情理之中的;他又不敢得罪呂芳,也是自然而然的。
可能會有人說:一定需要哈著腰、玩著手段上位嗎?
說到底,有些時候人是沒有選擇權利的,踏入了某種環境,陷入某種規則,人能做的只能是遵循著道路的曲折而行,而非內心的曲直。
畢竟,無論是擡頭走路,還是低頭哈腰,很多人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想要活出個人樣。
爲了活出個人樣,有些事也就不能單純用“對錯”“是非”“曲直”來評判了。

也許會有人問,那石公公混到最後能當上“掌印太監”嗎?
大概率是不能的,石公公對此也心知肚明,但這並不影響他想要前進,想要更進一步。
也許向前走就有機會,有希望了呢,也許這一次不前行,以後就再無希望了呢。
這個時候,也就沒有必要去诘問他——這麽做的意義是什麽?
什麽時候做什麽事,本就沒有什麽特別的意義,想做,只能做,也必須要去做,就是最大的理由。
至少,在石公公的心中,憑借自己的忍耐與機智,敏銳與果斷,他當上了司禮監首席秉筆。

這樣一來,他在司禮監,乃至在整個大明朝,也算成了一號人物。

卿心君悅,讀別人的故事,過自己的日子。用文字溫暖你,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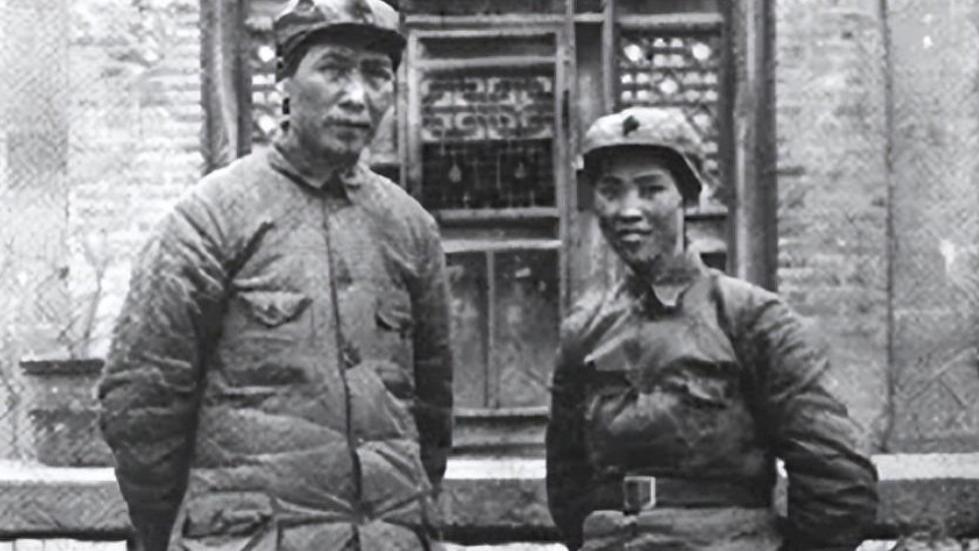


馮保厲害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