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謝爾格·貝利亞在其著作中揭露了一些不爲人知的真相,在學界內引發巨大轟動。他的說法看上去頗具說服力,真實度很高,而倘若這些都是真的,那麽斯大林逝世後發生的一段曆史將被徹底顛覆。
謝爾格表示,自己的父親死于一場險惡的“政治鎮壓”,其過程之殘酷堪稱駭人——其辦公室的牆壁上留下的誇張的彈孔,意味著蘇聯軍隊以一種近乎于屠殺的方式,用大口徑機槍直接對目標進行了消滅。
而謝爾格的父親,正是臭名昭著的蘇聯前內務部長、超級權臣拉夫連季·巴夫洛維奇·貝利亞,他向外界控訴自己的父親當年並沒有被捕,也沒有經曆調查和審判,我們所熟知的一切都是當權者們編造的謊言。

斯大林逝世後,巨大的權力真空使得蘇聯高層經曆了一輪又一輪殘酷的內部鬥爭,掌握著大量“黑料”的超級權臣貝利亞首當其沖地成爲同僚們的攻擊對象,黯然出局。
按照蘇聯高層的說法,這個過程驚險但迅速:1953年6月,赫魯曉夫以夏季演習爲借口,讓時任國防部長的布爾加甯抽調部隊進入莫斯科。從一些資料中我們不難看出,蘇軍的部署極有針對性,正是爲了在事發後可以第一時間壓制住規模龐大的內務部武裝,避免陷入混戰。
幾天後,馬林科夫宣布召開部長會議主席團會議。5位將軍提前藏在隔壁的房間中,殺氣騰騰。
衆人精心設置好陷阱,等待貝利亞入局。
1953年6月26日,貝利亞大大咧咧地走進會場,他一向狡猾謹慎,唯獨這次,面對山雨欲來的緊張氛圍,他破天荒地沒有展露任何懷疑。
當赫魯曉夫在會上話鋒一轉,突然向他發難時,按照官方的說法,貝利亞的臉上頓時寫滿錯愕與慌張。
在他做出反應並試圖呼叫自己的守衛之前,赫魯曉夫便按響了桌下的電鈴,將軍們一擁而入,一舉將其拿下。
這個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些有趣的小插曲:電鈴設置在馬林科夫座位的桌面下方,但由于這位難堪大任的“接班人”太過緊張,摸了半天都沒摸到電鈴,坐在一旁的赫魯曉夫實在看不下去了,決定親自出手。
經過漫長的調查與審判,1953年12月23日,法庭終于做出宣判,將這位超級權臣與其最核心的6位心腹處以極刑並立即執行。

而當時究竟是誰制服了貝利亞,大夥兒更是急著往自己身上攬功貼金。
朱可夫當仁不讓地表示:當然是我啊,難道還會有別人——是他第一個沖入房間扭住了貝利亞的雙手。
赫魯曉夫回憶稱,他看到貝利亞把手伸進公文包,擔心他拔槍,于是一個箭步沖上去按住了他。
莫斯卡連科將軍十分笃定地說,若非他持槍威逼,貝利亞絕不會乖乖舉手就擒。
巴季茨基將軍認爲他沖上去一把抱住了貝利亞,這才是整個計劃順利成功的關鍵。
這番“爭功請賞”乍看讓人哭笑不得,然而若幹年後,貝利亞兒子的一番話,讓這個不起眼的曆史小插曲瞬間變得詭谲起來。
謝爾格·貝利亞用近乎指控的語氣表示:他的父親既沒有被捕,也沒有經曆調查和審判,法庭上的那個也是個冒牌貨。真正的貝利亞死于一場險惡的謀殺——當天,一群軍人包圍了他的官邸,發動了滅絕式的攻擊。
若問證據何在?有人親眼看到了牆上布滿的大口徑機槍造成的彈孔,而這位“現場觀衆”,在不久後便被剝奪了權力,更是于1977年死于非命。
那麽這件事的真相如何,其中的陰謀論是否當真成立,我們不妨先把所有的疑點和證據擺出來。

我們常說“當局者迷”,尤其是政治人物,爲追求權力不擇手段乃至陷入瘋魔,曆史上這樣的事例簡直不要太多。而貝利亞似乎是個另類,他不但清楚斯大林對他的期待,並且曾在不同時間點、不止一次地表達了自己的抵觸。
早在1938年7月,當得知要被調往莫斯科並委以重任後,貝利亞曾試圖婉拒,卻被斯大林以“大義”拒絕,勸說他爲國出力。
斯大林同時向貝利亞許諾:“把契卡整頓好,然後如果願意你可以回老家。”
有著亨利希·格利戈裏耶維奇·亞戈達做前車之鑒,貝利亞豈能不知一旦蹚進這灘渾水意味著什麽?但斯大林把話說到這份兒上,貝利亞已經不敢再拒絕了。
于是,他在1938年8月29日的日記中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和無奈:“我說了,對任命不感到高興……我最好在格魯吉亞工作。但命令就是命令。”
或許貝利亞很清楚,不管你爲國家做了什麽,只要接受這個職位,曆史就一定不會給他好的評價。身爲秘密警察的他可以毫不顧忌地收集同僚的黑料,大肆殺伐,在政治鬥爭中搶占高地,但這會因此淪爲衆矢之的。
也許正因如此,斯大林逝世後,他才那麽急切地向外界釋放積極信號,對民衆釋以民主和善意,爭取民心。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是嗎?
但遺憾的是,他的自救失敗了。

後斯大林時代的最初階段裏,貝利亞握著一手好牌,怎麽看都不會輸。尤其是他手握一張王牌——外界普遍認爲的“接班人”馬林科夫。
據赫魯曉夫回憶,他計劃的關鍵就在于馬林科夫的態度,他明知後者是貝利亞的政治盟友,因而非常緊張。言外之意,倘若馬林科夫明確拒絕,那麽計劃很可能會泡湯,曆史也將改寫。而馬林科夫與貝利亞的同盟關系是經過政治戰火洗禮的,赫魯曉夫擔心他勸說不成,反而密謀暴露後,會招來對方的反戈一擊。
即便馬林科夫只是單純拒絕,不做任何反制,那麽計劃也極可能泡湯,曆史也將改寫。然而過程之順利不但超乎所有人想象,馬林科夫後來還主動說服了起初不怎麽想加入的伏羅希洛夫。
這個過程中,只有米高揚明確地發出了反對聲音,倒不是不同意拿下貝利亞,而是反對采用如此粗暴的方式——米高揚從維護最高領導層顔面的角度考慮,希望他們能處理得更體面一些。
馬林科夫的“背刺”,成了整個事件中最爲關鍵的一環。
按照蘇聯官方的說法:1953年6月26日,政變者們在軍方的幫助下,利用召開主席團會議的機會控制住了貝利亞,同時借由“夏季演習”名義開進莫斯科的蘇聯軍隊壓制住了內務部武裝部隊,整個過程迅速到敵人們根本來不及做出反應。

9月17日,當局通過決議,批准成立特別法庭。
12月18日,貝利亞案正式開庭,經過長達5天的審判,法庭給被告們扣上了一個個嚴重且部分有些莫名其妙的罪名,其中包括“叛國”、“陰謀顛覆蘇維埃政權”、“竊取國家權力”、“勾結並試圖複辟資本主義”等等。最終,7名被告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
庭審中,控方拿出了乍看極爲確鑿的證據,其中包括貝利亞于7月2日至7日分別寫給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的三封信,他在信中表達了自己的忏悔。這些信件被公開宣讀,令人們對這位超級權臣以及他被擒獲的過程深信不疑。
這個過程乍看沒有問題,但倘若深入去看,問題可太大了。
首先,檢方出示的證據,反而是疑點最大的。
這三封“忏悔信”中的兩封,用的是十分僵硬的印刷體,要知道,貝利亞一生中寫了數不清的信件,批複過無數文件,極少用這種字體。
對于剩余的一封信,筆迹專家做過非常謹慎的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雖然寫信者在極力模仿貝利亞的筆迹,而且看上去非常相近,但從細節處展露出的書寫習慣,尤其是信中的署名來看,這絕不可能是貝利亞親手寫下的。
其次,衆所周知,蘇聯是個非常講程序重形式的國家,即便在上世紀30年代那樣特殊的曆史時期,當局依舊要求囚犯在“認罪書”上簽字。
然而蹊跷的是,此案中其他6名被告的案卷都沒有問題,該有的都有,唯獨貝利亞的案卷問題重重,沒有簽名和手印,沒有死亡報告和火化文件,甚至連其中的照片都是不知從哪找來的一張貝利亞年輕時的照片。要知道,蘇聯相關法律中有明文規定:犯人入獄後要第一時間拍攝正面和側面照,這種級別的犯人,不至于連張正兒八經的照片都沒有吧?
如此多的反常之處偏偏全集中在一人身上,這難免不讓人生疑。
相比于這些晦澀的疑點,貝利亞之子提供的證據就簡單粗暴許多。

謝爾格回憶,1953年6月26日正午12時左右,他突然接到電話,來電者是兩次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功勳飛行員阿梅特·汗。
“謝爾格,我告訴你一個可怕的消息,不過你要堅持著!你們的房子被軍人包圍了,你的父親非常可能已被打死。我已經要了一輛汽車在克裏姆林宮的大門,你坐上去機場。趁爲時未晚,我打算把你拉到別什麽地方去!”
蘇聯醫學科學院院士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布爾加索夫少將也在回憶錄中聲稱,那天中午,他在蘇聯裝備部長辦公室裏看到了失魂落魄的鮑裏斯·利沃維奇·萬尼科夫,詢問之下,後者說道:“我們的領導,拉夫連季·巴甫洛維奇·貝利亞沒了。今天他在莫斯科自己的住所被槍殺了。我到那裏去過……”
結合其他知情者描述,我們可以還原出這樣的現場:當天,大批軍人突然出現並包圍了內務部大樓,解除了建築周圍內務部人員的武裝。一些士兵迅速沖進建築,緊接著有槍聲從中傳出。
這些執行“斬首任務”的士兵攜帶了大口徑機槍,足以摧毀目標負隅頑抗的意圖,牆上那些誇張的彈孔便是佐證。或許是軍方的人數占據絕對優勢,又或是懾于軍方的殺氣,貝利亞的爪牙們並沒有抵抗,而是選擇了投降看戲。
據目擊者之一的韋傑甯博士的回憶:“我當時緊挨貝利亞辦公室的一扇朝向院子的窗戶。從辦公室射出的兩發子彈打碎了靠樓拐角處第二扇窗戶的玻璃。”
韋傑甯稱只有貝利亞和他的兩名貼身警衛被擊斃,有一名死者被蓋著帆布擡出了大樓,隨後,貝利亞的副手謝爾蓋·尼基福羅維奇·克魯格洛夫出面控場,他要求所有人都進大樓,顯然是爲了防止消息外泄。
雖然謝爾格沒有親眼見證父親的死亡,但基于這些證據,他非常肯定當初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的只是個冒牌貨。
回過頭再看,就能發現赫魯曉夫們編造的謊言究竟有多拙劣了。這也難怪一向謹慎的貝利亞在走入會場前爲何沒有察覺異樣,爲何手握數十萬武裝部隊的他沒有給自己留後路,區區5名軍人就將其生擒。

幾年前,筆者曾在知乎上看到有人問這樣一個問題:當年貝利亞究竟該怎麽做,才能避免一死?
網友各抒己見,但討論到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貝利亞無論做什麽都無法改變結果,即便他在斯大林逝世後第一時間就宣布辭職,主動舉白旗投降——這非但救不了他,反而會讓他死得更快更慘。
政治場上的規則就是如此殘酷,如今回看,1938年8月29日寫下那篇日記之前,當最高領導人向他發來任命,發現無法推辭後,貝利亞揉碎在字裏行間那種漫不經心的抱怨與牢騷,更深層的恐怕是某種程度的絕望。
也或許,斯大林當初就是挑了這麽個人,作爲依附在他權柄上的寄生蟲,成爲他個人意志的延伸,隨著他的屹立而崛起,也隨著他的死亡而毀滅;在完成所有既定的曆史使命後,即便不願意,此人也必須就此退場。
“拉夫連季·巴夫洛維奇,我的老朋友,沒想到這麽快就又見到您了。”
兩人在另一個世界相遇,斯大林叼著煙鬥,上下打量著對方,眼神中沒有一絲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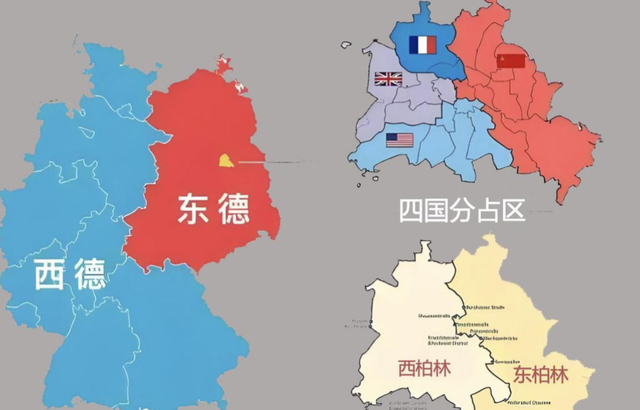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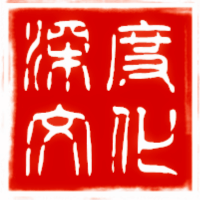
胡編亂造貝利亞是被槍決的,臨刑前還求饒
他們任何人想贏都必須聯合朱可夫,只可惜貝利亞和朱可夫有過節。
過眼雲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