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的童年是什麽樣的?
在深圳南山區,
一批改建後的幼兒園給出了這樣的答案:
一座可以“上房揭瓦”的幼兒園,
孩子們可以在露台上盡情地攀爬、運動;
一座“打通隔牆”的幼兒園,
孩子們可以“串班”嬉鬧;
一座“擁抱自然”的幼兒園,
起伏的遊廊如同堆疊的白雲,
奔跑其中,自然也觸手可及……

▲
“百校煥新”行動發起後,深圳南山區陸續有73所公立幼兒園接受校園改造,工期僅有一到兩個暑假,“學生不挪移、不停課”

▲
碧榕灣幼兒園改造後的多功能大廳,孩子們在這裏上體育課、音樂課
這些讓人“羨慕哭”的幼兒園,
都是深圳“南山百校煥新”行動中的參與學校。
2022年3月起,
深圳南山區143所老舊幼兒園、中小學
在低成本下,陸續得到創新改造。
每個工期僅有一到兩個暑假,學生課不能停。
雖然是“微基建”修繕項目,
卻讓這些學校煥發出全然不同的面貌。

▲
新桃源幼兒園的屋頂,被改造成了一個立體的遊樂園

▲
改造後的海月花園幼兒園

▲
“百校煥新”總策劃周紅玫,建築師姜伯源、顧田
有園長說,改建後的幼兒園,
“孩子都更靈動,更鮮活了!”
4月下旬,一條攝制組來到深圳,
對談了總策劃周紅玫,
以及兩位主持建築師、一位園長,
我們暢聊幼兒園空間如何釋放兒童的天性,
也探討低生育率背景下的幼兒園設計,
“可以改造成社區中心、養老中心,
我們爲未來做好這樣的一個空間的預留”。
編輯:韓嘉琪
責編:陳子文


▲
新桃源幼兒園的草地上,孩子們在“串燒烤”“炒菜”“搭爐子”
在深圳市南山區的新桃源幼兒園,孩子們的每一天都是在酣暢淋漓的“玩”中度過的。
一樓的院子有諸多的活動分區,每個人都“各司其職”——有人在草坪上“炒菜”,有人戴著安全手套搭爐子,還有專門來享受大餐的“小食客”。旁邊不遠,一群小朋友忙著挖沙子,蓋城堡。另一群孩子,全副武裝地戲水,有人在探究水車的運動,有人在水裏遛“金魚”……
三樓的屋頂,是整個幼兒園最亮眼的設計。露台上,設置了一系列的運動器械,攀爬的索繩、步梯、台階,構成了一個系統性的立體樂園。

▲
屋頂被改造成了一個系統性的遊樂園
晴朗的日子裏,屋頂上充斥著孩子們的嬉鬧聲,不斷上演著“體能大循環”。擁有30年幼教經驗的園長栾紅楓半開玩笑地向我們介紹:“新桃源的小朋友們是可以上房揭瓦的。”
如果在幼兒園走一圈,你很快就會發現,兒童才是這個空間真正的主人。園內所有的標語都是孩子們自己繪制的,哪怕字迹歪歪扭扭、線條隨意潦草;空間的使用方法也是孩子們自己開拓的,比如原本並不美觀的立柱被挂上了簡易的滑索。

▲
園長栾紅楓和孩子們一起觀察植物
但在改造之前,這所幼兒園卻遠遠沒有這麽“歡樂”。2020年,栾紅楓被調任至新桃源幼兒園當園長的時候,幼兒園剛從民辦轉爲公辦,設施老舊,空間沉悶閉塞,一樓和屋頂的活動場地雞零狗碎,對孩子的活動很不友好。
2022年暑假,新桃源幼兒園成爲“百校煥新”第一批改造的幼兒園。設計初期,建築師印實博和園長、老師們聚在一起探討,兒童的天性是怎樣的?如何用空間釋放兒童的天性?
爲了能讓孩子們盡情地奔跑玩耍,建築師拆除了不必要的矮牆和圍擋,打通活動場地,不僅實現了平面上的聯通,還通過加設空中連廊,把不同高度的屋面串聯起來,讓孩子們實現整個建築的立體漫遊。

▲
校園裏的標識,都是由孩子們繪制的
爲了滿足小朋友的好奇心,教師的餐廳、部分辦公空間也被設計成了透明的,因爲孩子們總是對成年人的世界充滿疑問:老師們中午吃什麽呀?他們和我們吃的一樣嗎?
“空間是孩子們最好的通識課本”,建築師就在設計過程中,留下了很多科學探究的伏筆,也設置了一些小小的“障礙空間”,以便孩子們在探索後發問、求證。
比如,空中走廊被設計成了不同形態,短斜坡、長斜坡、緩斜坡、陡斜坡,小朋友拿著廢舊的滾筒,從不同的斜坡上滾下來,他們會發現,滾筒軌迹不同,速度也不一樣;院子裏的戲水池,安裝了不同的孔洞,孩子們在玩耍的時候會發現,堵住一個孔,其他孔洞噴出的水柱的高度也不一樣了。

▲
小朋友們一邊玩水,一邊探究科學知識
“在一個多變的環境下,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也會在每天的生活裏不斷被激發”,從事幼教工作30年,栾園長親身經曆了學前教育的成長和變化,她感慨,現在幼兒園裏的小朋友特別鮮活,特別有創造力,狀態和30年前被要求“背起手,排排坐”的孩子們是不一樣的。
栾園長不鼓勵把孩子們圈在室內“死記硬背知識點”,在幼年階段,動手能力、自主學習、自主探究的能力才是奠定他們日後學習生活的關鍵,而一個好的空間,正是塑造他們心智、品格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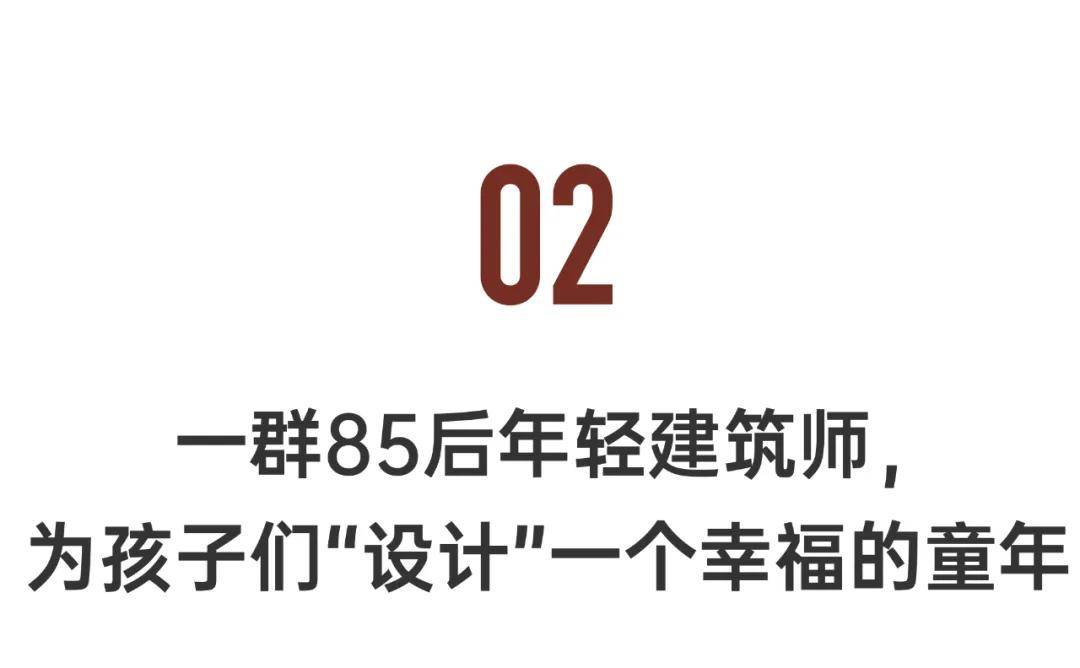

▲
海月華庭花園幼兒園改造後的俯瞰圖
空間如何能陪伴、呵護兒童的成長?
總策劃周紅玫聊到了幼兒園的特性:“幼兒園更像是一個集體生活的大院子,孩子對所處的環境和空間是有探索的天性的。學校的每一寸材料,每一個結構,每個欄杆……都是孩子認知世界的重要媒介。”
碧榕灣幼兒園的主持建築師姜伯源是一位“90後”,他所帶領的建築師事務所是“百校煥新”中最年輕的團隊。姜伯源小時候在北京的胡同裏長大,彎彎曲曲、枝枝叉叉的巷子,就像迷宮一樣,總能給他帶來意外的發現。童年的經驗,讓姜伯源意識到空間的豐富性對孩子産生的深遠影響。

▲
碧榕灣幼兒園的改造靈感來源于它的“榕樹文化”
接下碧榕灣幼兒園改造項目的時候,姜伯源對它的印象是“像一個用舊的派出所辦公樓”,在民辦園時期,幼兒園曾經曆多次改建,所以遺留了很多曆史問題,采光差、空間利用率低,還有一連串的安全隱患。
姜伯源想要和團隊把空間“歸還”給兒童,設計一所“探索欲和安全感共存的幼兒園”,而不是規訓、限制他們的空間。
“探索欲和安全感,在校園設計中常常是有點打架的。爲了保證安全性,往往就有很多過度的保護措施,讓空間喪失可以被探索的潛力”,反之亦然。團隊就在兩者之間最大限度尋找平衡。

▲
改造後的音體室的壓低了天花板的高度,地面和牆面使用了相同的材料,可以給孩子們帶來一種“被包裹”的安全感
爲了保留幼兒園自己的榕樹文化,設計師團隊在外立面用象征榕樹的棕色、綠色做了一個塗裝體系的改造,同時爲每一棵榕樹留出成長的空間。
孩子天性向往明亮的空間,團隊就在教室外面加置了一個反光板,延長太陽反射進入教室的時間;音體室被刷成了暖橘色,一端開了大圓窗,另一端開了拱窗,代表“太陽”的形狀。

▲
透明的玻璃門替代了厚重的牆體,孩子們的活動不再局限于一個班級的空間內
在室內空間,開放的玻璃折疊門取代了原來厚重的牆體,少了班級之間泾渭分明的界線後,孩子們是可以串班的,“因爲兩個小孩在一個屋子裏,很快就會沒有事情幹了。但孩子們在追跑打鬧的時候,很多交流和互動就會發生。”
一位來自斯洛文尼亞的建築師也曾提出過相似的觀點,名爲“分享時間理論”:串聯的大型空間,有助提升小孩的社交能力、觀察能力和身體素質。
團隊在空間細節上也費盡心思,天花板上開出的圓洞、燈軌上的射燈,就連踢腳線上方的通風孔都是精心預留的……這些“不經意”的細節,都可以引發孩子們的“驚奇”。
尺度,是兒童空間設計的另一個關鍵。改造前的音體室有5米多高,對孩子來說過度空曠,團隊就把天花板壓低下來,讓牆和地面使用了同樣的材料,“地面上翻以後,會有一種包裹感,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盒子裏。”

▲
改造後,海月華庭花園幼兒園的視覺風格由具象轉變爲抽象,外立面和雲梯的靈感來自于“清風疏影、浮雲流水”
在海月華庭花園幼兒園,建築師顧田和沈夢岑把對自然的感知融入了校園。外立面是柔和漸變的彩色曲線,像風吹過的水面,泛起漣漪;室外空間加建了一個立體的白色遊廊,像12朵飄散的白雲,也像12個巨大的嬰兒床。
錯落的遊廊下方有秋千、滑梯、攀爬的吊繩……形成了很多迷你的角落,建築師顧田解釋:“就像貓喜歡盒子一樣,人也喜歡找一個小點的角落躲起來”。

▲
遊廊的下方,加入了秋千、滑梯、攀爬牆
遊廊還可以用作風雨連廊,南方天氣濕熱多雨,放學後,孩子們可以從遊廊下方穿行而過。
“每個人都擁有對童年的話語權,正是因爲我們走過了童年並離開了童年,才更能知道童年需要什麽、渴望什麽”,建築師沈夢岑曾在設計手記中寫道,給兒童做設計也是回溯童年的過程,她希望能把自己對美的認知、對美的想象力傳遞給孩子們,守護他們的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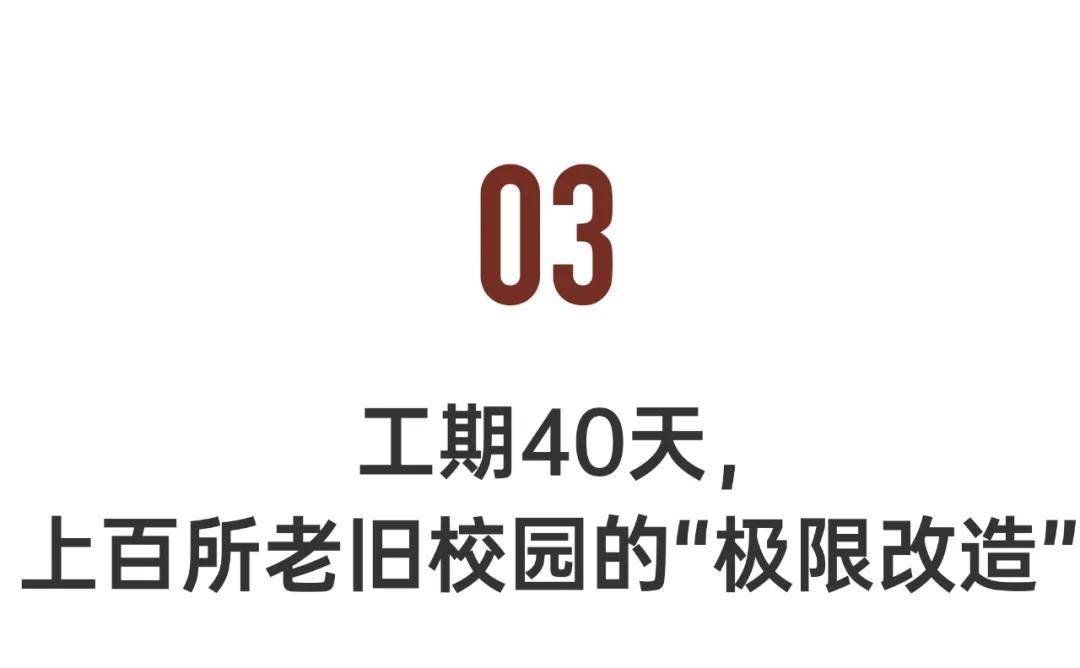

▲
“南山百校煥新”總策劃周紅玫
2022年3月起,深圳市南山區政府爲解決高密度城市中“存量校園”更新改造的需求,工務署協同區各職能部門共同探尋出一條不同尋常的創新實踐。
至今,深圳市南山區已經陸續有143所中小學、幼兒園接受了改造,超12萬名學生受惠。改造幾乎都在一到兩個暑假內完成。
“這類每年一次的老舊校園修繕項目工期很短,預算低,很難吸引高水准的建築師參與,常常淪爲裝修工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百校煥新”總策劃周紅玫告訴我們。
周紅玫希望“百校煥新”可以打破校園修繕工程的傳統操作模式,用“針灸式”的微改造對校園進行系統性升級,一校一策。

▲
很多校園年久失修,存在著諸多安全隱患

▲
改造前的九祥嶺幼兒園,由城中村的舊工廠改造而成,活動空間狹小、走廊僅有1米寬
深圳經過40多年粗犷、高速的發展,留下了一系列的存量建築問題。私搭亂建、違規改造,問題都是經年累月形成的。
走訪這批老舊校園的時候,周紅玫特別震驚,很多校舍建于八九十年代,年久失修,視覺元素糟糕,還存在著結構安全、漏水漏電等問題。另一方面,這些校園的密度很高,迫于學位壓力,原本的架空層、活動空間都被改造成了教室或者功能用房,給孩子的公共空間極其匮乏。
因此,在百校煥新行動中,很多校園都增加了應對南方多雨氣候的“灰空間”,不僅可以遮風遮雨遮陽,還隱性地增加了容積率。建築師們也用抽象的美學風格取代了千篇一律的“花朵動物”的具象元素,塑造孩子們的抽象思維。

▲
改造後的九祥嶺幼兒園

▲
改造後的育才四小
但改造難題也隨之而來。由于當年的城市檔案建設沒有那麽完備,“建築師找圖紙都就像做偵探一樣”,疫情期間,很多建築師不能及時抵達學校現場,只能在網上研究校方打包發送的“像素包漿照”。
校園改造不僅限于既有建築的空間、結構,工期也很短,孩子們不能停課、不能挪移,必須在一到兩個暑期裏完成。周紅玫感歎:“螺蛳殼裏做道場,比很帥地在一塊空地上造出一所學校難度還要大。”

▲
很多學校身處老舊小區,四周路面狹窄,施工難度極大
另一個難點是:沒有現成的審批流程。周紅玫就把區住建局、土監局、規自局、教育局等多個部門的人拉到一起,共同尋找新的審批路徑,在一個平面上折疊決策。省去了傳統線性審批裏“層層傳遞”的時間,加上工務署積極推動流程優化,整個項目從立項起就變得超乎尋常地高效。
通常,青年建築師在城市重要的公共建築招投標裏集體失語,周紅玫希望“百校煥新”能給優秀年輕建築師爭取寶貴的機會。創新的“矩陣式集群”設計模式保證了高效和産出質量,一個學術總牽頭人,外加4~8組的導師,把控年輕設計師的出品方案,並在落地過程中給予技術層面的支持。
年輕的建築師們也想盡辦法“在極限的時間裏做出最好的改造”,比如,盡量讓一個設計解決多個問題,天花板上用于裝飾的孔洞,可能同時能夠吸收噪音,充當空調出風口,以便節省工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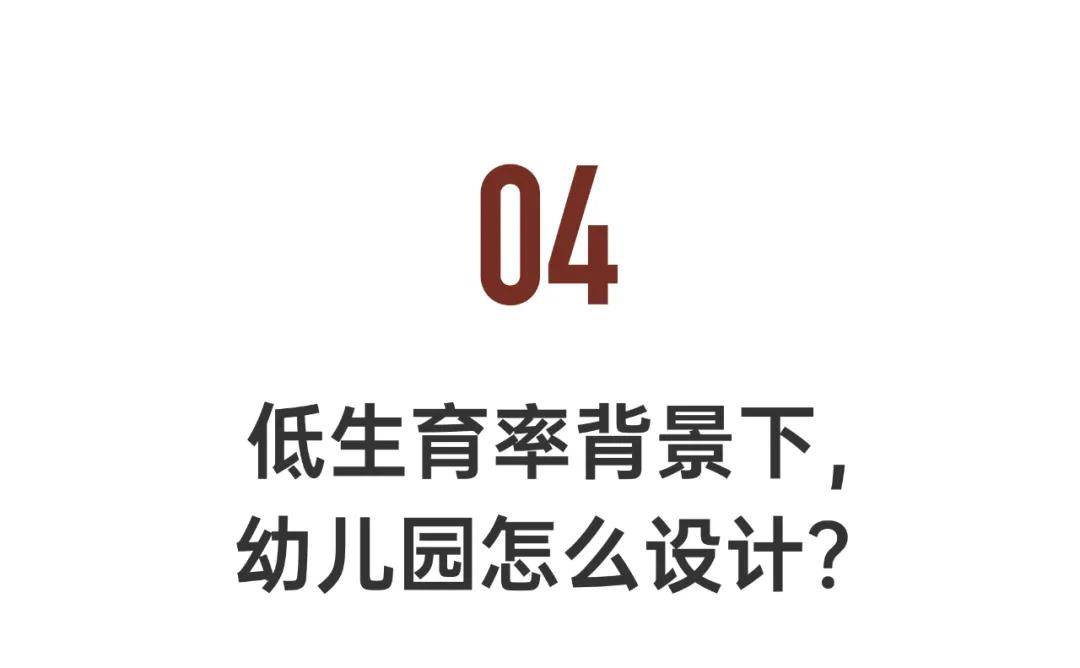

▲
改造後的校前區可以與社區進行共享,爲周遭居民提供休憩場所
當下,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全國各地的幼兒園也開始出現“關停潮”。
深圳作爲全國最年輕的城市,平均年齡僅爲32.5歲,生育率高于全國平均值。深圳也是全國率先提出系統性建設“兒童友好”目標的 城市,很早就倡導以一米的高度看城市。
但在不遠的將來,席卷全世界的“人口危機風暴”,也很難避開這座城市。
周紅玫發起“百校煥新”的另一個初衷是:我們解決學校問題的同時,能不能讓城市、社區變得更友好一點?
“在高密度城市,學校作爲最核心最基礎的公共建築,不應該是一個象牙塔,不應該是封閉的孤島。”

▲
新桃源幼兒園門口的接駁空間

▲
新桃源幼兒園的設計圖。建築師順應小區內的老樹增設連廊,改善小區物理環境的同時,保留居民的曆史記憶/對角線建築工作室
在百校煥新中,很多學校都開始嘗試向所在的社區敞開懷抱。改造後的幼兒園校前區,爲家長、附近居民提供了遮風擋雨的休憩場所;大量的風雨連廊,不僅是兒童放學後的友好安全路徑,同時也共享給周邊社區。海月華庭幼兒園的建築師團隊提出,把幼兒園設計成“社區盆景”,提供小區的環境綠化。
周紅玫已經做出了大膽的設想:這一系列學校和社區之間的接駁空間,無形中促進了學校和城市的互動,“未來隨著出生率的下降,就可以改造成社區中心、養老中心,我們爲未來做好這樣的一個空間的預留”。
她相信,建築的核心還是人,“我們是想用小的資源去撬動城市和大家的認知,解決人與社會,人與城市的關系”。
部分圖片由百校煥新設計聯盟、ACF域圖視覺提供

[點贊]這種想法和做法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