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傍晚就看完電影,在天橋上駐足半響,看著腳底下奔騰的車流,城南的雲層還透著陽光,城北的烏雲則在集結,遙想這撥雲見日的和平世代之來,聯想著暗潮湧動的寰宇秩序之去,總想寫點什麽。入夜在院裏發呆,暴雨洗禮過的京郊大地,透著泥土和植物的清香,萬物在路燈的守護下葳蕤生長,蟲鳴的交響中,又想起了這部電影。
原始的觸動有兩點:一是黃軒飾演的李達在天台,和愛妻王會悟聊起當年抵制日貨,點火時發現,手中的火柴也是日本造,茫然于偌大的中國,連一根自己的火種都沒有;二是青年毛潤之圍觀洋人Party,燈紅酒綠,一欄之隔,若有所思的他突然奔跑起來,從南京路一直跑到了外灘的外白渡橋。
李

達表面上在說國家羸弱,虎狼環伺,背後另有情緒和所表。此時的李達,剛會晤馬林,本興致盎然的會面,因爲對方遞過的一包錢,變得別有意味。一大缺錢,那是肯定的,李達家宴毛潤之時,說得很明白了,爲了錢,陳獨秀在廣州和陳炯明杠上了,最後連一大都沒趕上。可接這錢,意味著成爲別人分舵,李達和李漢俊果決相拒。天台上,李達表面上在說洋火,其實另有憤懑和遠思。初代黨人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不能走附庸之路,要有自己的火種。影片在此沒有台詞明示,表達暗藏于言語之外的情緒中。
毛潤之奔跑的那場戲,更是始終無一台詞,一切盡在情緒的流轉之中。一開始,他和圍觀民衆一樣,被洋人盛大的Party吸睛,甚至試圖混在洋人隊伍中進場,被攔後的他,突然意識到,這熱鬧非凡的光景背後,是弱國的反差,于是奔跑起來,直到在外白渡橋上駐足,重新流露出欣喜之情。導演選擇這出戲,不是沒有出由。毛潤之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1917年以“二十八畫生”之名刊登于《新青年》的《體育之研究》,青年毛潤之喜好運動之余,懷有一顆運動強國之心。此處用一段跑步戲的調度,來表現青年毛潤之的情緒流轉,再合適不過了。從南京路到外白渡橋的路,我不知道走過多少回,如今百年滄桑的老舊建築不論中西,皆成新上海的美景和風情,幸甚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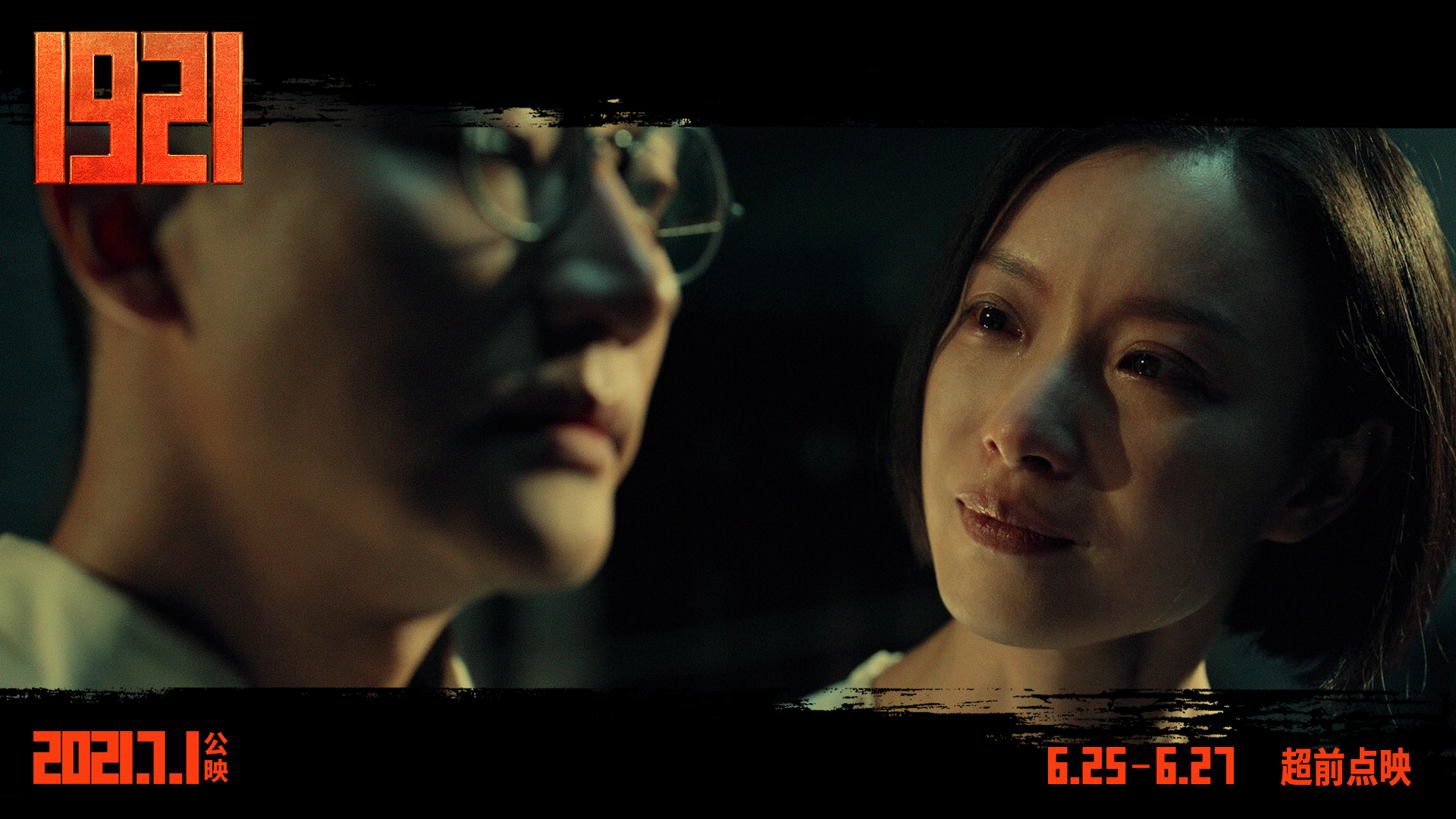
“美景”還有片中的王會悟,那麽婉約,灼灼其華,對新郎官李達來說,是“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對觀衆來說,是“揚娥微眄,懸藐流離”。作爲李達之妻的王會悟,雖不在十三代表之列,卻參與了會議籌備和會議全程,會議地址、代表住處皆由其安排,密探攪局後,又是她提議轉戰嘉興南湖,不是代表勝似代表。看得出導演黃建新和鄭大聖對這一角色的厚愛,不僅把主敘事視角交給了李達夫婦,還把最美的鏡頭給了王會悟。由李達之妻、毛潤之之妻和陳獨秀之妻組成的年代美女團,不僅有人文底蘊還有時代擔當,在鏡頭裏就像行走在林微因的詩句中。
這些浪漫主義的鏡頭即是黃建新和鄭大聖導演組合的花火,也是黃建新《建國大業》以來的新主旋律敘事的變量。此前《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三部曲和《決勝時刻》,都是類編年體的節奏,這種創作模式的優點在于有曆史做軌,怎麽走都是厚重的,而它的代價是敘事性和人物的弱化。一大的故事黃建新在《建黨偉業》裏講過一次了,再一次聚焦這段厚重曆史,固然要求變量。這一次黃建新和鄭大聖從人物出發,選取截面敘事,借李達夫婦的視角重溫一大背後的點點滴滴。故事架構上,影片借取了諜戰片元素,尤其是巡捕房對馬林的死纏爛打和日本特高課的支線,讓故事有了國際視野的廣角。

影片的另一大“美景”,是它的青春感。尤其是劉仁靜、劉恩銘和王盡美三位美少年代表,導演恨不得讓他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滬上花”,令人不禁唏噓“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不要懷疑自己的眼睛,也不要懷疑導演的誠意,想當初一大代表一行十三人,除了何叔衡和董必武是百年前的“70後”與“80後”,剩下毛潤之、李達等都是“90後”,而劉仁靜和鄧恩銘則是“00後”,不過是19、20歲的少年郎。一大代表平均年齡27歲,這些人要是沒有青春感,那就怪事了。
場外的亮相少年郎同理,一大召集令傳到法國時,正勤工儉學的周翔宇(恩來)同學不過23歲,與王會悟、王盡美同年,而鄧先賢(小平)同學不到17歲。他們和一大場內少年組成的中國曆史上最強少年天團,毫不猶豫地站在了曆史的C位,成爲攪動曆史風雲,改變中國命運的風雲人物。這大許就是梁啓超《少年中國說》裏希冀的“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 ;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吧。

